歷史學家是個來自過去的會說話的幽靈。
——霍夫曼
「1764年10月5日,就是在羅馬,當我佇立在這座古都的廢墟裡,在夕陽中緬懷往事,陷於沉思時,看到那些赤著腳的修道士在朱庇特的神廟裡唱晚禱詩,於是我腦海裡第一次閃過一個念頭,要寫一部羅馬帝國衰亡史。」這是一段很有名的自述,曾經激勵過不少年輕人投身古代歷史的研究。說這段話的人叫吉本,後來他真的寫了一部《羅馬帝國衰亡史》,成為西方史學的經典名著。
歷史學家是怎樣成長起來的呢?
我們一起來聽聽另一位英國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的另一番更詳盡、更有豐富內容的自述吧。
湯因比在他的著作《歷史研究》的卷末寫了一篇「自跋」,自述其思想的形成過程,對於影響他一生的人物、書籍和思想表示感激之情。在這篇自述中,我們深深地被一種心靈上的高尚嚮往和人情的溫暖所感動。下面的內容就出自這篇自述:
母親在我幼年時把她對歷史的愛好灌輸給我,啟發了我畢生對於歷史研究的興趣。
愛德華·吉本以他的《羅馬帝國衰亡史》使我領略到他心智能力的偉大和一以貫之的孜孜不倦的精神,令我欽仰不已。
我的曾祖父是位退休的遠洋船長,他和他的老友克勞頓將軍在我們倫敦的寓所壁爐邊的談話,喚起我對印度和中國這些遙遠的異域的神奇嚮往。在牛津的拉丁語言學院學習時,我的導師啟發了我對古羅馬詩人盧克萊修的長詩《物性論》的歆慕,我對這首詩所闡揚的嚴謹而敏感的人格十分欣賞。
我是七歲時在課堂上讀到《聖經·創世紀》的,當時我為自己得以窺見歷史初展時的真義而大為激動。我在八歲時讀彌爾頓的《失樂園》,讀了整整三天,雖然生吞活剝,有許多地方茫然不解,但那種博大、神秘的氣息令我難忘。
我幸而生在一個較早的時代,還有可能在古典文學和《聖經》方面接受舊式的英國的人文教育。英王詹姆士一世時代頒行的《欽定聖經》的語言深深植根於我的記憶之中,它的語調高古而又平易親切,深透理智而直扣心弦。
而我首次瞭解世界通史的概念,是讀了愛德華·克裡西爵士的《世界十五大戰役》。八九歲時,《各國史話》的著者同時為我揭開了埃及、巴比倫和敘利亞文明的歷史,啟發了我對於歷史提綱挈領的興趣。
有一次,在牛津的一家書店裡偶然看到的一部《中國古代史》,使我得以窺見秦始皇統一前的古中國文明。
一部《俄國南方的伊朗民族和希臘民族》使我馳騁在歐亞大草原的遊牧文明歷史中。
我還記得,當1908年6月的一個晚上我乘火車去愛丁堡的時候,讀著亨利·霍華德爵士的蒙古民族史著作,中國的宋、金、西夏朝代、西遼和花剌子模等等歷史情景展開於眼前,我永不會忘記那個晚上我的情緒上的激動。
當我在阿姆普爾福德的修道院裡諦聽唱詩班的贊唱時,領悟到英國教會團體1400多年來面對厄運而堅忍圖存的精神和偉大生命力。
1907年夏天,當我即將升入大學的時候,讀了狄奧多·蒙森的《羅馬共和國史》的英譯本,使我明白好的歷史著作同時也是一件藝術作品。
…………
湯因比接著還列舉了一系列人名和著作,其中包括希羅多德、托爾斯泰、雨果、榮格、穆勒、柏拉圖等許多人的許多著作,他認為自己從中學到了心智工作的方法和文字表現的方法,甚至日常生活中的觀看演出,也能培養他的觀念和悟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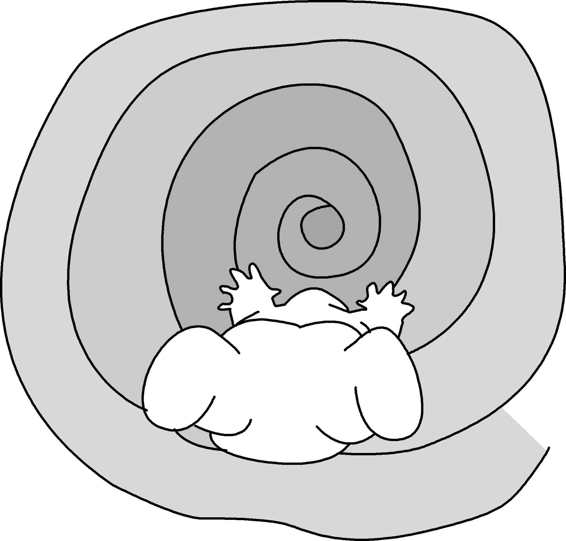
歷史學家飛向過去
從湯因比這位傑出的歷史學家的自述中,如果你能感受到一種無與倫比的偉大的精神價值,一種心靈上的美感,一種對世界、對宇宙的深沉的愛,那麼,我相信你也有可能成為一名歷史學研究者。
再來看看瑞士著名歷史學家布克哈特對古希臘文化史的研究。1872年冬季學期,布克哈特開始在巴塞爾大學發表關於希臘文化史的演說,首次聽眾共有53人。現在我們可以讀到他的《希臘人和希臘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這本書就是在他身後出版的演說集《希臘文化史》的英文選譯本。布克哈特把這個系列演說稱為「情有獨鍾的系列演說」,並且在一開始就立下了自己的目標:我們的任務是站在高處進行觀察,是重新建構希臘人生命中的力量,是研究希臘心靈或精神的歷史;這就是研究文化史的方法和益處。他關注的是精神內核而不是事件的表象;是整體的結構、發展的趨向而不是局部的細節和凝固的瞬間。丟棄「歷史的碎石」,喚起對於古典精神的真正意義上的心領神會與回應,從而保持一種對於古典世界的最鮮活的感情,這就是他的文化史研究的核心目標。
而作為古希臘文化史最傑出的研究者,布克哈特竟然還從未到過希臘,這是何等強烈的精神嚮往!在同樣是在他死後才出版的《世界歷史沉思錄》(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中,布克哈特說:「沉思對我們意味著自由」——或許他是說,在深思中的人可以擺脫時空的約束,神遊於古今;我們也可以說,布克哈特的沉思意味著歷史研究中的自由境界。
這種對於古希臘文化所懷有的強烈的嚮往之情,在英國作家列昂納德·柯特勒爾的《愛琴文明探源》(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中同樣感人,而且有一種類似鄉愁那樣的感受。20世紀50年代,當他來到希臘邁錫尼,投宿於一家路邊小店的時候,開門接待他的店主的名字竟然就叫阿伽門農,令他十分驚訝和激動;當一位持燈少女出現的時候,他真擔心她的芳名不是叫海倫或安德洛馬克。晚上,令他躺在床上難以入睡的是,想到明天就要前往的那些壯麗的、早已在書本上熟知的古代勝跡僅沉睡在一英里外的黑沉沉的山上。幾年前我也曾有機會在希臘各地漫遊,當我站在邁錫尼城堡獅子門下的時候,想到當年阿伽門農和他的軍隊就是從這裡出發奔赴特洛伊的,心情之激盪難以形容。
應該再三詢問自己:為什麼要關注古希臘、關注「荷馬問題」?對此,著有《古希臘文學史》(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的英國著名希臘史學家吉爾伯特·默雷說:「在我的生活中,簡直沒有一種深厚或寶貴的感情,不是由希臘詩歌所激起,或闡明或昇華的。」能給出這樣理由的人在古典與當代生活之間建立了最好的連接橋樑,因而是很有福的。
再來看看近代奧運的創始人顧拜旦。對於曾經置身於奧運熱潮中心的國人來說,這位「奧運之父」並不陌生,但是有誰知道他對古希臘和古典學的嚮往之情?他成長在法國一個信仰天主教的貴族家庭,從小對他有很大影響的是一位博學多才的修辭學老師卡龍神父。古希臘文化是他從小培養起來的人生之夢,修辭學幫助他找到理解古典文本的鑰匙。我們知道,修辭學是古典學中的重鎮,當西塞羅以及後來的人文主義者思考所有關於對表達人的尊嚴的學科的熱愛時,修辭風格的流暢與雋永便總是與成熟心智聯繫在一起。古希臘文化史、古典修辭學等在我們今天強調實用功利主義的教育體系中簡直近乎天方夜譚,但可以說,我們距離古希臘、古典學有多遠,距離現代文明就有多遠;那些狂熱地湧向街頭的人群距離古典學有多遠,距離真正的奧林匹克源泉就有多遠。
歷史學家的成長不僅需要有良好的教育背景,而且更需要有強烈的精神嚮往,更需要在內心漫溢著一種對人類文化記憶的「溫情和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