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爾蘭人喬治·貝克萊(1685—1753年)由於持「物質並不存在」的主張而在哲學界獲得了重要的地位。早在22歲時,貝克萊就做了都柏林大學的特別研究員。後來,他懷揣在百慕大群島建立一所學院的夢想前往美國,但卻沒有成功。在羅德艾蘭住了三年之後,他離開美國回到歐洲。在美國期間,他寫下了著名的詩句「帝國的路線取道西方」,就因為這一句詩,加利福尼亞州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座城市。1734年,他擔任了克羅因的主教。晚年時,他放棄研究哲學,轉而研究他認為有種種神奇藥性的焦油水。
與其他哲學家不同的是,他最優秀的著作都是在很年輕的時候寫的:寫《視覺新論》時,他24歲;寫《人類認識原理》時,他25歲;寫《海拉斯和斐洛諾斯的對話》時,他28歲。這以後,他的著作就不是特別重要了。
在《海拉斯和斐洛諾斯的對話》裡,他發表了令他聲名遠播的否定物質存在的觀點。他以為他是在證明一切實在都是屬於心的,其實他所證明的也就是我們感知的是種種性質,不是東西。性質是相對於感知者而言的。
貝克萊的觀點主要分為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的主題說,我們只是感知到了顏色、聲音等性質,並沒有感知到物質實體;第二個方面說,所有感知到的都屬於心(或在心中)。貝克萊的第一個觀點完全可以說服任何人,但第二個方面的觀點就有些毛病了,因為「屬於心」的說法沒有任何定義。貝克萊之所以提出這樣的觀點,主要是因為他以為所有事物必定是物質或心靈的。在哲學領域,這是一種習以為常的見解。

喬治·貝克萊(1685—1753年)。英國主觀唯心主義哲學家、近代經驗主義哲學代表人物之一
貝克萊說,我們感知到的只是物質的性質,並不是物質的實體,而且,我們也沒有認定「常識認為屬於同一個東西的各種性質,一定是在一個與它們都有區別的實體裡」這一說法的理由。這時,我們就完全可以接受他的觀點。但是我們的接受只是瞬間的和短暫的,因為他後面的觀點就要出現毛病了。接下來,貝克萊又說,所有感知到的性質都是屬於心(或在心中)的,與前一種觀點相比,這個觀點是不同的種類,而且確定性也降低了。這裡提到的觀點,一部分要證明邏輯必然性,另一部分要比較經驗性。
貝克萊的著作《海拉斯和斐洛諾斯的對話》裡,涉及到一個謬論,與下面的這個例子類似。眾所周知,沒有舅舅就沒有外甥。假如甲是外甥,那麼按照「沒有舅舅就沒有外甥」的邏輯關係,甲必然有舅舅。如果已知甲是外甥,那麼他有舅舅就是邏輯必然的,但是,分析甲可能知道的任何事情都推不出這種邏輯必然性。這樣一來,某物如果是感覺的對象,那麼必然有一個心和它產生關係,但並不能由此推斷出,這個物品如果不是感覺的對象就不會存在。
這是一個很常見的謬論。我們可以用由經驗得來的概念組成一些關於種類的命題,不過種類裡的分子可能是沒有被經驗發現的。如果「必」是指邏輯必然性,那麼如果甲「必」是可感對象,貝克萊的這個觀點才成立。對於「除了甲的可感覺性之外的其他性質能推出甲是可感覺的」這一問題,這個觀點並不能加以證明。同樣,這個觀點也不能證明「本質上與我們所見的顏色區分不開的顏色不能因沒有被發現而不存在」這個問題,根據視覺方面的經驗性理由,我們完全可以相信不存在這種顏色。因此,在邏輯上,我們沒有理由說「沒有眼睛和頭腦就不存在顏色」。
根據貝克萊經驗論據的說法,將邏輯論據和經驗論據合到一起就表示有弱點,顯然,如果前者能成立,後者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舉個例子,我認為正方形不是圓形,那麼我不必舉出所有城市的正方形廣場都不是圓的這個事實。然而,現在還是有必要按照經驗論據的是非考察一下經驗論據,因為我們已經否定了邏輯論據。
第一個經驗論據很奇怪。這個經驗論據說,最強烈的熱是很大的痛苦,我們也不能想像沒有知覺的東西會感受到痛苦或快樂,因此熱不在對像之中。在這裡,痛苦一詞有兩層意思,它首先可以是某個感覺的痛苦性質,其次可以是具有前述性質的痛苦感覺。舉個例子,說「一條折斷的腿很痛」時,與這條腿在心中的意思無關。同樣,也許是熱引起了痛苦,因此,說「熱是痛苦時」,指的大概也是這個意思。這樣就可以發現貝克萊這種論據的愚蠢了。
從嚴格意義上說,恐怕關於把手放進溫水的提議只能證明,在此時感知到的是較冷或較熱,並不是極冷或極熱,而且也不能證明這些感知是主觀的。同樣,在提到味道時,貝克萊說,甜和苦都是屬於心的感知,快樂是甜,痛苦是苦。此外,他還多次主張說,在健康時感知到是甜的東西,在生病時也許就覺得是苦的了。眾所周知,氣味只有快感和不快兩種,因此在提到氣味時,貝克萊認為,氣味不能存在於有知覺的任何實體中。不論提到什麼,貝克萊都假設說,任何東西都不能既是心靈的又是物質的,因此,如果不是物質固有的東西,就一定是心靈固有的東西,反之亦然。
以記憶為代表的整整一類與習慣有關係的作用,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心靈現象特有的。舉例來說,被燒過的孩子怕火,但卻不怕點火的鏟子。生理學家認為,他們沒有必要違背物理主義的解釋,於是,他們把和習慣類似的事情都視為神經組織。按物理主義的解釋,被感知到是指某個事件有某種作用。按這個說法,似乎也可以這樣說:河道感知到了衝擊它的水流。或者說:河道是對以往奔流的河水的記憶。如果用物理主義的說法解釋,即使是靜止的事物(物體),也一樣有習慣和記憶。在有習慣和記憶這一點上,活動的事物(物體)和靜止的事物(物體)的差異只存在於感知程度上。

《貝克萊主教與他的隨從》(美國·約翰·斯米伯特繪)
在認識論裡,貝克萊的做法和大多數哲學家的做法一樣,是從所依據的對科學的信賴的知識出發的,並不是從已完成的科學出發的。這樣的話,我們就不必急於提前給知覺對像下定義,而要面臨「我們能否從自己的知覺對像裡推斷出其他事件」這個問題。
和黑格爾及其後繼者一樣,貝克萊也認為「只能存在心和精神上的事件」這一命題是可以得到輕鬆證明的,只不過黑格爾及其後繼者依據的是別的方面的理由,而貝克萊依據的是邏輯方面的理由。但是,我的意見是:這是一個根本性的錯誤(貝克萊、黑格爾及其後繼者都犯了這個錯誤)。有這樣一個命題:過去有過一個時代,那時,這個星球上還不存在生命。我要說明的是,這個命題的真假都無所謂,因為它就如同「世間存在著永遠沒有人算過的乘法算式」這個命題一樣,不能根據邏輯理由駁倒它。被察覺就是成為知覺對象,但這只是說事物(物體)具有某種作用。同樣,從邏輯上看,沒有理由斷定所有事件都有這個作用。
除此之外的另一個觀點雖然沒能確定唯心論為一種形而上學,但如果被證實是正確的話,它卻可以把唯心論視為實踐的方針立即確定下來。一般認為,不具有意義的命題也是無法驗證的。眾所周知,知覺對象是驗證命題的依據,因此,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除了現實的知覺對像或可能有的知覺對像之外,其他任何事情的命題都是不具備意義的。依我之見,如果嚴格解釋這個結論的話,就會發現,這個結論否定我們沒有親眼見到的任何事件。如果我的這個理解沒有出錯,我還可以肯定,在具體實踐中,沒有哪位哲學家願意持有這樣一個結論。對於一個依據實際理由得出的結論而言,這是一個很嚴重的缺陷。我知道,關於驗證(當然也包括驗證和認識之間的關係)的任何問題都太過複雜和艱難,因此我就暫且不自找麻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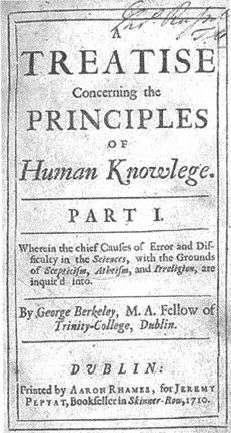
1710年版貝克萊《人類知識原理》扉頁
因果性是先驗的,而且,不管是何種規律,只要是能夠通過觀察得到,那麼就一定是和知覺對像聯繫在一起的。這樣說來的話,可以通過知覺對像表述出來的物理學定律,好像都是可以被證明的。也許,這個表述不僅複雜古怪,還缺乏物理定律應該有的連續性(連續性是至今仍被人們認為是物理定律該有的特徵)。
排除實體以後,種種事件所構成的某種集團或結構一定是「心」,劃分這類集團的過程,必定是由我們稱作心的那類現象所特有的關係完成的。在這裡,可以用記憶做典型的關係說明問題。也許我們可以採取簡單化的方法,把心的事件定義為進行記憶的事件或被記憶的事件,這樣一來,借記憶之力與已知事件聯繫起來的那些事件的集團,就是某個已知的心的事件所隸屬的心。
根據以上定義,我們可以知道,一個心和一塊物質各是一個事件集團,但是,我們不能確定說,任何事件都屬於某個事件集團,因為沒有這樣的依據。同樣,我們也不能確定說,沒有同屬於兩個集團的事件,因為也沒有這樣的依據。也就是說,可能某些事件既不屬於心也不屬於物質,而另一些事件可以既屬於心又屬於物質。要想給這一點下決斷,只有依據詳細的經驗方面的考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