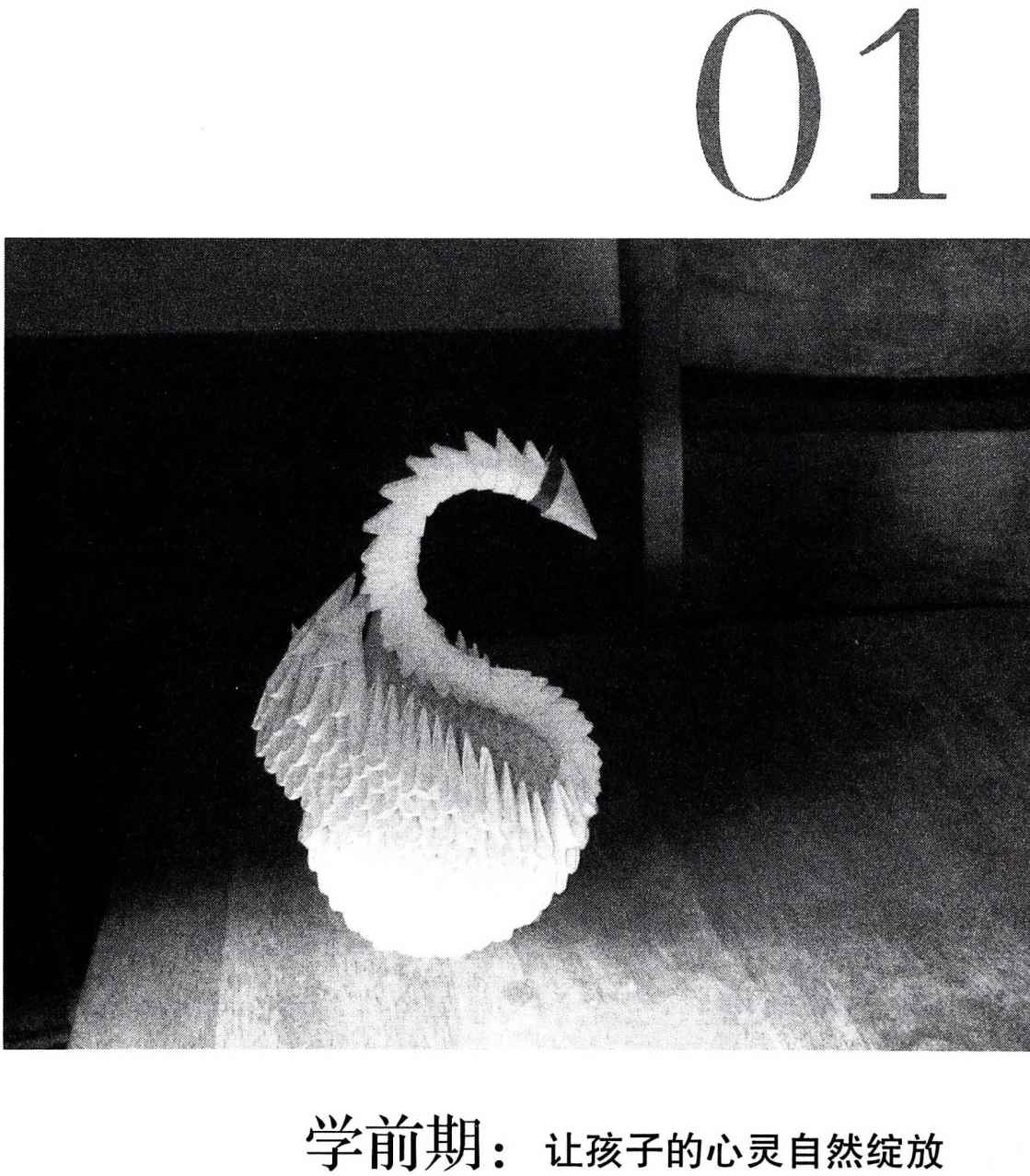嬰兒學得最快的時期,正是成人無法指導其學習的時期。
在生命的最初一兩年時間裡,
嬰幼兒能夠把毫無頭緒的“噪聲”整理為語言,
並用之進行基本的交流,
而這一切都是在無師自通的情況下完成的。
認識嬰兒的大腦
為人父母的,當聽到孩子的第一聲啼哭時,就強烈地感受到自己對孩子的癡情。但是,有多少人能感受到對孩子的敬畏?
“我們在嬰兒床裡看到的那個小東西是迄今為止最偉大的心智,是宇宙間最有效能的學習機器。那精巧的小手指和嘴巴,就是理解陌生世界的探測儀,運轉得比火星巡航器還要精確得多;那皺皺巴巴的小耳朵接收著雜亂無章的噪聲,並將之準確無誤地解讀為意義明確的語言;那雙有時似乎是洞悉我們靈魂的大眼睛,在破解著我們最深層的情感;那毛茸茸的小腦袋裡,每天形成著幾百萬個神經連接。這至少是30年的科學研究所告訴我們的東西。”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學家Alison Gopnik與Andrew N. Meltzoff、Patricia K. Kuhl這樣寫道。他們合著的《嬰兒床裡的科學家:早期學習過程向我們揭示的心智》(The Scientist in Crib: What Early Learning Tells Us about the Mind)一書開篇就指出:人類雖然已經進入了計算機時代,但是,不管比爾·蓋茨拿他的數百億美元和他卓越的技術才能造出了什麼了不起的計算機,世界上最好的計算機比起他的女兒躺在嬰兒床時期的大腦來,也要粗陋得多。再高級的計算機也是人造的,孩子的大腦則是天造的。計算機與嬰兒的大腦一個最根本的區別是:計算機不會自發地應付出其不意的環境挑戰。比如,不管是多麼高級的計算機,沒有中文軟件就無法處理中文信息,還是要依靠人所輸入的程序。一個嬰幼兒則不同。你不管把她或他放在什麼語言環境裡,不用任何語言課程,到兩三歲時都能說話。也就是說,你把全世界最聰明的人都集中在一起,他們也製造不出一種比嬰兒的大腦更有效的學習機器。“早教之母”——意大利教育學家蒙台梭利(Maria Montessori)早就感歎:一個孩子在生命頭三年的學習成就,要成人奮鬥六十年才能達到。所以她提倡以孩子為中心的教育方法:成人的使命是給孩子創造心智發育的良好環境,而不是試圖去“教”他們,要讓比成人更聰明的孩子自己“教”自己。
人類對嬰兒智能的這種認識是建立於現代兒童心理學和生理學研究的基礎之上的。科學家們通過腦電圖等手段發現:嬰兒大腦中的腦細胞或神經元要比成人豐富得多。在嬰兒的腦皮層(控制感性和高層次思維的中心)裡,各部分之間的連接也比成人更充分,運轉得更有效率。這也解釋了人類自古以來的常識:為什麼兒童幾乎學什麼都比大人快得多?
不過,我們更要問的是:這一被現代科學驗證了的常識,對自古以來的教育方法提出了什麼挑戰?既然孩子比大人聰明,為什麼孩子要聽大人的?當然,大人有孩子沒有的經驗,大人靠著這些經驗積累了更多的知識,這是大人權威的依據。但是,即使大人的經驗和知識中有相當多的“內容”值得孩子們學習,難道在學習的“方法”上,更聰明的孩子也要聽那些遠不那麼聰明的大人的指揮嗎?也許大人可以對孩子說:“我年紀大了,腦子不如你好使。但我也曾經是個孩子,曾經像你一樣聰明。我有你的經驗,你卻沒有我的經驗。所以我有指導你的資格。”可惜,我們所謂的童年,主要是指3歲以前,這是超出了任何大人的記憶範圍的時期。大人早已忘記了自己和嬰兒一樣聰明時是怎麼學習的,自然也沒有能力指揮這台自己並不瞭解的“學習機器”的運轉。
我們傳統的教育方法,基本就是建立在這種大人的自以為是的基礎上,他們經常覺得自己具有種種實際上並不存在的能力:自己腦子明明已經不好使了,卻要指揮一個天才如何運用大腦;自己已經沒有什麼彈跳力了,也忘了怎麼打籃球,卻堅持要教科比怎麼“三步上籃”,而且這位科比還必須聽。
我們最習慣的死記硬背,就是經典的一例:腦子已經變笨的大人,要讓比自己聰明得多的孩子遵守笨人所奉行的教條。我們一直說“書讀千遍,其意自見”。我們學習語言的傳統辦法就是背誦。嬰兒則不用這一套。如蒙台梭利所言,嬰兒學得最快的時期,正是成人無法指導其學習的時期。在生命的最初一兩年時間裡,嬰幼兒能夠把毫無頭緒的“噪聲”整理為語言,並用之進行基本的交流,而這一切都是在無師自通的情況下完成的。如果換了成人會如何呢?我們都知道破解古文字或密碼的難度。成人經過嚴格的訓練,大多數人對此還無法勝任。如果你能用十年的工夫破解一個失傳的出土文字,你就是世界級專家,可以到哈佛或者牛津拿個終身教職。這就是嬰兒和我們之間的差距:他們每一個都有比哈佛、牛津的教授還高得多的智商。擺在我們面前的挑戰是我們怎麼向他們學,而不是怎麼讓他們向我們學。你要是一個考不進哈佛的人,就別試圖去教一個哈佛教授怎樣學習他專業領域內的知識。用中國的話說,這叫“關公門前舞大刀”。你要爭取的,是一個旁聽他講課的機會。
現代兒童心理學和生理學的許多研究,其實就是“旁聽”嬰兒這一最大的“天才”給我們講課。學者們大多承認,直接學習這位“天才”的大腦運轉方式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們對自己的嬰兒期都沒有記憶,也無法讓嬰兒來答疑。也就是說,嬰兒無法直接給我們授課,我們只能“旁聽”,也就是從各種側面觀察研究。特別是最近幾十年,科學的發展為我們的“旁聽”提供了各種便利的條件。比如,通過腦電圖等手段,科學家們可以測量嬰兒腦組織的密度,分析其神經連接的階段性發育,在解剖學上對嬰兒的大腦和成人的大腦進行比較。上面所講的兒童大腦的優越性,就是被這些技術手段所證明的。
孩子的觀察力超出你的想像
接下來的問題是:這種生理上被證明的優越性,是如何在功能上體現出來的?這也是許多家長必須面對的問題:當自己說東,孩子卻向西時,究竟是孩子不懂事,還是孩子比自己聰明正確?在什麼時候應該引導孩子聽自己的,什麼時候應該接受孩子的引導?記得女兒不到兩歲的時候,我用童車推著她在街上散步,看到馬路邊一對鴿子正在交配。按照我這個成人的思路,要真給女兒解釋什麼是交配,就要解釋什麼是性行為。女兒還不到兩歲,似乎太早了。況且,鴿子交配,就如同雞交配一樣,公的要踩到母的身上,嘴咬住對方後脖兒的羽毛,母的作掙扎狀,更像打架。我們小時候(也就是七八歲記事的時候)看見雞的交配,都說是公雞欺負母雞(或者“公雞耍流氓”)。所以,我當時就對女兒說:“看看,它們在打架呢。”誰知女兒用小手指著這對鴿子用中英混雜的語言高聲糾正我:“一塊kiss(接吻)!”
這比我的解釋靠譜兒多了。此事多年來一直令我玩味不盡:我對動物的交配或人的性行為都有著基本的知識,女兒則完全沒有。假設我像女兒一樣沒有這些知識,僅憑肉眼觀察,這兩隻鴿子的行為更像打架或者一個欺負另一個,就像幼兒園的孩子一個騎在另一個身上拳腳相加一樣,和人類充滿愛意的親吻非常不同。女兒每天都接受爸爸、媽媽的親吻,也見過自己幼兒園裡的大班孩子打架。但她在不需任何解釋也無任何知識的情況下,怎麼一眼就能看出這兩隻鴿子是在接吻而不是打架呢?她肯定觀察到了我這個成人觀察不到的東西。
傳統的觀念認為,兒童無法集中注意力,沒有耐心,只能跟著感性和慾望走,無法遵循理性的引導。這是兒童智力尚未充分發育成熟、無法像成人那樣進行高強度思考的證據。但是,現在的一些研究修正甚至推翻了這樣的成見。比如,前述的兒童心理學家Alison Gopnik就概括說:“我們有時說成人比兒童更有注意力,其實正好相反。成人比兒童更缺乏注意力。成人善於把許多事情迅速地從意識層面過濾掉,而把注意力集中在一個非常狹小的領域。”我和女兒一起看鴿子交配就是一例。我在解釋這一現象時不自覺地把一些關鍵性的細節給過濾掉了,女兒則根據被我忽視的細節得出了接吻(kiss)的結論。我的注意力之缺乏,實在是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
成人和兒童的這一對比,有著生理學上的根據。腦神經體系有一種不斷進行著的“修剪過程”(pruning process)。在我們睜開眼睛的一瞬間,這種“修剪”就開始,把那些龐雜的、似乎是沒有必要的神經連接都去除掉。在一方面,“修剪過程”就像收拾房間一樣,把我們的大腦整理得更乾淨整齊、更有效率,使我們能夠排除干擾、集中精力。但在另一方面,因為“修剪”得太乾淨簡潔,彷彿是把一些一時不用的“傢俱”都給扔掉了,這一過程也就把我們的思維變得更為狹隘,導致了學習的困難,使我們缺乏對新環境的適應能力和吸收新知識的能力,就好像被收拾得乾乾淨淨的家在應付幾位不速之客時竟找不到多餘的凳子坐。從生理的角度說,嬰兒沒有經歷這樣的“修剪過程”,其腦組織更密集,更有可塑性,其構造中有非常少的抑制性神經遞質(inhibitory neurotransmitter,一種防止神經元被激活的化學物質)。這就使嬰兒的大腦充滿了比成人多得多的飛速馳騁的思緒。這就是為什麼他們的思維強度反而是成人無法達到的。Alison Gopnik舉了一個簡單的例子,經過“修剪過程”的成人,大腦的神經連接簡單明瞭,進而更有效率。結果,成人比孩子更容易把自己的鞋帶繫好。相比之下,未經“修剪”的兒童大腦神經連接四通八達,甚至以成人的標準來看是混亂無序的。這就使孩子沒有辦法集中精力繫好鞋帶,但卻能輕而易舉地同時掌握三門語言。那麼,兩者誰更優越呢?
用個更直接的比喻,成人的智力像個手電筒,當準確地射到一件物體上時,這件物體的形態就非常清晰地顯示出來。兒童的智力如同一盞燈籠,點亮以後光芒四射,周圍的物體大致都能顯現,但是不像在手電筒照射下那麼清晰。我們在黑暗中走路,靠手電筒能看清眼前每一塊絆腳石,但路究竟通向哪裡卻不是那麼一目瞭然,甚至看了這個漏了那個。打起燈籠,則頓時四下亮堂、一覽無餘,很容易看清大概的方向。“修剪過程”的目的本來是提高效率,但是也使我們喪失了太多的神經連接。這些神經連接也許僅僅是因為一時無用而被淘汰,但時過境遷後可能派上大用場時,卻已經不在了。這就使成人在觀察世界時經常忽視了太多看似多餘混亂、實際可能是非常關鍵的事實。這也是成人的思想為什麼越來越僵化、越來越不能接受新鮮事物、越來越難以適應新環境的原因。
法國象徵派詩人波德萊爾有句名言:“天才不過是能自如地恢復自己的童年而已。”成人必須向兒童學習,只有設法恢復自己的童心,才能保持創造力。娛樂、坐禪等等,都有此功能。根據《波士頓環球報》的報道,一些科學家在成人看電影時用腦電圖記錄他們的大腦活動,發現他們大腦前部的活動被抑制,大腦後部與視覺相關的部分則被激活。Alison Gopnik指出,這就是在成人大腦中發生的瞬間即逝的還童狀態:你繪聲繪色地捕捉到眼前所發生的一切,一下子喪失了自我意識,完全想著屏幕上的事情。在坐禪的玄想中和被美麗的景色所震撼之時,成人也會出現這種“忘我”、“無我”的境界,這是一種兒童的境界。他們大腦中的神經連接是如此豐富活躍,乃至無法把思想集中在“自我”身上。用禪師鈴木俊隆的話說:這就是起初的心智,是人像嬰兒一樣思想的時刻。用心理學家的語言來解釋,大腦經常在你不試圖控制它時運轉得更好。
我們傳統的“早期教育”,實際上是在做相反的事情。這種教育,是要過早地把孩子的智力發育納入嚴格結構化的成人模式,加速受教育者腦神經的“修剪過程”,進而更早地使孩子的大腦僵化、封閉、喪失學習能力。所以,當孩子上這個班、那個班,學鋼琴、外語、美術,納入成人的學科時,家長一定要格外注意。孩子腦神經複雜豐富、思緒流動迅速,很難在一件事情上停留太久,也不受成人的意識框架和學科的局限。幼兒的學習淺嘗輒止也許是好事。除非像莫扎特那樣的天才,小時候在一件事情上太專注,可能會不自覺地把孩子的想像力和在其他方面的創造力給砍掉。我在《一歲就上常青籐》一書中引述的一些研究證明,過早開始識字的孩子後來的閱讀能力反而比晚開始的孩子要差,像日本這種過早開始成人式教育的東亞社會,人均諾貝爾獎得主的比例遠比那些不讓孩子在5歲前讀書的同等發展水平的歐洲國家要小。道理很簡單:孩子的腦神經被過早“修剪”,其學習過程過早被納入成人的學科中,結果會導致他們的思路太狹隘,也許照本宣科時更能集中注意力,但是創造力受到了極大的損傷。
在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傳統的死記硬背的方式並不是好的早期教育方式。比如我反覆舉例的古詩:“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我無意貶低此詩的偉大,但是這畢竟是一個人的感受和詮釋。詩人本身的思維是發散式的,大腦的神經連接是豐富活躍的,情感狀態是亢奮忘我的,所以才能言人所未言。此詩的原創性,正在於其不可重複性。如果你一定要讓孩子重複、背誦,就是按這一單一的模子對孩子的腦神經連接進行“修剪”,毀掉了他或她成為詩人的潛力。比如,孩子如果真登上鸛雀樓看到這樣的景觀,本能的結論也許不是“更上一層樓”,也許是想飛翔,也許是想追逐入海的黃河。甚至孩子們對景觀本身的描述也各有不同。他們也許想白日飛到天邊一把拎住快入海的黃河,停止其奔流,也許白日和黃河站在地平線上“一塊kiss”,也許是黃河正在把白日沖走……我這麼個中年人也能想出許多,對孩子們而言,可能就更是無限的了。但是通過背誦,天真爛漫的孩子就變成了心如死灰的老學究。
孩子是人生最大的禮物,也是你最好的老師。你從孩子身上學到的,常常要比你能教給孩子的更多。應該發生的,是孩子讓父母的思想和精神生枝開花、枯木逢春,而不是父母把孩子這一棵枝葉茂盛的小樹砍成了一根光禿禿的樹幹。
幼兒園戰爭
其實,成人對童年的入侵,已經是個世界範圍的現象,正在引起全球教育學家、心理學家和家長的警覺。
不久前,一位美國母親在網上發飆:“我上幼兒園的女兒每天拿回來快一個小時的家庭作業!她還不會讀,怎麼寫?怎麼可能回答卷子上那些問題?她的作業自然成了當媽的作業。我每天下班5點才回家,孩子也是差不多那時候回來。我要先忙著做飯,等吃完晚飯,還要給孩子的學校忙一個小時的家庭作業。而且,我一管她,更小的孩子誰來管呢?這實在太不公平了!”網友們紛紛回應:“老師總說是15分鐘的作業。可是,孩子本來精神就不集中,作業又那麼難,怎麼也要一個小時。”“你要大膽地和老師理論。這不僅是替你自己說話,也是替別的家長說話。”
這是美國幼兒園大戰的一角。在最近二十年,美國的幼兒園裡發生了一場靜悄悄的革命。本來,幼兒園只是個孩子們玩耍的地方,沒有任何書本的因素。但不知不覺中,幼兒園不僅教讀書、寫字、算術,甚至還有頗為系統的課程要求,老師要照本宣科地跟著教學大綱走,孩子們則每天帶回家一堆家庭作業,要按時完成,家長檢查、簽字等等。總之,如今的幼兒園,越來越像是小學的低年級。
這種幼兒園小學化,和高中大學化一樣,是美國教育的一個大趨勢。以高中而論,學生畢業時往往已經通過了許多“高級課程考試”。這種高級課程,是大學入門課的水平,通過了這個考試就可以在大部分大學免掉相關課程的學分。《新聞週刊》的全美高中排名,甚至以各校提供的“高級課程”的數量為基準。以教育上最為領先的馬薩諸塞州為例,本來該州最好的公立學校是波士頓拉丁,這是美國第一所高中,培養了四位哈佛校長,進去要考試。但是,1992年馬薩諸塞州議會決定建立“馬薩諸塞數學與科學學院”(Massachusetts Academy of Math and Science),通過考試招收全州最優秀的學生來讀高中最後的兩年。這所學院,說是半個高中(正常高中是四年),實際則設在伍斯特理工學院(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校園內。學生第一年上精英級的高中課,第二年則在伍斯特理工學院像普通本科生一樣選課。因為伍斯特理工學院在美國算是一所科技名校,學分絕大部分大學都承認,馬薩諸塞數學與科學學院的高中畢業生,實際上也就都是該上大二的學生了。該校在各種成績上,也大有超越波士頓拉丁之勢。
應該說,高中大學化,對一部分聰明的學生而言還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幼兒園小學化則產生了大量的副作用。2009年美國的“兒童聯盟”發表一份報告,題目是“幼兒園的危機:為什麼我們的孩子在學校需要玩耍”,警告幼兒園小學化正在全面摧毀孩子的身心健康和學業的發展,必須緊急剎車。
報告提出的事實是清清楚楚的:全日制幼兒園的孩子每天花在閱讀、算數、準備考試和應試上的時間,高達兩三個小時,而自由活動的時間則僅有30分鐘。學業的壓力,使孩子變得越來越憤怒、越來越有侵犯性,行為問題日益加重。幼兒園小學化毫無必要地加速了孩子的學業,造成了“孩子老得快”(KGOY:Kids Getting Older Younger)的現象。調查表明,那些從幼兒園就開始讀書的孩子,學業確實起步早,比其他孩子領先,但是,這種領先到四年級時就消失了。在那些“問題孩子”(kids at risk)中,早讀書反而帶來了嚴重的問題。早讀書使這些孩子的智商在初期有所提高,但到15歲時,他們的學業急速下降,還不如那些晚讀書的孩子。
這種“死讀書、讀到死”(drill and kill)的惡果是國際性的。德國在20世紀70年代進行了教育改革,把幼兒園從以玩為主轉化成以學為主。後來有學者對50名在以玩為核心的幼兒園長大的孩子和另外50名在以學為核心的幼兒園長大的孩子進行了對比,發現在以玩為中心的幼兒園中長大的孩子,在閱讀、數學等方面明顯比在以學為中心的幼兒園中長大的孩子要好,而且在情感發育、社會能力上更健康,在創造力、口頭表達能力和勤奮上,也具有明顯的優勢。面對這樣具體的證據,德國的幼兒園又改回到以玩為中心去了。芬蘭的幼兒園一直堅持讓孩子玩,沒有小學的內容。另外,芬蘭的孩子7歲才上小學,比美國的孩子晚一年。但是,芬蘭15歲的孩子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進行的“國際學生估測”中,一直在西方國家中排名第一。
為什麼在幼兒園讀書會毀了孩子?要想理解這一問題,就必須回顧一下幼兒園的歷史。幼兒園是德國教育家福祿培爾於1840年前後創立,這是一場不折不扣的教育革命。在工業革命以前的歐洲,孩子在7歲前一般不上學,上學則無非是滿堂灌的大課和背誦經典,這就和中國式的死記硬背非常接近。後來盧梭寫了《愛彌爾》,主張孩子要拋開課堂,到大自然中去,讓自己的手腳和眼睛當第一位老師,從直接的經驗中學習,這在哲學上為現代教育奠定了基本的原則。接著,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齊把盧梭式的哲學貫穿到教育實踐中,創立了實體教學法。他提出,孩子在接觸一個概念前,必須先接觸這個概念指涉的實物,通過直接和實物的接觸獲得知識。詞語、閱讀當然都屬於概念的範疇,屬於成人世界,實物則屬於孩子的世界。教育要以孩子為中心,就必須從實物開始。福祿培爾作為裴斯泰洛齊的追隨者,把其實體教學進一步深化,發明了“福祿培爾的禮物”,實際上是一系列做手工和遊戲的材料,積木是其中的核心。這樣,他把裴斯泰洛齊的實物抽像化為積木式的幾何形體,孩子可以像科學家們用原子來解釋萬物一樣,用積木等基本元素構成自己的世界。
這套教學的有效性,使幼兒園成為世界學前教育的主流。現代兒童心理學、教育學的研究不斷證明,孩子在這種由成人引導和組織的遊戲中能夠最有效地學習。他們能夠自己發明場景和故事,解決問題,磨煉社會技能。他們知道自己要做什麼,而且做起來很自覺、很努力。因為他們有內在的動力,從遊戲中很自然地就學會了如何成功地追求自己的目標。那些在這種複雜的遊戲中長大的孩子,比起不太愛遊戲的孩子來,有更好的社會能力、理解他人的能力、更豐富的想像力和更高的語言能力。他們性情更溫和,更有自制力。動物的研究也證明,經常做遊戲的動物比不做遊戲的動物有更靈活的大腦、更複雜的神經系統。
以上這些,本是戰後歐美幼教的主流理論,但是,在最近二三十年的時間裡,美國的教育實踐漸漸偏離了這種理論,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全球競爭。冷戰前的全球競爭是國家競爭,個人之間很難跨國較量。冷戰後美國成為獨霸,但因為全球化的國際人才流動,美國人再不可能躲在國界後面自己過日子了。在個人的層面上,美國人要和來自世界各地的人競爭,彷彿是大家都在申請一個工作。而移民,特別是亞裔子弟的優異學術表現,使美國的家長坐立不安,生怕自己的孩子日後被別人擠掉。舉例而言,2005年波士頓34所公立高中的第一名(即被師生選為畢業典禮代表學生致辭的人),有20名是移民或者移民的孩子。有的孩子才13歲,剛到美國時一句英語都不會;有一個還在等待遣返。最近還有一些研究,調查亞裔和拉美裔移民,發現第一代移民學術表現最好,第二代則稍弱,但到了第三代就明顯下降,和美國主流社會的學生差不多了。也就是說,越是美國化,學術表現就越差。再根據國際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McKinsey(麥肯錫咨詢公司)等權威機構的調查評估,在2006年30個主要工業化國家15歲的學生中,美國學生的數學水平排第二十五,科學排第二十四。在40年前,美國在高中畢業率上還領先於世界,如今在28個工業國家中排第十八。在1995年,美國的大學生比例還是世界並列第一,十年後跌到第十四。這樣裡裡外外不如人,日後怎麼生存?於是,許多美國家長越來越迫切地要求讓孩子早點起步。
基於這樣的壓力,聯邦政府也大力投身於教育。1997年4月17日,“早期兒童發展和學習白宮會議”舉行,第一夫人希拉裡不僅出席,而且發表了重要講話。早期兒童教育成了美國的國策。在布什任上,國會又通過了《不讓一個孩子落後》的法案,其中一個核心內容就是加強聯邦政府對學校的監督,通過標準化考試的辦法確立基本的教育水準,懲罰那些達不到標準的學校。結果,標準化開始越來越熱。我女兒從四年級開始有全州的考試,有時一周要考兩三次。有學習慢一點的孩子,嚇得不肯來上學,家長只好將之轉到私立學校。為了讓孩子們在四年級時適應得好一些,許多學校也紛紛從幼兒園起就開始為標準化考試作準備。比如,有些學校採取了家庭作業遞進制,每升一級,家庭作業多10分鐘,從幼兒園的10分鐘家庭作業開始。這樣,到了四年級需要應試時,孩子就自然養成了一天做50分鐘作業的習慣。當然更不用說,商業教育公司大肆兜售《嬰兒愛因斯坦》、《嬰兒莫扎特》之類的產品,許多家長生怕孩子落後,要求學校多留作業。
這場幼兒園的家庭作業大戰,體現了美國教育應試化的趨勢。面對這樣的趨勢,中國要不要追風?事實上,中國根本不是追風的問題。中國的應試教育之風早已吹在美國的前面,早已滲透到了更小的年齡層中。不過,美國和西方這種早期應試教育的經驗,還是給我們提供了很有參照意義的反面教材。畢竟,西方的心理學、教育學的研究比較發達,能夠追蹤接受不同類型教育的孩子從四五歲一直到成人時期的表現,比起我們普通人的印象來要準確得多,而且能夠進行跨國比較。前面已經提到,目前歐洲的研究結果證明:接受了早期應試教育的孩子,雖然小學享受著短暫的領跑階段,但到中學以後學習比較慢,普遍被沒有接受早期應試教育的孩子趕超。我們日常的經驗也能提供不少印證。那些從小用功的乖孩子,到了中學後就越來越沒有優勢,似乎大腦已經老化。而一些調皮搗蛋的孩子,小學時不好好讀書,但到了初中或高中突然“懂事”,學業突飛猛進。我們常說,這種孩子的大腦還處於清新狀態,特別好用。
其實,美國的應試教育有許多社會原因。大體而言,應試教育在中低產階層中比較盛行,在中高產中則受到許多抵制和批評。中低產階層,特別是貧困階層,一般家長的教育程度很低,不知道怎麼教育孩子。同時貧困地區的學校很窮,以有限的資源解決弱勢階層子弟的教育問題,最有效率的辦法就是批量生產,一個照本宣科的老師(這種老師經常素質不高,無法創造性地教學)管一大堆孩子,用統一考試來測量進度,多少能保證基本的教育底線。中高產階層所在的學區相對來說也比較富裕,能花得起錢雇更好的老師。素質高的老師不需要統一教程,每個人教的班級裡人數又很少,當然可以進行啟髮式教學。更重要的是,中高產的家長至少是大學生,對教育的體會要深刻得多。即使沒有學校,他們大多也能在日常生活中對孩子循循善誘。所以,教育水準高的家長,大多要求孩子的教育是“對話式”,而不是“滿堂灌式”。
我女兒在這方面非常幸運。她從1歲半開始就進入了紐黑文一家著名的幼兒園“創造孩子”(Creating kids)。該幼兒園遵循的是哈佛著名心理學家Howard Gardner的“多重智力”理論,這套理論認為,兒童乃至人的智力比傳統學校課程所涵蓋的要寬廣得多。傳統學校課程主要以語文和數學為核心,擴而廣之不過是文史和數理,這基本上是傳統的智商理論所強調的能力。但是,Gardner發現人的能力要廣泛得多,如音樂、肢體運動、人際互動等等。他主張突破學校常規課程,給孩子更廣泛的發展機會。Gardner的理論雖然還有許多爭議,但他至少意識到成人對孩子智力和情感發育過早地干預和“修剪”是多麼有害。女兒所在的這個幼兒園,在Gardner的影響下堅持自然成長的原則。其中的一個硬規矩就是絕不教讀書識字或者算術,從來沒有家庭作業。同時,幼兒園強調老師給孩子讀故事,教孩子各種舞蹈,帶領孩子接觸自然(玻璃窗上設有透明的鳥窩讓孩子觀察鳥兒的家庭生活)等等,保證孩子絕對快樂。我們當時還有些擔心,曾質詢過幼兒園的主管是否應該讓孩子認識幾個字母,但被乾淨利落地拒絕。結果呢?女兒上小學一年級時,閱讀已經很好。早晨醒來看父母還沒起床,自己先讀半個小時的書。如今到12歲,也是班上頂尖的學生之一。也難怪,當時耶魯的許多教授和研究生,為了把自己的孩子送進這個不教讀書寫字的幼兒園而不遺餘力。
我接下來要討論的,就是父母怎樣根據孩子不同階段的發育特點,最大限度地激發孩子的潛力。記住,這裡講的是“激發”,而不是“灌輸”。“激發”是點燃孩子內心的火焰,等這火焰燒起來,孩子的成長你想擋也擋不住。“灌輸”則是把你有的東西急急忙忙地硬塞給孩子。最後孩子所掌握的,大不了就是你有的東西,或者你認為有用的東西,很難有超出你想像的發展。而在大部分情況下,硬塞給孩子的東西很難成為孩子自己的東西。總之,孩子是個幼苗,家長和老師要對之施肥澆水,培育其內在的生長動力,而無法替代他們的生長。下面,我就將具體記述和討論這一施肥澆水的過程。
讓孩子的心靈自然綻放
那是2004年的夏天,我們全家從紐黑文移居波士頓。我搭乘搬家公司的大卡車,5歲的女兒則和媽媽一起乘火車和我到新居會合。大家安然到達後,妻子興沖沖地告訴我在列車上發生的事情。
當時列車正駛過海邊一片廣闊的平野,鐵路兩側隨風搖曳的樹在車窗外飛逝而過,彷彿是一行綠色的舞女。女兒驚喜地用小手指著窗外叫起來:“媽咪,那真是美麗,就像電影一樣。那是一種破碎般的美麗!”(Mammy, they are so beautiful, just like movie. And it is a broken kind of beauty.)當時周圍素不相識的旅客聽到她的話,一臉吃驚的表情。有的還轉過身來,讚許地把她好好打量了一番。
應該說,她的語言非常簡單,而且不太規則。但是,“破碎般的美麗”這一句,實在是點睛般地描繪了透過飛馳的車窗奔湧進來的景色。她的語言是和這景色直接撞擊而產生的,其本身的幼稚和不規則也正好反映了她詩一般的原創。乃至妻子在對我這位不在場的父親複述時,也讓我身臨其境、刻骨銘心。
這一幕,體現了我們的教育哲學:讓孩子的心靈自然綻放。任何家長的雕琢,都可能是對這率真的童心的摧殘。
把教育留給孩子自己
什麼是家長的雕琢呢?我不妨假設性地描述一個大家絕對不感到陌生的景象:
一個“教育媽媽”帶著寶貝女兒乘坐同樣的列車,列車穿過同樣的平野。這位“教育媽媽”絲毫不忘自己的本職,手指窗外叫著女兒:“寶寶快看,外面多漂亮呀!你還記得咱們剛剛學的詩嗎?”聰明的女兒馬上朗聲背出: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啊,寶寶真聰明!”媽媽驕傲地鼓起掌來……
應該說,在家教良好的家庭中,這一景像是相當常見的。這樣的教育,比起完全沒有教育來當然要好得多。應該說,那位母親很有修養、很聰明,循循善誘,希望通過窗外的景色幫助孩子理解經典。但是在我看來,她這種教育方法本身卻不自覺地扼殺了孩子天生的潛能。孩子除了背誦了一段一千多年來世世代代都在背誦的古詩外,沒有顯示出任何創造力。相反,大人無意中用古詩捆住了她想像的翅膀。孩子不是觸景生情、自由思想,而是按照大人鑲嵌於其心中的框架來感受。如果大家都這樣培養孩子,孩子長大後也就千篇一律,難以特立獨行。有時看中國的孩子表演節目,他們似乎很懂得大人眼中的“可愛”是怎麼回事,而且非常熟練,本能地按照大人的期望來表現出“可愛”的樣子,似乎是把自己的性格按照大人設計好的模子填進去的。那一張張稚嫩的臉上,經常露出一絲早熟甚至世故,童心反而喪失了。
這當然是教育的結果。我一直堅持,讓孩子背古詩就是一種非常糟糕的教育方法。請不要誤會!我並不是說背古詩的孩子都不行。相反,很多這樣的孩子長大後可能在各方面都優於他人。但他們之所以優秀,完全是出於不同的原因。道理很簡單,除了智力上的因素外,背古詩需要大人監督。能背許多古詩的孩子,一般和大人的互動比較多,從父母乃至親友那裡得到的關注也比較多。這樣,他們的情感發育比較充分,心理自信,學什麼也就都會比較快。但是,在家長和孩子充分交流,並對其教育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的前提下,背古詩恐怕就不如其他教育方法有效了。換句話說,只要家長充滿愛意地和孩子消磨時間,孩子就可以獲得許多感情的滿足。如果孩子發現自己沒有別的辦法和父母處在一起的話,她就寧願給父母背古詩以成為家裡的小中心。不過,如果她有別的選擇,她寧願和父母一起做遊戲、談天說地,甚至做家務事。這些活動,可能都是比背古詩更好的教育手段。
開篇提到的蒙台梭利(1870—1952),在兒童教育上的信譽恐怕是很難有人與之匹敵的。她是意大利的第一位女醫生,年輕時致力於教育那些智障、不幸福,甚至被認為是“不可教”的兒童。1896年,她在“教育議會”上就訓練智障兒童進行的講演,讓在場的意大利教育部長心服口服,馬上任命她主持一個智障教育中心。結果,在不久後舉行的國家讀寫考試中,她的幾名8歲的智障學生不僅通過了考試,而且分數高於考生平均成績。這一成就被稱為“第一個蒙台梭利奇跡”。蒙台梭利的回答是:既然智障的孩子都能如此,她的方法在正常的孩子身上就更有效。於是她很快開辦起自己的學校來。蒙台梭利教育法和蒙台梭利學校很快就遍及全球。如今不僅在歐美等發達國家,就是在印度、中國等發展中國家,蒙台梭利學校也都發展成卓有聲譽的教育機構。下面是蒙台梭利的一段經典論述:
“教育並不是由老師來完成,而是自然過程在人身上的發展。教育並不是通過聆聽詞語而獲得,而是孩子通過對環境的反應而形成的經驗。老師的職責不是說教,而是為孩子在特別的環境中準備和安排一系列從事文化活動的主題……這樣,所造就的不是一個學校,也不是一套教育方法,而是人本身:一個通過他的自由發展來顯示其本色的人,一個有著顯而易見的偉大品格的人,乃至直接的思想壓制已經對他無能為力、限制不了他的內在發展、征服不了他的精神。”
我本節開篇時的兩個場景對比也正要說明這個問題:孩子本身就是一首詩。女兒是在沒有任何大人的指導和暗示的情況下對環境作出的自然反應。“破碎的美麗”實際上就是她創造的一行詩句,只是她沒有意識到自己是在作詩而已。接下來假設的那位“教育媽媽”,則處心積慮地教孩子詩歌,但孩子除了會重複別人外,並不能作出詩來。孩子心中的“內在的老師”和“教育媽媽”這個“外在的老師”的高下,一比就能看出來。還是讓孩子自己教育自己好。
家長應該幹什麼
那麼,當把教育留給孩子自己時,家長應該幹什麼?當然不是無事可做。其中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幫助孩子心中的“內在教師”找工作:把孩子放在各種各樣有益的環境中,讓其心靈自發地感應。女兒兩個月到十四個月這一階段,我們全家住在日本的橫濱市,家離海岸著名的山下公園很近。從一到日本開始,我就幾乎每天都要帶女兒到公園走一趟。因為海濱到處是海鷗,飛起來十分壯觀。我是希望這場面對她有所刺激。我只記得我小時候和父母去頤和園時第一眼看到昆明湖時那番美麗的震驚。我忘了是幾歲,只是知道從小的多少教育我都沒有記住,可這一瞬間的印象則終生難忘。我希望女兒早點有這番經驗。但是,孩子實在太小。我經常還沒有走到公園,她就在我胸前的嬰兒掛袋裡睡著了。我只好在公園裡苦苦等著她醒來,而當她真看到海鷗時,似乎也不如我期望得那樣興奮。我實在是搞不懂她小腦袋裡的“內在老師”是怎麼工作的。
和孩子的這番經歷使我認識到,我並不懂怎麼教育她,還是她自己更懂,而且她經常能教育我。我帶她外出把她抱在胸前時總是讓她臉朝前,以更好地觀察外面的世界。而我則觀察她,向她學習。一次,從一個購物中心出來,她眼睛一亮,頭仰起來,兩隻小手上揚,嘴巴也不禁張開,彷彿是在驚歎:“哇!”我馬上順著她的眼神看去,面對的正好是廣場上的一座巨大的抽像雕塑。我忘了她那時是四個月還是五個月,總之還不會說話。這大概是我觀察到的她第一次對外界有如此激動的反應。其實,這一雕塑坐落在我每天上學必走的路上,但我來去匆匆,從來沒有太注意。女兒的反應,則使我開始仔細端詳這尊雕塑,發現了其藝術氣質。這一點一滴的小事不斷地告訴我,這幾個月的嬰兒,確實比我敏感,心靈更加開放。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之一就是把她抱在胸前,讓她臉朝前,在各種自然風景、城市廣場和雕塑間走來走去。她心中自有“內在教師”給她講解,比我高明多了。
女兒長到三四歲以後,和成人建立了基本的溝通能力,我們有對她傳授知識的機會了。但是,我們從來都堅持這樣的原則:萬事讓孩子自己先經歷體驗,切不可事先給她一個框框或結論。做家長的,必須保持在孩子面前的謙卑以及對童年的崇拜。如果我們相信孩子是花朵的話,就讓她自然綻放,也不要想當然地預期花開了後是個什麼形狀和顏色。用手去把花瓣掰開,即使能一時領略盛開的景象,那花也很快會枯萎。我們是根據自己的知識對環境作出反應,孩子則根據她的內在直覺和經驗對環境作出不同的反應。我們總懷疑自己的反應是平庸的,她的反應則是這個小生命對世界的新貢獻。過早地對她“傳授知識”,實際上就是用我們有時是陳腐的知識替代了她最有創造性的直覺。還是回到開篇:孩子要是太早就被傳授了“白日依山盡”、腦子被成人的知識框住,可能就喪失了自己的感知能力,說不出“破碎般的美麗”來。
好爸爸有多重要
這是本父親寫的書。雖然我對母親們的偉大充滿敬意,但要利用這個機會特別講講爸爸的重要。
我在《一歲就上常青籐》中記述育女的經驗,說在女兒7歲半前,我每晚都要和她一同躺下,撫摸、按摩著她的背,直至她入睡。這一“保留節目”,沒有一日錯過。直到女兒11歲半時,我偶爾跳過幾天,但大部分時間還是如此。連她自己都知道這樣實在太嬌慣了。
女兒跟媽媽親是天性。有些明明需要找爸爸的事情,也本能地喊“媽咪”。這時做父親的總難免有點酸溜溜的感覺。但我的“保留節目”當媽的卻搶不走。媽媽哄女兒睡覺,很難哄著,經常萬般無奈之下把事情再推給我。而女兒一旦看到爸爸到了床前,馬上有一種安寧之感,睡意矇矓,一會兒就進入夢鄉。
更重要的一點:我哄女兒睡覺時,她經常話特別多。父女倆有時乾脆討論起問題來,從音樂、歷史、文學,到道德、人生、社會、經濟、政治,幾乎無所不涉及。我一直稱這是“睡前討論班”。比如貨幣供應量對物價的影響、政府是否應該在財政困難時大印鈔票等等大人的問題,女兒居然也興致盎然地要和我討論,有時興奮得不想睡覺。
俗話說,孩子是媽媽身上掉下來的一塊肉,更不用說孩子一生下來就要母乳餵養,和媽媽在身體上幾乎都難以分開。20世紀對發展心理學、教育學、兒科醫學等影響巨大的依戀理論,主要也是圍繞著孩子和母親的關係展開。養育孩子是母親的天性,舉世皆然。父親在這方面和母親競爭,難免要自討沒趣,還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為好。甚至動物世界都是這個規矩。美國雖然經歷了女權運動的洗禮,父親越來越多地操持家務、帶孩子,但耶魯大學的臨床心理教授和兒童專家Kyle D. Pruett驚歎,關於父親在教育孩子中的角色問題,在英文資料中幾乎沒有像樣的專著。
根據Pruett教授的研究,新生兒六周時就能分辨出父母的聲音,八周時就對父母發展出不同的期待。父愛和母愛一樣,對孩子的發育都非常重要。比如,那些經常受到父親照顧(包括換尿布、抱著哄覺、講故事、讀書等等)的孩子,長大後抵禦生活壓力的能力明顯要強一些。他們更自信、更有耐心,功課也好很多。和父親獨處時間長的孩子,探索性的行為和社會技能都更加突出。這在父女關係中表現得特別明顯。心理學家Ellen Bing在20世紀60年代初進行過一項開創性研究,發現父親小時候給女兒讀書,對女兒高中時的語文能力有重大影響,而母親不管是給兒子還是女兒讀書,都沒有這麼強的影響。另一位學者Norma Radin發現,女兒或兒子的智商,和父親的關愛程度有正比關係,和父親的嚴厲程度則有反比關係。中國那種“嚴父慈母”的教育方法,似乎有些站不住腳。Henry Biller則揭示出,缺乏父愛的孩子在學習數學時的能力要稍弱。20世紀70年代對MIT(麻省理工學院)一年級女生的研究也證實,父親和女兒分享在數學和分析性思維上的興趣,對孩子日後在這些領域的能力和興趣有著巨大的塑造作用。賓夕法尼亞大學的Frank Furstenberg和Kathleen Harris的研究提供了十分具體的數據:那些感覺和父親親密的孩子與那些和父親沒有這種親密感的孩子比起來,上大學或者高中畢業後維持穩定工作的比例要高一倍,進監獄的比例低80%,青春期懷孕的比例低75%,經歷多種抑鬱症的比例減少一半。
可見,儘管對父愛、父教的研究還很缺乏,但是父親對孩子成長髮育至關重要的意義已經被許多心理學家所證實。隨著西方對這一問題漸漸開始重視,估計更多的研究結果會不斷湧現出來。
那麼,父愛、父教和母愛、母教究竟有什麼區別呢?理解了這個問題,我們才能扮演好父親的角色。
生物進化過程造就了父母的明確分工。母親從一開始就負責滿足孩子基本的生存需求,比如餵奶。母親後來對孩子的照顧,也多是圍繞著這種生存的物質需求而展開的:孩子是否吃飽了、穿暖了,是否乾淨,等等。人的精力和時間都是有限的,當母親完成了這些職能後,對孩子其他方面的發展就有些心有餘而力不足了,這也正好為父親提供了舞台。研究者發現,父親和孩子的關係,主要不是體現在溫飽等方面的基本物質照顧上,父親更關注的不是這些,而是直接和孩子玩起來。母親雖然也和孩子玩,但即使玩起來也處處體現了母親對孩子的基本物質需求的考慮。母親總是用兒童玩具和孩子玩,玩的是地道的孩子遊戲。父親則更加“非功利”,經常不通過玩具和孩子隨意地玩,而且特別喜歡讓孩子參與自己的遊戲,比如打球,而不是玩孩子的遊戲。總之,父親和孩子的互動,往往超越了生存的基本物質需求,進而引領孩子冒險、探究。當然,人類的文化又強化了這一模式。即使在現代西方社會,一般家庭中大多還是父親在外面闖天下,母親在內理家照顧親人。孩子往往會順著父親的視野去看社會。因此,父親經常是孩子和外部世界的重要橋樑。
以孩子練琴為例。你觀察許多家庭就會發現,母親監督孩子練琴,孩子經常會撒嬌,拖延或乾脆拒絕練習。即使母親自己是個音樂家,也往往一籌莫展。父親監督,孩子則更多地集中精力工作。我們中國人往往把這種現象歸結於“嚴父慈母”的功能。其實未必如此。我們家的女兒從來不怕我。她學鋼琴從來都是媽媽帶著去,我等於是“圈外人”。但是,監督練琴,常常是我更有效率。女兒見了爸爸,本能的反應就是該工作了。見了媽媽,則擺出一副吃奶的小樣子沒完沒了地發嗲、貧嘴。
總之,孩子對父母的感情需要是不同的。父愛和父教,在塑造孩子的“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方面,恐怕比母愛、母教還重要。西方在女權運動之後,男女的角色確實有混同之趨勢。母親在外面忙,父親守家的例子也越來越多。但是,這種社會角色的混同,並不能取消進化過程為人類家庭設計的基本模式。懷孕、母乳餵養孩子的只能是母親。母親照顧孩子的基本物質需求,也是這種自然安排。父親扮演著更多的社會角色。通過這種社會角色,父親把一定的“社會期待”帶給了孩子。“爸爸期待我做一個什麼樣的人”,這種觀念在學前孩子的心靈中就根深蒂固。所以,父親在塑造孩子的價值觀念、人生目標等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是母親很難取代的。也只有當父親和孩子關係親密時,才能把自己的期待傳達給孩子,讓孩子的生活有個方向感。這比一天到晚督促孩子用功要重要得多。我和女兒的關係就是這樣。我其實是個很能“硬”得起來的父親,可以非常嚴厲,我經常告誡女兒工作時要有工作的樣子,不許跟我耍在媽媽那裡常耍的小孩子脾氣。但是,正是因為我不時地對她嚴厲,不管白天發生了什麼,睡覺時我總要守候在她身邊,保證她帶著無可置疑的父愛進入夢鄉。我不一味地反對“嚴父”,但“嚴父”的本錢是孩子對父愛的信心。我雖然從來不具體要求女兒成為什麼人,但她知道爸爸期待她有精彩的生活,能對社會作出卓越的貢獻。因此,她根本不用督促,每天課後能夠用功三四個小時甚至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