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可視錯覺與新的心理學
1910年仲夏,在一列從德國中部飛馳而過的火車上,一位名叫麥克斯·韋特海默(Max Wertheimer)的年輕心理學家遠眺窗外的風景。儘管電線桿、房舍和山頂是靜止不動的,可看起來卻似在與火車一起飛奔。
這是為什麼呢?
成千上萬的人都知道這是一個錯覺,也都視其為想當然,但韋特海默卻不這麼想,他認為這件事必須有個解釋。這個疑團使他聯想到另外一種錯覺運動——頻閃觀測儀。它的基本原理與電影差不多,作為一種玩具在當時非常流行。不管是電影還是萬花筒,都是一系列以幾分之一秒的時差所留存下來的照片或展示其最細微變化的畫面快速地在眼前通過,給人留下連續運動的印記。
幾十年來,這種現象廣為大家所知,卻從未有人給出過令人滿意的解釋。然而,就是在這輛火車上,剛剛在魏茨堡獲得博士學位的韋特海默突然直覺上意識到答案所在。他突然意識到,運動錯覺的成因可能並不發生在許多心理學家所認為的視網膜上,而是發生在意識深處,極有可能是某種高級的精神活動在連續的圖片之間提供出轉接,從而對運動產生了感知。
當時,韋特海默正在維也納大學就閱讀恐懼症進行研究,此番正要趕往萊因蘭度假。這一想法使他激動異常,於是他急不可待地在法蘭克福跳下列車,前去拜謁弗裡德裡奇·舒曼(Friedrich Schumann)教授。他是感知方面的專家,在去魏茨堡之前,韋特海默曾與其一道求學於柏林大學。
進城後,韋特海默去玩具店買了一隻頻閃觀測儀(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這是一種流行玩具,可以產生連續活動的印象)。這只頻閃觀測儀中有馬和小孩的圖片,如果控制好速度,就可看見馬在行走,還可看見小孩子在走路。韋特海默用紙片代替那些畫面,並在紙片的兩個位置上畫一些彼此平行的線條。他發現,用一種速度轉時,他先看到一根線條,然後才在另外的地方看到另一些線條;用另一種速度轉時,兩根線條則平行在一起;再換一種速度轉,有一根線條從一個位置移動至另一個位置。就這樣,他開始了一次具有歷史意義的實驗,一種全新的心理學理論即將產生。
第二天,韋特海默打電話給法蘭克福大學的舒曼,告訴他自己的猜想,徵詢他的看法。舒曼解釋不出所以然來,但同意讓韋特海默使用他的實驗室和設備,包括他親自設計的新型速讀訓練器。速讀訓練器可精確地控制頻閃觀測儀只能粗淺演示的實驗。
韋特海默需要一些志願者充當實驗的受試者,舒曼便找來自己的助手沃爾夫岡·苛勒(Wolfgang Kohler),苛勒又介紹來另一位助手庫爾特·考夫卡(Kurt Koffka)。他們兩個比韋特海默年紀要輕(他30歲,苛勒28歲,考夫卡24歲),但三人都對神經心理學中的新心理學派和馮特的門徒們所忽視的高級精神現象極有興趣。他們立即著手工作,此後成為終生的朋友和同事。
韋特海默沒成婚,還有一份額外收入——父親為布拉格一所商業學校的校長——因而可以隨心所欲地支配自己的時間。於是,他放棄了自己的度假計劃,在法蘭克福一待就是半年。他讓苛勒、考夫卡和考夫卡妻子充當受試人,進行一系列實驗。
按照在旅館裡所做的初期實驗模式,韋特海默的基本實驗是輪流投影一條3厘米長的水平線條和另一根在它下面的約2厘米長的線條。在投影速率較低時,他的受試者先看到一條線,然後是另一條線;速率較高時,兩條線可同時看到;速率中等時,一條線平滑地向下面的線條移動,然後又返回。
為變些花樣,韋特海默使用一根豎直的線條和一根水平的線條。速度剛好時,他的受試者可看到一條線以90度的角度來回運動。在另一個變換中,他使用了許多燈。如果速度恰好達到臨界點,那麼,看起來就像是只有一盞燈在移動一樣。他還使用了多根線條,並將之塗成不同的顏色,設計成不同的形狀。在每種情況下,它們都能製造出運動的錯覺。即使他將正在進行的事情告訴3位受試人,他們也無法對此視而不見。在其他許多種變換中,韋特海默都力圖排除此類現象是由眼睛運動或視網膜殘留而引起的可能。
他得出的結論是:運動錯覺的發生不是在感覺的水平上,不是在視網膜區,而是在感知中,在意識中。在這裡,由外面進入的、互不關聯的感覺被視作一種組織起來、具有自身意義的整體。韋特海默將這種總體感覺叫作格式塔,一個德語詞彙,原意為外形、形狀或配置,他在這裡用以表示被作為有意義的整體而感知到的一組感覺。
這樣看來,他花費數月所進行的工作似乎只是解釋了一個小小的錯覺。但在實際上,他和同事已埋下了心理學中格式塔學派的種子,它將形成一個運動,該運動將極大地豐富和擴大德國和美國的心理學內容。
第二節 思維的再發現
韋特海默的理論是,思維讓進入大腦的感覺有了結構和意義。這一認識顯然走出了行為主義心理學。格式塔心理學往往與格式塔療法相混淆,前者是一種心理學理論,後者是心理療法的技巧。
當時,自然科技正在迅速地改變著人們的生活與思想。電燈正在快速地改變城市甚或遙遠鄉鎮的夜生活,汽車也正在改變各個國家的習慣,飛機已可以進行長距離飛行,瑪麗·居裡剛剛分離出鐳和釙,盧瑟福(Rutherford)正在編製原子結構理論,齊柏林(Zeppelin)客運服務開始起步,黎·德·福裡斯特(Lee De Forest)的晶體管也剛剛申請到專利。新的心理學與這些發展相輔相成,心靈主義心理學則比以前更為形而上,更不科學,因而更像明日黃花。
心理學領域,其他研究者也不斷地提出證據,證明感知與視網膜或其他感官接受到的感覺並不一致,認為感知是思維對這些感覺中數據的解釋。
遠在1890年,奧地利心理學家克裡斯蒂安·馮·埃倫費爾斯(Christian von Ehrenfels)就已指出,當樂曲變調時,所有的音符都已改變,可我們聽到的卻是同一個旋律。因為我們辨識音樂是由思維而不是耳朵。
對心理學感興趣的醫生厄恩斯特·馬赫(Ernst March)於1897年說道:當我們從不同角度觀察一個圓圈時,它總是圓的,但在鏡頭上觀察時,它卻是橢圓的;當我們從不同角度觀察一張桌子時,視網膜上的圖像改變了,可我們在內心裡體會到的、看見過的桌子的經驗並沒有改變。思維在解釋感覺時將按自己所知道的目標形狀進行描述。
1906年,維托裡歐·本魯西(Vittorio Benussi)進行了著名的穆勒-裡爾錯覺實驗。實驗中,兩條線(如下圖所示的平行線條)在長度上看起來有所不同,而實際上它們是等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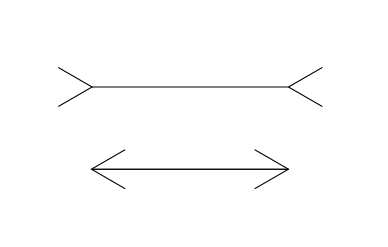
圖 1 穆勒 - 裡爾錯覺
他發現,即使他告訴受試者集中精力於平行的線條,他們還是無法使自己忽視整個圖形。他們可以減少錯覺,但不能消除錯覺。
韋特海默、考夫卡和苛勒在接受培訓時早已熟知了這些發現與概念。此後,三人都進行過包括較高級精神功能的研究:韋特海默研究過有閱讀障礙、思維遲鈍的孩子和病人的思維能力,考夫卡的博士論文是格式塔式節奏形態,苛勒研究的則是聲響心理學。
然而,這樣一個志趣截然不同的三人小組,乍看起來,還達不到徹底擊敗馮特心理學的智力水平。
在布拉格長大的韋特海默是個猶太人,長相頗具孩子氣,頭頂略禿,蓄一臉毛乎乎的、元帥般的大鬍子,但骨子裡有股詩人氣質,有音樂天賦,熱情,幽默,個性樂觀。他富有煽動力,當然也有口才,腦子裡總是閃現出新的念頭。然而,他非常不擅於寫作。
柏林人考夫卡只能稱得上半個猶太人。他個子矮小,身體瘦弱,瘦長的臉上寫滿嚴肅,性格內向而敏感,且極易動搖。但使人無法解釋的是,這些特點儘管使其上課乾巴得味同嚼蠟,卻對女學生極具吸引力。儘管他在講台上渾身都不自在,但在寫字檯上卻是游刃有餘,不斷地炮製出一系列格式塔心理學的學術報告。
苛勒則出生於愛沙尼亞,不是猶太人。他在德國的沃爾芬布特爾長大成人,臉上呈現出好鬥的表情,硬邦邦的短髮在中間分開。他是三人組中最刻苦的實驗者,後來到一所研究院工作,成為一個強有力的管理者。他高傲、古板,為人正派——對於結交10年的朋友,他才肯使用“你”來替代“您”——但在寫作中,他的文筆總是令人意外,感到既放鬆又使人著迷。
然而,三人性格及愛好的不同卻能使其各司其職,取長補短,從而結出難以意料的碩果。格式塔心理學史的一位研究者認為,韋特海默是“智慧之父、思想家和革新者”,考夫卡是“該組的銷售者”,而苛勒則是“內勤人員,干實事者”。
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格式塔心理學成為德國心理學的主要力量,也成為其他國家不斷成長中的心理學流派。但它對美國心理學的影響卻非常有限,且大多發生在1927年至1935年間,也即三人全部來到美國之後。儘管三人均沒有在美國心理學的機構中擔任要職,但他們的思想已漸漸地充斥於心理學之中,並發展壯大,直逼行為主義的營壘。
第三節 格式塔定律
從一開始起,韋特海默就認定格式塔理論並不僅限於對感知的解釋。他相信,它將能證明自己是學習、動機和思維的關鍵。
他的這些認識建立在自己的一些早期研究之上。他在法蘭克福就運動錯覺進行研究之後不久,受到維也納精神研究院兒童診所主任醫師的邀請,到那裡尋找對聾啞兒童的教育方法。他的實驗方法之一是,由自己搭建一座簡單的橋,橋上有3塊木板,建橋時,一位聾啞兒童看著,然後由他拆下來,再讓他試著搭建。通常情況下,犯過一至兩次小錯之後,他將學會並成功地搭建幾座不同形狀和大小的橋來。在韋特海默看來,孩子的思維並沒有建立在對演示中所使用的物品的數目和大小的感知之上,而是建立在對某個穩定的配置的感知之上,該配置即是格式塔。搭橋即是這種模式,兩個同樣長短的長條物水平定位在兩個終端。
韋特海默還閱讀人類學就原始部族的數字思維所做出的報告,並收集到一些數據。這些數據,外加他在法蘭克福所做的實驗,使他於1913年在一系列講座中勾畫出一種全新的心理學輪廓。他認為,格式塔並不是相關聯想物的累積,而是某種整體架構,因而要將事物看作一個有序的整體。
儘管韋特海默認為格式塔理論是整個心理學的基礎,但他的大部分研究,都是在應付感知問題。在十幾年的時間裡,3位著名的格式塔心理學家發現了一系列的感知原理,或被稱作“格式塔定律”。韋特海默總結了自己和他人的一些觀點,在1923年所發表的為數有限的幾篇論文中對若干主要定律一一命名,其中,最為重要的是下列幾條。
就近律:在觀察一系列類似物體時,我們傾向於以彼此距離較近的組或集對它們進行感知。韋特海默的簡單演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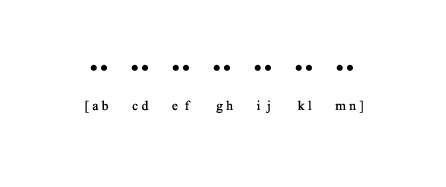
圖 2 就近律:簡單例子
他發現,給人們看一排黑點時,他們會自發地以彼此距離最近的黑點結對來看(ab/cd/……),但實際上,完全也可看作一對分隔較遠的黑點和分隔較近的黑點(a/bc/de/……)。然而,沒有人以這種方式去看,且大多數人無法使自己這樣來看。還有一個更具說服力的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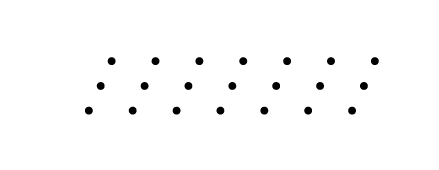
圖 3 就近律:極端例子
在這裡,我們看見由3個距離較近的黑點構成的一些線條,以豎直方向向右上傾斜。人們一般不會以另一種結構來看它,或就算以其他結構去看,也非常吃力——即由3個彼此分隔較遠的黑點構成的線條,以豎直方向向左上傾斜。
相似律:當相似和不相似的物體放在一起時,我們總將相似的物體看作一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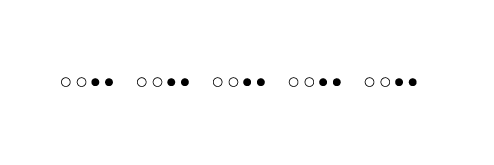
圖 4 相似律:簡單例子
相似因素實際上可以克服就近因素。在下面的左圖框裡,我們傾向於看見四組距離較近的物體;在右邊的圖框裡,我們傾向於看見兩組分佈在各處但相似的物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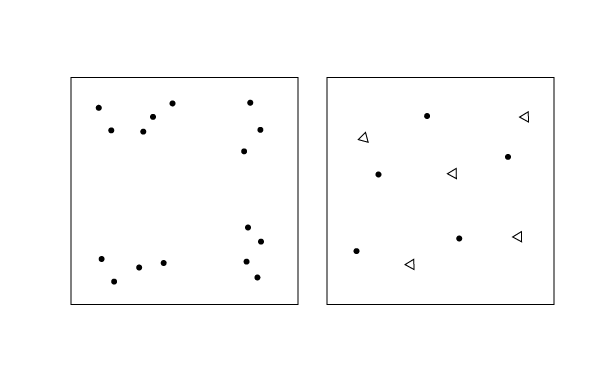
圖 5 相似律:複雜例子
方向的連續律:在許多模式中,我們傾向於看見一些有內在連續性或方向性的線條,我們可據此在令人迷惑的背景中找出有意義的形狀來,如平常所玩的“藏圖”遊戲。這樣的線條或形狀就是一個“非常不錯的格式塔”——內部具有連貫性或需求。例如,在下面這個例子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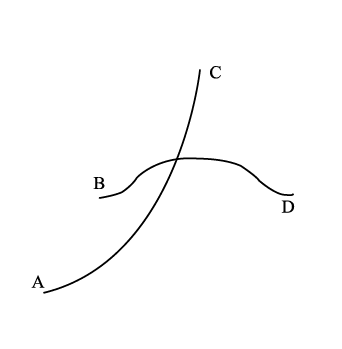
圖 6 連續率:兩條曲線呢,還是兩個有尖角的圖形?
我們只能強迫自己將其視為兩個彎曲的、有尖角的圖形,即AB和CD,但我們傾向於看到的是更為自然的格式塔形態,即兩條相交的曲線AC和BD。連續因素可構成相當驚人的力量。考慮下列圖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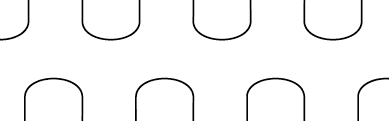
圖 7 兩個圖案,它們一樣嗎?
再看下面,前兩圖合併在一起就成這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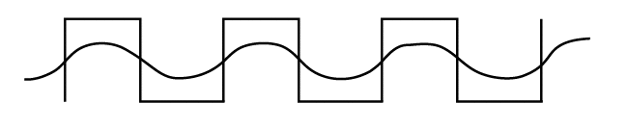
圖 8 相同的圖形,但就視覺上說,你能將其分開嗎?
在合併的圖中,幾乎不可能再看出原來的圖形,因為連續的波紋線已控制整個圖形。
求簡律:相關的英文詞是“懷孕”(pregnancy),但該詞並不能傳達韋特海默的意思,因為他所要表達的是“看見最簡單形狀的傾向”。正如自然法則使肥皂泡採取最簡單的可能形狀一樣,思維也傾向於在複雜的模式中看見最簡單的格式塔。如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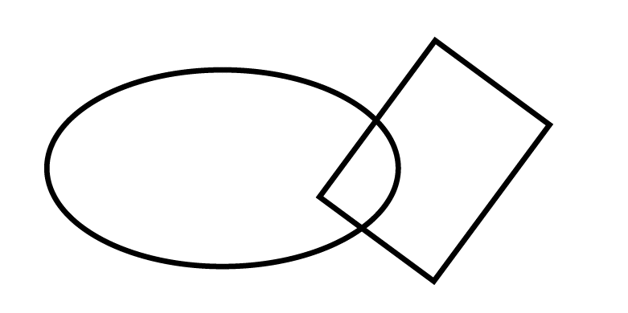
圖 9 求簡律:我們只看見最簡單的可能性形狀
該圖可解釋為一個被直角切去右邊的橢圓相接於一個被弧形切除一角的長方形。然而,這並不是我們所看到的。我們看到的要簡單得多,即一整個橢圓和一整個長方形互相重疊,僅此而已。
閉合律:這是求簡律的一個特別並且重要的案例。我們在看一個熟悉或連貫性的模式時,如果某個部分失去了,我們則會把它加上去,並以最簡單和最優秀的格式塔對它進行感知。比如,在下圖中,我們總是傾向於把它看作一顆五星,而不是五個構成此圖的V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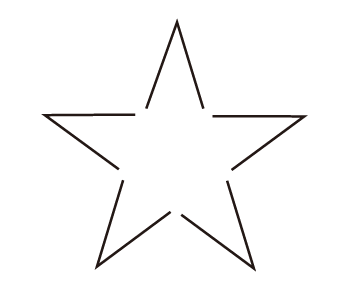
圖 10 閉合律:我們把缺失的部分補上去
20世紀20年代,格式塔心理學家庫爾特·盧因(Kurt Lewin)注意到,侍者能輕易記住尚未付款的客戶的賬單細節,而一旦付過之後,他就會立馬忘記。這使他想到,這是記憶和動機領域的一個閉合案例。只要交易沒完成,它就沒有閉合,因而可以引起張力,保持記憶。一旦閉合完成,張力即消除,記憶也就消失了。
盧因的學生,一位名叫布魯瑪·塞加尼克(Bluma Zeigarnik)的俄國心理學家,用一非常著名的實驗測試了老師的推想。她給志願者分配些簡單任務——做泥人、解決算術問題等一連串工作——很快又打斷他們,不使其完成任務。幾個小時後,她要求他們回憶所做的工作,結果發現,他們能清楚地記憶尚未完成的任務,而已經完成的任務,他們的記憶效果要低很多。這個效應被稱為“塞加尼克效應”。
圖形-背景感知:注意某物時,我們一般不注意或很少注意它的背景。我們看的是一張臉,不是臉後的房間或風景。1915年,古丁根大學心理學家埃德加·魯賓(Edgar Rubin)深入探討了圖形-背景現象,即大腦將注意力集中於有意義的圖案而忽略其他數據的能力。他使用許多測試圖案,最廣為人知的就是魯賓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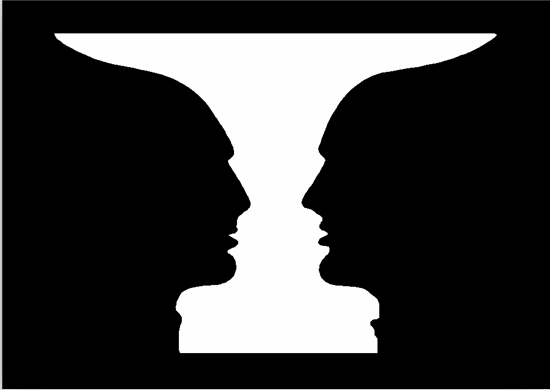
圖 11 魯賓瓶,是陶器還是剪影?
如果看到瓶子,你就看不到背景;如果看到背景——兩個人臉的剪影——你就看不見瓶子。
尺寸衡定律:一個已知尺寸的物體,拿到遠處去的話,會給視網膜留下較小的圖像,但我們感知到的卻是它的真實大小。我們是怎樣做到這一點的呢? 聯想主義者認為,我們是從經驗中得來的,格式塔學者卻發現這個解釋過於簡單。對雛雞加以訓練,使它們只啄大顆飼料。在該習慣完全形成之後,把較大顆的飼料放在遠處,使其看起來要小於近處的較小顆粒,小雞仍毫不猶豫地直奔遠處的大顆飼料。對11個月大的女嬰進行訓練(通過獎勵辦法),使她在兩個並列的盒子中選擇較大的盒子。把較大的盒子移至足夠遠的地方,使大盒子看起來很小,可嬰兒還是選擇遠處的那隻大盒子。
我們感到,遠處的物體與它們在近處同樣大小,因為大腦用相互關係——如鄰近的已知物體或可提供遠景的特性——的辦法組織了這些數據。圖12中的兩圖摘自最近的感知教科書,可對此進行說明。

圖 12 遠景可提供物體大小的線索
在左圖中,遠處的人與他身邊物體及與走道的相互關係可使我們將他視作與近處的人一樣大小。然而,在視網膜上,遠處那個人的圖像卻要小許多,如右圖所示。
第四節 夠不到的香蕉及其他難題
薩爾頓是一隻雄性猩猩,它整個上午什麼也沒有吃,已經餓極了。飼養員領著它來到一個房間,天花板上吊著一串香蕉,但它夠不到。薩爾頓朝著香蕉又躥又跳,接著,它開始在屋子裡打轉,發出不滿的吼聲。在離香蕉不遠的地上,它發現一根較短的木棍和一隻很大的木箱,它拿起棍子,試圖打下香蕉來,可依舊夠不著。有一陣子,它來回跳個不停,極為憤怒,突然,它直奔箱子,把它拖到香蕉底下,爬上去,輕輕一跳就拿到了獎品。
幾天之後再次實驗,香蕉被掛得更高,而且不再有棍子。所不同的是,屋內有兩隻箱子,一隻比另一隻稍大一些。薩爾頓自認為明白該做什麼,它把大箱子搬到香蕉底下,爬上去,蹲下來,似乎要跳起來。但它看看上面,並沒有跳,因為香蕉掛得太高了。它下來,抓住小箱子,拖住它滿屋子亂轉,同時憤怒地吼叫著,踢打著牆壁。顯然,它抓住第二隻箱子,並沒有想到要將其疊放在第一隻箱子上面,只是拿它出氣。
然而,它猛然停止叫喊,將較小的箱子直拖到另一隻箱子一邊,稍一用力,就將其放在大箱子之上,然後爬箱子,解決了香蕉難題。一直站在一邊進行觀察的沃爾夫岡·苛勒將這一切盡數記載下來,並表示了由衷的高興。
在1914年至1920年間,苛勒做了一系列的實驗對猩猩的智力進行研究。苛勒的發現直接導引出格式塔心理學家對人類解決難題的類似研究,並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發現。
苛勒在與韋特海默進行完運動的錯覺實驗之後,於26歲時,受命為普魯士科學院設在特裡萊夫的猩猩研究站站長。特裡萊夫是西班牙偏遠的屬地孔拉裡島的一部分。苛勒於1913年整裝出海,萬沒想到的是,此後發生的世界大戰和德國戰後的混亂竟將他困在島上長達6年之久。
在這期間,苛勒設立了許多不同的難題讓猩猩解決。最簡單的是繞道問題,猩猩得通過轉彎抹角的路徑以獲取香蕉。複雜一些的是使用工具,即猩猩得使用工具才能獲取掛在高處的香蕉。如棍子,猩猩可用它打下香蕉。再如梯子,它們可將它靠在牆上和箱子上。
有的猩猩需要較長時間才可看出箱子是用以獲取香蕉的,有的猩猩總是做些徒勞無益的事情,如把箱子碼在離香蕉很遠的地方,或碼得水平過差,待它爬上去時,箱子往往翻倒在地。另一些猩猩顯然要聰明一些,做得也很出色。它們學會以更安全的方式碼放箱子,即使要碼放兩隻以上的箱子才能取到香蕉。雌猩猩格蘭德甚至在需要時可使用4只箱子,雖然在碼放它們時頗費周折。
猩猩似乎能時不時地突然在某個節骨眼兒上想出解決問題的方法,苛勒解釋說,這是猩猩在腦海裡對形勢的重塑。他將這種突然的發現叫作“感悟”。
苛勒證明感悟是可以誘發的。苛勒常把一隻猩猩放在籠子裡,再把香蕉放在籠子外面它夠不到的地方。他在籠子裡放一些棍子,猩猩可能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不知道用棍子夠取食物,但可能在突然之間,它會想到這一點。一個叫謝果的雌猩猩先用手嘗試著抓取香蕉,半個小時後,它失去了信心,乾脆躺了下來。但另外幾隻猩猩出現在籠外時,它一下子跳了起來,抓住一根棍子,猛地把香蕉撥到跟前。顯然,其他猩猩接近食物對它起了促進作用,從而誘發出了她的感悟力。
苛勒還有一個對認知心理學意義重大的發現,那就是,感悟式學習不一定依靠獎勵。當然,猩猩一直在尋找獎勵,但其認知的結果並不是獎勵帶來的,因為它們在吃到食物之前就已解決了問題。
另一項重要的發現是,當動物得到某種感悟時,它們不僅知道解決問題的方法,而且還能概括並把稍加改變的方法應用到其他不同的情形之中。按照心理學的術語來說,感悟式學習能進行“積極傳遞”。按照一般人的說法,猩猩已學會應付各項考試。
苛勒在1917年的專論中報告了自己的發現,在1921年又出版了《類人猿的智力》。他的專著使心理學界大受震動,苛勒的觀察為格式塔心理學研究人類解決問題方法的能力鋪好了道路。
1928年,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的一位心理學家利用苛勒式方法對一些1歲半至4歲不等的孩子進行實驗。在實驗中,即使這些遠未成熟的孩子,其解決問題的能力也要遠遠高於成熟的猩猩。
類似的實驗還包括年齡更小的8個孩子,他們的年齡從8~13個月不等。這些實驗是稍晚的卡爾·登卡爾(Karl Duncker)做出的。登卡爾最重要的研究發生於1926年至1935年之間,主要研究成人受試者解決問題的能力。
登卡爾的其他主要研究方法是把受試者帶入一個房間,裡面堆滿一大堆亂七八糟的東西。他請受試者完成一項任務,而這些東西裡根本沒有一樣東西適合這項任務。該實驗的目的是測試受試者在什麼情況下能考慮常見的東西有其他的可能用途,又在什麼情況下不能考慮到。
實驗發現,解決問題者如果認定某物體具有專門用途,就很難看出它的其他用途。生活中也有這樣的例子,比如一些最熟悉自己所從事行當的人往往最不可能在自己的領域裡找到解決問題的新辦法。一位專家看其手中的工具時,看到的是各個工具的專業用途。一個生手儘管可能出些不著邊際的餿主意,但也往往能夠提出極有創見的新方法。毫不奇怪,科學家們往往是在早年提出其最有創見和重要見解的。
第五節 學習
格式塔心理學的最大貢獻之一,是有關學習方面的研究。
好玩的是,第一份證明聯想主義等學說存在嚴重不足的證據,是一隻母雞的思想。苛勒在特裡萊夫島時,曾對四隻雞進行過實驗。他讓其中兩隻雞啄食散落在一張淺灰色紙板上的米粒,當發現其啄食另一張深灰色紙板上的米粒時即將其趕走。同時,讓另外兩隻雞接受相反的訓練。大家都知道雞特別傻,但經過400~600次實驗之後,前兩隻雞便只啄淺灰色紙板上的米粒,而後兩隻雞也只啄深灰色紙板上的米粒。
接著,苛勒將兩種情形互換一下,讓雞學會吃食的那張紙板的背景顏色保持不變,但將另一張紙的色調調換。對前兩隻雞,調換成更淺的灰色,對後兩隻雞,則換成更深的灰色。聯想主義者可能得出預測,雞認準了紙板的顏色,只會在原來的紙板上吃東西。但在70%的實驗中,被訓練在較淺紙板上吃東西的母雞大多選擇新的、顏色更淺的背景,學會在較深背景上吃食的母雞則大多選擇新的、顏色更深的背景。格式塔學說提供的答案是:動物所學的不是兩種顏色,而是兩種顏色之間的關係。
苛勒在一隻猩猩和一個3歲幼童身上重複了這個實驗。他們兩個各得到兩隻箱子,一隻是暗色,一隻是亮色。當猩猩受試時,亮色箱子裡放著食物;當孩子受試時,亮色箱子裡面放著糖果。猩猩和孩子都知道亮色的箱子裡有獎品,但此時苛勒拿走了暗色的箱子,各用一隻比盛放獎品的箱子更亮的箱子替代之。這一次,他在兩隻箱子裡都放了獎品,這樣的話,除兩隻箱子的顏色不同外,沒有其他的激勵因素以供挑選。結果,猩猩和孩子通常選擇的都是新的箱子,即更亮的箱子。
但苛勒的實驗無一例外地證明,動物所學的不是兩種顏色,而是兩種顏色之間的關係。關係是感知、學習和記憶的關鍵。這個事實此前被排除在心理學之外,現在又由格式塔學者重新將其找了回來。
韋特海默、苛勒、考夫卡和他們的許多學生都對學習問題進行了探索,宣佈該觀點的許多功績卻大多歸在考夫卡名下。這位害羞、自疑、其貌不揚的小個子男人性格古怪,嗓門巨大,但當他坐在桌前編輯事實和學說時,卻總是心曠神怡,游刃有餘,文筆既有大師的氣度,又尖刻潑辣。
考夫卡本人並沒有進行過什麼值得注意的認知研究。然而,由於他的英語很好,1921年他接受《心理學快報》的邀請用英語講解格式塔心理學。自此之後,考夫卡就成為整個運動的非正式代言人。考夫卡的兩本書《思維的成長》和《格式塔心理學原理》讓格式塔心理學研究發現和有關學習的思想廣為人知。除此之外,考夫卡的理論也為記憶方面提出了一些有見解的思想。
第六節 失落與成功
在德國,如我們所見,格式塔心理學已成為20世紀20年代的領導學派。在其3位創立者及其學生相繼離開德國之後,格式塔心理學於30年代中期幾乎銷聲匿跡,重心轉向美國。考夫卡於1922年開始發表介紹性文章,之後,格式塔心理學漸漸引起人們的興趣,甚至激起了相當的熱情。
然而,當時的美國正在流行行為主義學說,行為主義已經成為美國心理學中最具影響力的學派,根本不給格式塔思想任何發展空間。而幾十年之後,格式塔心理學得到了眾多研究形式的強力確證。比如,對語言獲取能力的研究證明,兒童被教授語法之前就會按照語法說話。行為主義對格式塔心理學的反感也遭到報復,考夫卡、苛勒和韋特海默均對行為主義學說不屑一顧,並將自己的學說視作唯一有效的理論。
到30年代末,格式塔心理學雖已在美國心理學界紮下根來,但仍是二流。然而,他們對心理學的發展所做的貢獻,卻遠超出了其人數和位置的影響。
韋特海默熱情但沒有耐心,因而並不是個好老師。考夫卡枯燥無味且古板教條,卻頗受其所教書的史密斯大學女生的青睞,他所著的百科全書式的《格式塔心理學原理》一書對心理學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苛勒儘管擁有德國人的古板,卻是3個人中在傳統學術圈子裡混得最好的一個。他創立了一個心理學研究中心及一份獎學金,吸引來許多一流的博士生。苛勒於1958年退休,但一直積極從事研究工作,直到9年以後他年屆80歲為止。退休以後,他得到了美國心理學界的最高頌揚,並被選為美國心理學學會主席。
一個令人困惑的現象是,到20世紀中葉,儘管格式塔運動已失去地位並銷聲匿跡,但它的一些重要概念卻漸漸匯入心理學的主流,迄今仍然佔據重要地位。格式塔心理學的基礎教義,即整體——格式塔——重要於構成它的所有組件,並主宰我們的認知力,完全經受住了時間與實驗的雙重考驗,在感知、解惑和記憶領域仍發揮著作用。
更重要的是,格式塔學者把意識和意義重新帶入心理學,他們並沒有對馮特的信徒或行為主義者的發現造成損毀,只是極大地擴大了科學心理學的範圍和規模。如考夫卡所說:
我們並不是被迫從心理學和普遍意義的科學中廢棄諸如意義和價值這些概念,相反,我們必須利用這些概念以更全面地理解思維和這個世界。
1950年,已成為遙遠流派的格式塔心理學慢慢失去了影響,對此,艾德溫·波林用迄今仍無人超越的文筆對其命運小結如下:
學派可以沒落,也可因成功而消亡。有時,盛極必衰……(格式塔心理學)開創了許多重要的研究領域,但把它繼續標榜為格式塔心理學已不再具有益處。格式塔心理學的巔峰已經過去,現在已是盛極而衰,銷匿在心理學的海洋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