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精神生命力取決於他內心愛的活力——一個人心中的愛越誠摯,他的精神生命越堅韌;一個人心中的愛越廣闊,他的精神生命跨越的時空也就越廣闊。當一個人愛天下人,他的精神也就趨於不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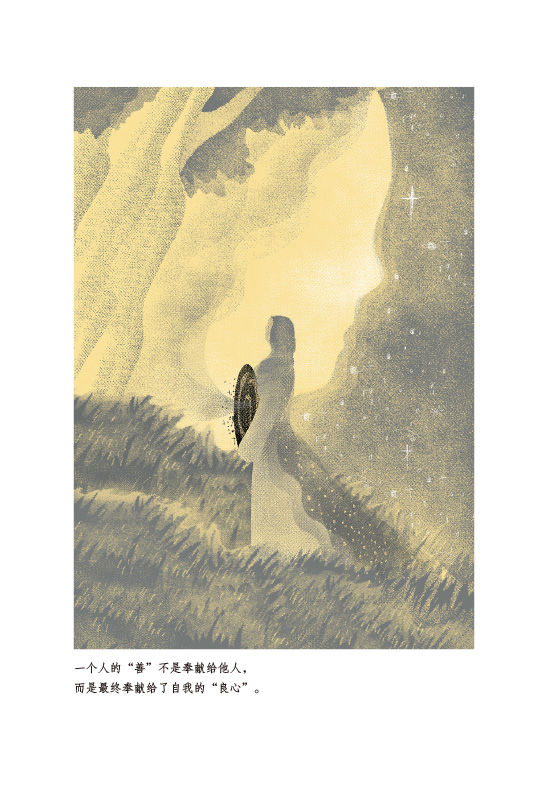
做一個「達」人
我們常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這本是自古至今中國傳統中稱頌讚譽的個人修養。但時至今日,當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用「獨善其身」一詞形容某人時,卻似乎抱有某種明顯的不滿,不但背離其原初的讚美之情,而且含有相當的批評之意。
誰說「獨善其身」不是善?
「獨善其身」絕非「不善」,更不是「惡」,其實它也是「善」,代表了一個人決不妥協的道德原則,是他無可退讓的「良心」底線。換言之,「獨善其身」是一個善良的人在自己最黑暗、最沉重的階段依舊在保守和堅持的「良知」。所謂「窮則獨善其身」,其中的「窮」類似於「窮途末路」的「窮」,指的是處境的窘迫、人生的失意、長久的不得志。「窮則獨善其身」意味著一個人即使在自己生活最沒落、最不如意、最艱難困苦的階段,也至少要潔身自好,絕不因受害而害人,絕不隨境遇失落而人格低賤,絕不為生活所迫而危及良知——雖處境無比糟糕、自顧不暇的「我」已無力造福於人,但至少還能問心無愧;雖自問無能於獲得「兼濟天下」的「助人之樂」,但至少還有「獨善其身」的「無虧之安」。
事實上,「窮」時的「獨善其身」意味著一個人無論境遇如何,始終保持自我人格的無害;不管是否受到他人卑鄙下作的毀傷,依舊堅持高潔的操守,不動害人之念;即使唯有同流合污才能換來生活之輕逸,卻不為所動、置身境外,執意保全自我靈魂的清白。
這樣的「獨善」固然不及「兼濟」之「廣利」,但究其實質,始終的「無害」何嘗不是一種長久的「兼濟」?在任何情況下,尤其是舉步維艱的逆境中,能堅持做一個對他人無害、對社會無害、對國家無害、對民族無害、對人類無害的人,何嘗不是一種難能可貴的「公益」?一個人能施以援手、救助他人,當然是美好的大愛,而一個人如果能長期在烏煙瘴氣中立於超然之境,對心胸狹隘之人懷有包容之心,何嘗不是一種「慈悲」?
或許,真正「兼濟天下」的「關懷」必須首先具有「獨善其身」的「清淨」,真正「兼濟天下」的「豪邁」不能離開「獨善其身」的「純粹」。記得1979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特蕾莎修女接受記者採訪時,記者問她:「我們能做些什麼來促進世界和平?」她的回答是:「回家,並且愛你的家庭。」
「獨善其身」與「兼濟天下」的完美融合
其實,「兼濟天下」與「獨善其身」不是兩種截然對立的人格,而是同一個人在不同的處境中,其內心的「真善美」從不同的側面折射而出的光輝。或者說,一個道德品質真正高尚的人,必然同時具備「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品行,而一個在「窮」時不知「獨善其身」的人,我們也不敢奢望他會在「達」時成為心存關愛、「兼濟天下」的善士,就像我們很難想像出有這樣一種「義人」,在富有的時候積極投身於慈善事業、終日以救助他人為己任,在窮困潦倒的時候卻會為了存活不擇手段、傷天害理。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只是說明了一個道理:一個真正善良的人,不論是貧困還是富裕、得意還是失意、窮途還是達境,他都不會心懷惡意、都不會傷害他人,他的善良不以環境優劣而改變,不因他人態度而轉折,他的「向善」「求善」、對「善」的忠誠持之以恆、矢志不渝。
而「獨善其身」和「兼濟天下」的差別僅在於——人生境遇的起伏跌宕,使其內心之善如浪裡行舟,若隱若現,隱時為「獨善其身」,顯時為「兼濟天下」。而那些在世人口中被一致稱頌為「兼濟天下」的高尚德行,對真正實踐它的人而言,或許只是出於一種微不足道的「獨善其身」,為的是日久年深的問心無愧;那些對眾生始終飽含深情的偉大心靈,我們以「聖人」之名加諸其身、以神聖的光環籠罩其一言一行,而他們看到的自己卻往往是一顆不夠堅強的心和一個平淡無奇的人;我們以為那是犧牲小我的大公無私,卻不知道那是「小我」與「大我」的合二為一,是在愛中自我與他者休戚與共的命運交織。
「達則兼濟天下」既是「公益」,也是「私善」,因為對於一顆博愛的心而言,我不在天下之外,天下亦常居我心中,又何來「獨善其身」與「兼濟天下」的格格不入?
特蕾莎修女題為《不管怎樣》的短小演說恰是「獨善其身」與「兼濟天下」的完美融合——
人們經常是不講道理的、沒有邏輯的和以自我為中心的,不管怎樣,你要原諒他們。
即使你是友善的,人們可能還是會說你自私和動機不良,不管怎樣,你還是要友善。
當你功成名就,你會有一些虛假的朋友,和一些真實的敵人,不管怎樣,你還是要取得成功。
即使你是誠實的和率直的,人們可能還是會欺騙你,不管怎樣,你還是要誠實和率直。
你多年來營造的東西,有人在一夜之間把它摧毀,不管怎樣,你還是要去營造。
如果你找到了平靜和幸福,他們可能會嫉妒你,不管怎樣,你還是要快樂。
你今天做的善事,人們往往明天就會忘記,不管怎樣,你還是要做善事。
即使把你最好的東西給了這個世界,也許這些東西永遠都不夠,不管怎樣,把你最好的東西給這個世界。
你看,說到底,它是你和上帝之間的事,而絕不是你和他人之間的事。
——你看,說到底,一個人的「善」不是奉獻給他人,而是最終奉獻給了自我的「良心」。
身心修養是做人的根本
南懷瑾先生曾說:「身心修養是做人的根本。」君子當務本而修身,一個人若修身到位,即使無力飛黃騰達、「兼濟天下」、造福於民,至少能夠修己正心、「獨善其身」、與人無害。我們應當努力使自己知書達理、耳聰目明、識時達務而成為一個真正的「達人」,以此「兼濟天下」,給他人帶去驚喜,並從他人驚喜的幸福中,收穫自我的驚喜與幸福,但生活無常,好景時有更變,當我們跌落失意或深陷困境,無力為他人帶去驚喜和幸福時,至少我們還能盡自己最後一點心力:不給他人帶去災難和痛苦。若不能「立人達人」,至少不「損人利己」。
身心的修養之所以重要,就是因為它能在我們的內心培植起一株精神的參天大樹,在盛夏繁榮之時,它茂盛蔥蘢的樹冠能為眾人提供陰涼,在嚴冬酷寒之際,它至少能維持自身不為強風所折、不被堅冰所鏤。能「兼濟天下」往往令我們精神振奮、情緒歡暢,「獨善其身」的清冷孤寂自然與之不可同日而語,但它至少能使我們對自己還抱有一絲敬意。在濁流中堅守「清者自清」的「自愛」,有時需要「敢與世界為敵」的勇氣,不論最終效果如何,這樣的勇氣本身已然是一股強大的心靈力量,業已為我們的人生不濟做出了一些補償:當世界不值得尊敬的時候,至少我們還可以尊敬自己。
寫到這裡,我想到了二戰中的德國哲學家雅斯貝斯,他的妻子是猶太人,面對當時納粹對猶太人的殘害,她終日深陷恐懼與絕望之中,雅斯貝斯本人也因為妻子的猶太人身份而遭到當局的迫害,這位德國著名的哲學教授隨即失去了工作,他的作品被全面禁止出版,連他最好的朋友哲學家海德格爾也選擇了置若罔聞、漠不關心。而當他的妻子表現出對長久生活的德國充滿仇恨時,雅斯貝斯卻說:「不要恨德國,你要愛德國,因為我就是德國。」當他的妻子不想連累丈夫的學術前途而主動要求丈夫放棄自己時,雅思貝斯卻選擇「站在妻子與世界之間」,以個人微弱的良心之光芒與無邊的黑暗相抗衡。
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兼濟天下」的人也好,「獨善其身」的人也好,他們都是「好人」,他們是同一個「善」在不同情況下的不同化身,就像神話故事《西遊記》中那位「大慈大悲」的觀音菩薩,能化身為世間形態萬千的各種形象,此刻是與人方便的少女,彼時是指點迷津的老翁……而萬變不離其宗的是一顆承載著「真善美」的良心。他們本是同一把琴上的不同琴弦,由同一支「善」的琴弓拉奏出不同的音色,時而輕細,時而激昂,但同樣優美、同樣高雅。
「獨善其身者」與「兼濟天下者」之間不存在根本的善惡道德之界限,唯一的差別只在於他們的處境不同,個人德性的影響範圍由此也就有了遠近深淺之分。
換言之,對於一個高尚的人而言,「窮」「達」僅是身外之境的變遷,而根深蒂固的是內心的道義,也就是孟子所說的「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兩者同樣可貴。
事實上,很多時候,「窮不失義」並不比「達不離道」更輕鬆,同樣,處境沒落時不求聞達的「獨善其身」並不比富貴顯達時樂善好施的「兼濟天下」更容易做到。仔細想來,一位心存大愛的慈善家,與一個一輩子克勤克儉、誠實待人的勞動者,似乎是同樣偉大的。
當一個人還能辨認出自己的「良心」,當他的「良心」還能認同並尊重他的舉止行動,那麼這或許還不是一個人最糟糕的處境。更糟糕的是,我們被黑暗攻克,摒棄了內心美好的信念,而不得不故作親熱地去擁抱我們發自內心鄙視的醜陋,不但為其鼓掌、讚美它,還要與之融為一體,成為它的附庸、隨從、幫兇;我們對自己不齒、對自己厭惡,不再覺得自己dear(可貴的、親愛的),不再熱愛自己,不再欣賞自己,不再尊敬自己。
當我們面對窮乏困頓的處境,我們的選擇不會像富貴達利時那麼多,到了那時,或許我們全力以赴所能做的,也僅僅只是阻止情況變得更糟。我們最後的底線或許就在於「獨善其身」,唯其如此,我們的內心至少還能留存一絲安慰、一絲驕傲、一絲自尊,此時如果我們捨棄了獨善其身,恐怕我們就真的什麼也沒有了。
大愛者,無惑
很多年以前,當我還是一名哲學系的本科生時,在西方哲學史的課上讀到了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的那句名言——「德性即知識」。由五個字排列而成的這一句話當時就隱隱約約對我的內心產生了一股不可名狀的衝擊力,我深信其中一定蘊藏著真理。
求善就是求真?
蘇格拉底為什麼會把「知識」和「德性」聯繫在一起?兩者之間如何能畫上一個等號?我們平常提到人類精神的至高境界時往往用「真、善、美」三個字加以概括,既然它們是三個字,而沒有用同一個字來表達,可見「真」必然不可能等同於「善」。毋庸置疑,在此,「知識」指向「求真」,「德性」指向「求善」,「求真」與「求善」在我們看來是兩個維度的東西,風馬牛不相及,那麼我們又該如何理解蘇格拉底所說的「求善即求真」?
無獨有偶,我們中國有著同樣悠久歷史的儒家經典《中庸》裡也有相似的論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意思是「有知識、仁愛、勇氣,是普遍通行天下的美德」。似乎也可以理解為,這三者是眾美德之本源,其他的很多美德由它們引申而來、派生而成。它們就像是「道德」這棵大樹的主幹,其他美德則是從主幹分叉延伸出去的枝繁葉茂。由此可見,即使在古老的東方文化中,「知識」與「美德」也是直接相關、不可割裂,而且「有知識」相對於其他很多美德而言,堪稱通達四方的「根本之德」、追本溯源的「大德」。但這個結論跟我們的實際生活經驗相去甚遠。現實生活中不勝枚舉的事實告訴我們,道德與學問不成正比,一個博聞廣識的人不見得就是一個明辨善惡的人,而一個斗字不識的農村老者很多時候倒有著一副大慈大悲的「菩薩心腸」。這麼看來,「知識淵博」與「人格高尚」根本上就不是一回事。
「知識是人對靈魂中的真理的回憶」
從蘇格拉底的學生柏拉圖那裡,我得到了支持這一結論的證據。對古希臘的這些哲學家而言,「知識」不是我們對外部世界的物質的認識,而是我們對潛伏在自我靈魂世界中的真理的回憶。在他們看來,我們在身體上、物質上是我們父母的孩子,而我們在精神上、靈魂上則都是真理的產兒,就像我們每一個人的身體基因裡埋藏著父輩母輩遺傳的密碼,同樣,我們每一個人靈魂的某處也與生俱來被打上了「真理」的印記。這也就意味著,蘇格拉底所說的「有知」不在於我們識多少字、懂多少國語言、看不看得懂股票的走勢、明不明白什麼叫文學,而在於我們能不能回憶起我們與真理的嫡系親緣,我們能不能摸到天賦的真理與我們的「良心」。因此,蘇格拉底所說的「無知」也不是我們口中的「文盲」,或者未曾受過良好的文化教育的人,而是那些遠離了靈魂中的真理、背棄了生而有之的良心的人。
換言之,在古希臘的思想傳統中,人類的「知識」可被區分為兩類——「生存的知識」和「生命的知識」,前者是一個人用來獲得物質、維持自身基本生存的知識,後者是一個人用來呵護精神、使生命健康美好的知識。「生存的知識」教給了我們謀生技能以及一些日常生活的人情世故;「生命的知識」則讓我們事理通達、心安理得、自由歡樂;「生存的知識」十分有用,卻冷冰冰,「生命的知識」看似無用,卻相當溫暖;「生存的知識」有一個別稱,叫「精明」,「生命的知識」也有一個別稱,叫「智慧」。
這後一種「知識」就是蘇格拉底所強調的「德性」,也是儒家經典中所指的那個「知」——達德之一。在《孟子·告子上》中,孟子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捨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他的意思是:從人天生的性情來說,都可以使之善良,這就是我說人性本善的意思。至於說有些人不善良,那不能歸罪於天生的資質不良。《詩經》說:「上天生育了人類,萬事萬物都有法則。老百姓掌握了這些法則,就會有崇高美好的品德。」同情心,人人都有;羞恥心,人人都有;恭敬心,人人都有;是非心,人人都有。同情心屬於仁;羞恥心屬於義;恭敬心屬於禮;是非心屬於智。這仁義禮智都不是由外在的因素加給我的,而是我本身固有的,只不過平時沒有關注它因而不覺得罷了。「探求就可以得到,放棄便會失去。」人與人之間有相差一倍、五倍甚至無數倍的,其實天資上的差別微弱,只是有的人清醒認識並充分發揮了這些天資,有的人糊里糊塗、渾渾噩噩、自暴自棄。
孟子認為,這「仁義禮智」四種「美德」,本來就在人的天性中,一個人後天要使自己成為有德之人,只需去探索追求那些先天被植入他天性之中的「善端」,它們就自然會像種子一樣生根發芽、開花結果,這與柏拉圖所說的「知識是人對靈魂中的真理的回憶」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厭世」,是「自厭」的蔓延
在蘇格拉底、柏拉圖、孔子、孟子這些偉大的思想者那裡,真正的「知識」只有一種——真理,只指向一個終極目標——善;真正的「知識」不教人如何成為優秀的律師、優秀的政客、優秀的金融家,而是教人「何以為人」、何以成為「好人」、何以成為一個「社會的良知」、何以成為一個優質的「人」;真正的「知識」超越了「生存的知識」,超越了謀生,超越了金錢和物質,它是「生命的知識」,教人獲得心靈的安寧和精神的歡樂。而蘇格拉底、柏拉圖、孔子、孟子,以及一切偉大的人,他們之所以偉大,不在於他們比我們更博學、更有見識、有更豐富的科學知識、更擅長生存之道,而在於他們比我們更有德性、更有胸懷、更懂得生命的真諦。
難怪孔子在《論語·子罕》中說:「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也就是說,一旦我們掌握了「生命的知識」,始終能明辨是非、區分好歹、看清善惡,那麼我們自然而然會去追求那些真正對我們善的、長久對我們好的、始終對我們而言是正確的事物,生活中又哪來那麼多難以決斷的選擇,又哪來什麼揮之不去的困惑?
如果我們仔細想想,就不難發現,生活中那些雞毛蒜皮的麻煩雖然令我們時時不快,但我們終究知道原因、明白其中的來龍去脈,即使一時解決不了,終究不足以構成我們彷徨無助的「困惑」。而那些真正能被我們稱為「困惑」的東西,駐留在我們的精神世界裡,有時讓我們覺得所做的一切都沒有意義;有時讓我們覺得內心空蕩蕩、那麼孤獨;有時我們走到哪裡、和誰在一起、吃什麼都只是無聊和乏味;有時我們發現無論做什麼事都不能使我們發自內心地快樂,我們變得什麼也不在乎、什麼也不愛……「困惑」對人的影響就像是一個人掉入了精神的「荒漠」、情感的「空洞」,四處縈繞而無可驅散,上下求索卻處處踩空,深受其擾卻無力擺脫。它對我們情緒的破壞力遠超過那些令人惱怒的雞零狗碎,後者會使我們情緒激動,甚至大發雷霆,前者卻使得我們沒情緒,對什麼都無精打采,只剩下對生活的深深的倦意與冷冷的漠然;後者激起我們的嬉笑怒罵,但那至少證明還有一股生氣、一種活力,前者卻讓我們瞥見了一個逐漸乾涸的自己,生命的汁液正慢慢地流失殆盡,無計可施。我們會發現這樣的「困惑」一旦纏上了我們,多少物質上的投入都無法解決,相反,更大的困擾就是不管多少錢、多高的地位、多奢華的享受,都換不來那生命的朝氣、內心的充實、精神的振奮、靈魂的安寧。
一切「厭世」,都是「自厭」的蔓延。「自厭」是「厭世」的起源。當一個人對自己失去興趣了,自然而然也就對一切都失去興趣了。
愛比生命本身更溫暖
如果我們靜下心來,去審視和探索一下那些能使我們自始至終興趣盎然的對象——那幾個我們願意花一輩子時間去瞭解和交往的人、某一項願意為之獻身的事業——我們就會發現他們有一個共同點:他們之所以能喚起我們持久的熱情、能激發我們全身心去奉獻,就是因為他們本身充滿了新鮮活躍的創造力,他們總在不斷地自我更新,如永不乾枯的源泉、如亙古常新的自然。與這樣的人為伴,或者投身於這樣的事業,我們不覺厭煩,我們孜孜不倦。
那麼,同樣的道理,如果我們不想對自己生厭、希望能對自己保持長久的興趣,毫無疑問,我們自己身上就必須有一些能夠始終吸引自己的、歷久彌新、永不衰竭的好東西。
什麼樣的東西能這樣曠日持久地散發光和熱,一旦我們擁有了它,就能分享它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能量?什麼樣的東西能馴服我們不知饜足的精神,使之長久安樂?——這不是「生存的知識」力所能及的問題,多少金塊堆砌出的璀璨耀眼也亮不過一個發自內心的微笑。關於生命的問題只有在「生命的知識」中才能找到答案,而能為生命源源不斷提供熱情的東西,一定比生命本身更溫暖。這世上還有什麼,能比心裡的愛更溫暖?
英國哲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羅素在談及他為何而生時,說出了這句舉世皆知的名言「有三種情感,單純而強烈,支配著我的一生:對愛情的渴望,對知識的追求,以及對人類苦難不可遏制的同情」——這支配他一生的情感就是「愛」:對真理的熱愛、對某一個人的深愛、對人類的博愛。
就像一朵花盛開了,它的芬芳會在空氣中瀰散一樣,一個人心中的愛會以某種類似熱能的方式傳導給他身處的空間和空間中的人。生活會因為這一團暖意而變得更溫柔可愛,而他對這樣的生活和生活中的自己也會萌生更多的喜悅和熱情。一朵花的香味越濃郁,飄散的地方就越遙遠。同樣,一個人心中的愛越充盈,這愛波及的人就越多,不僅能照亮他自己、惠及親人,還能由近及遠、推己及人,傳遞得更寬廣更久遠,被他的愛溫暖到的人也就更多更普遍——甚至是一些他所不知的陌生人,甚至是一些對他一無所知的後人。
一個人的精神生命力取決於他內心愛的活力——一個人心中的愛越誠摯,他的精神生命越堅韌;一個人心中的愛越廣闊,他的精神生命跨越的時空也就越廣闊。當一個人愛天下人,他的精神也就趨於不朽。這世上只有兩樣東西能讓人千秋萬代——思想與愛。而所謂「思想」,不過是對真理的大愛。
這裡所說的「由近及遠」「推己及人」的、像陽光般溫暖更多生命的大愛,不就是孟子推行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嗎?不就是孔子一生所倡導的「仁愛」,即儒家文化的核心嗎?
而這樣的「大愛」同時也是哲學家蘇格拉底為之獻身的生命意義。公元前399年,蘇格拉底被雅典法庭判處死刑,罪名是他不信神和腐蝕雅典青年的精神。事實上,他不但沒有毒害青年人的精神,反而是青年人精神的助產士;他不是不信神,而是不願意像當時絕大多數人那樣以無知和盲目去迷信神;他對希臘眾神不但沒有絲毫的褻瀆,反而對他們充滿虔誠的敬畏,他認為人類能用理性思考、用德性生活正是拜眾神所賜的恩典;他不但不是希臘城邦的破壞者,反而對希臘城邦飽含深沉的愛,他一生引導希臘的公民探求關於做人的「知識」,過有「德性」的生活。當時的希臘時局動盪、社會腐敗,蘇格拉底為之痛心疾首。於是他決心做一隻牛虻,用尖銳的理性鋒芒去蟄醒雅典這匹昏睡的純種馬,就像我們的魯迅先生用辛辣的文字敲打「鐵屋子」裡的中國人一樣。蘇格拉底獲罪於他的德性之善、理性之強,蘇格拉底的死源於他與眾不同的、對世人的大愛。
愛像一束光,照亮一切陰霾
「大愛」,對於蘇格拉底而言,或者在儒家聖賢那裡,既是情感,也是理性;既是純正的「美德」,也是最高的「知識」;既是至善,也是至真,同時也是至美。所以「德性即知識」不是蘇格拉底的隨口一說,而是他畢生的哲學精髓,他的一切知識都以「善」為根據,為「善」服務,追求更「善」的生活。
同時,只有「大愛」,能使人既寬厚仁慈,又剛正不阿。正是「大愛」成就了「仁」,又激發了「勇」。所以儒家的「知、仁、勇,天下之達德也」,說到底就是「三位一體」,植根於儒家的「仁愛」精神。
「德性即知識」「德性即大愛」,所以,在愛中,「真」「善」「美」融合為一。
愛,無惑——一個人的困惑就起於他不知何所愛,於是面對選擇常不知何去何從。當一個人心有所愛,愛之所指便是家園,那麼無論面對什麼誘惑,他都不會糾結,因為他走出的每一步只為「回家」。縱使這條回家之路艱難曲折,也甘願為之受難。愛像一束光,能照亮一切陰霾。我們的身邊注定時不時會出現絢麗多姿的流光溢彩,可與前方「家」中窗戶裡透出的暖暖的爐火相比,又算得了什麼?若一個人眼前常有家的遠景,他怎會迷路?若我們心頭常有愛的觀照,這一生又何來迷茫?
蘇格拉底被判處死刑之後,他的親友和弟子們都勸他逃往國外避難,那是多麼誘人的選擇,換誰不心動,卻遭到蘇格拉底的拒絕。最後他鎮定自若地當著弟子們的面飲鴆而亡。他並非不珍惜自己的生命,而是他願意將自己純潔而無辜的生命奉獻給他所熱愛的城邦,他願意為他執著信守的「德性」和「真理」殉道。與之相似的是「戊戌變法」失敗後英勇就義的「六君子」之一譚嗣同,當時日本使館曾派人與他聯繫,表示可以為他提供「保護」,他斷然回絕,並對來人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這兩個人有一個共同點:心中有愛——願為愛而生,也願為愛而死。即便是死,也不過是回家路上又進一步罷了。為愛而死,就是他們的活法、他們的生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