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在北京羊坊店派出所,我給我閨女辦戶口。
按說她那麼大點兒,有沒有戶口也無所謂,可是我覺得既然已經是個人兒了,就辦了吧。她出生之前我們商量過,一脫離母體,就是個社會人,不是我們倆的私有財產,我們當爹娘的,只不過是幫社會撫養她。
錄入姓名的時候,片兒警搗鼓了半天,問我:「系統裡只有『下圓點兒』,行嗎?」
我說:「同志,卡爾·馬克思的那個點兒,在下面還是在中間?在下面,那是兩個人,一個叫卡爾,一個叫馬克思。在中間,才是一個人。沒有就給我畫一個!」
戶口本拿到,姓名一欄寫著:法圖麥·李。
閨女大了,還不怨我一輩子?
很長時間以來,我認為孩子就是「第三者」,堅決不能要。
結婚以後,我和哈文恣意享受著二人世界。
宿舍裡從不開伙。白天在外面,下館子,哪兒好吃奔哪兒去,為餐飲業做了不少貢獻。晚上回來,想看錄像看錄像,想打牌打牌,想約朋友約朋友,想睡覺睡覺。
最大的愛好之一,是一人一個小馬扎,並排坐陽台上聽隔壁家兩口子吵架。說是吵,其實只有一個憤怒的女聲:「你放手!放手我就不打你!」摔碟子拌碗兒挺熱鬧。吵就吵唄,還動手?第二天一問,原來是男的跟食堂裡的服務員多說了兩句話。這位大哥還是CCTV的顧問,在家被老婆連顧帶問,日子過得沒我有滋味兒。
我們的生活,無拘無束,天馬行空。老覺著沒玩兒夠,共同抵制「第三者」,一抵制就是10年。
直到有一天,哈文特認真地跟我說:「你不覺得屋裡挺冷清嗎?」
「嗯?怎麼冷清了?不是玩兒挺好嗎?」我警惕地盯著她。
「要不,咱要個孩子?」
「哦……要孩子啊?」我撓撓頭,沉思半晌,最後橫下一條心。
「行,零件齊備,咱現在就搭流水線,製造開始!」
沒過多久,哈文告訴我:「有了。」
喲,挺快哈?機器好使!好傢伙,我奔超市,買果汁,買話梅,買酸奶,買一切孕婦愛吃的東西。買回來往哈文面前一堆,「老婆,可勁兒吃!」
兩天以後,哈文鬱悶地告訴我:「弄錯了,沒有。」
「我!」我挺窩火。
冷靜片刻,立馬兒又改了口,「老婆,不急,咱繼續製造。」
這麼折騰了好幾回,就連超市收銀員都一看見我就樂。
直到那一天,哈文說:「好像真的有了。」
「老婆大人,希望您端正態度,別老『詐和』,行嗎?」
結果,這次是真的。她樂了,我傻了。
太突然了吧?「來路不明」的第三者成功人侵,我們家得變成什麼樣啊?
2001年11月10日午夜,懷著說不清楚的心情——惶恐,期待,懺悔,都有點兒,我寫下了第一篇「寶寶日記」。
一個生命的孕育是那麼神奇。據說直到現在,許多大學問家也無法解釋清楚。人,真是個了不起的物種,真是和別的動物不同。因為人的後代會逐漸形成思想並思考問題,而且定會超過前人。
感歎之餘,我衷心感謝我的妻子,她給我這個機會,讓我能夠再次目擊自己的成長歷程。
除了愛,只剩下焦急的期待。
一開始寫,就停不下來了,期待是一天一天緊跟著腳兒的。每天,無論我在北京,在外地,睡覺前,還是路途中,我都會和小寶寶絮叨幾句。文章開頭千篇一律:「親愛的小寶貝,你好嗎?」

寶寶日記陪我度過漫長的期待
最初,多是抒發初為人父的焦慮、惶然,為自己這麼多年抵制他或她的到來而懺悔,就怕將來有一天他娘把不住嘴說出來。後來便成了流水賬。大到中東戰事,巴以紛爭,小到和哈文的一次口角,或春節前的家庭大掃除。甚至工作中的不順心也要講一講,譬如對長官有啥意見,有啥看法,今天誰氣著我了,替你爹記著他!
有時候在外地出差,睡不著,凌晨4點多還要寫上一篇。有時候寫了兩三篇都不過癮,後面還附一篇。有時候在家裡,晚上做完胎教,哈文先睡了,隔一會兒就叫我幫她翻個身。我等著伺候她老人家,又沒其他事做,也用寫日記來打發時間。每一篇都記著某月某日,幾點幾分,我怕這些事兒自己老了以後忘了。
寶寶的日記本是好友楊惠珊送的。楊惠珊曾是台灣電影「金馬獎」影后,二十多年前和丈夫共同建立「琉璃工坊」,投入中國現代琉璃藝術。在上海時,我常常光顧她的酒吧「透明思考」。
日記本裡印著很多琉璃工坊的工藝品照片。本來我就習慣豎排字,繁體,寫的時候還要特別小心繞開這些花兒。哈文一看就起急:「你費勁不費勁啊?」我笑瞇瞇地告訴她:「我不費勁。我幸福。」
我們住的單身宿舍只有11平米。一想到要當爹了,要養家,要給孩子盡可能好的生活,我就覺得肩上擔子挺沉。於是我開始拚命到外地演出,也就是「走穴」。哈文大著肚子,無數次在首都機場接我,送我。最慘的一次,我所有的現金、證件、銀行卡、演出稅單,還有哈文送我的錢包,都丟了。很辛苦,但是除了那個錢包,我都不介意。
和其他孕婦相比,哈文的肚子一直不算大,看上去尖尖的,胎心強勁有力。參考了方方面面的說法,對比各種數據指征,我們認為肚子裡是個男孩兒。小衣服小玩具,也都是按男孩兒準備的。我把寶寶的胎心錄下來了,沒事兒就趴在被窩裡聽,老覺得他在叫我。
有一天,例行B超檢查,男士止步。我跟婦產科主任和B超室主任都挺熟,就揣著DV混進去了,對著顯示屏一通亂拍。
醫院有規定,「禁止非醫學需要的胎兒性別鑒定」,不許告訴男孩兒女孩兒。可咱是「名人」啊,可以破回例。況且我信心十足,問,也不過就是證實一下。
我邊拍邊問:「是男孩兒吧?」

就我這張臉,扎倆小辮兒,那得什麼樣啊?
倆主任對著屏幕仔細研究了半天,回答:「閨女。」
「啥?閨女?」
我和哈文面面相覷,半天緩不過神兒來。
記得那是2002年3月20號,北京下了第一場沙塵暴,整個世界都是昏黃的。
回到家裡,我們一下午不說話,也不開手機,看著嬰兒床上那些藍色、黃色的小衣服發呆。
直到晚上天黑透了,我打開燈,扒拉一下哈文,「老婆,你看著我,看著我的臉。」
「看什麼呀?」她很不耐煩。
「你說就我這張臉,扎倆小辮兒,那得什麼樣兒啊?閨女長大了還不怨我一輩子?」
法圖麥,聖人的女兒
預產期是2002年5月29日。我說不行,提前剖!我疼我媳婦兒,不想讓她受罪。再說了,我的閨女,必須跟我一個星座,反正在肚子裡呆夠37周就熟了。
特無聊是吧?可是愛就這麼自私。而且對我來講,怎麼自私都不過分。
那一年5月21日出生的孩子就是雙子座了。不都說雙子花心嗎?我家閨女寧可像我,軸點兒,也別花!於是手術日期定在5月20日,當天打早頭一例。給哈文「掌刀」的是京城名醫金燕志大夫,人稱「金一刀」。
一大早我就趕到醫院。管停車場的師傅喜歡看我節目,專門給我留著車位。我在病房窗台上放了一隻小魚缸,裡面是送給閨女的兩條紅色小金魚。
可氣的是,所有護士都進去看李詠老婆生孩子,就不讓李詠本人進去!我站在手術室門口,乾著急沒辦法,只好把D V交給護士,囑咐她一定把我閨女出生的全過程都拍下來。
8點15分,我在手術知情同意書上簽字,實施麻醉。
手術室門框上方的紅燈亮了:手術中。我屏氣凝神,在心中數秒。祈求各路神仙菩薩,都來保佑她們母女平安。
15分鐘以後,突然聽見「哇」的一聲哭,尖尖的,細細的。老天爺,我閨女出來啦!嗓門兒夠亮的啊!可是只哭了幾聲又沒動靜了。
哦,估計給孩子洗澡呢,多乖啊,一聲不吭的。
我老婆咋樣啦?這會兒是醒著呢?睡著呢?
我在門口浮想聯翩,不停地看表。5分鐘過去了,10分鐘過去了,還不出來,想急死我啊!
正在這時,「嘩啦」一聲,手術室門開了。我下意識地來了個挺胸抬頭立正站好。
「女孩兒,6斤8兩!」一個小護士脆生生的聲音。
「砰!」門關上了。
我保持立正姿勢,回味著,陶醉著。多麼激動人心啊!我當爹了!
喲,沒給家裡報喜呢!我趕緊掏出手機給我娘打電話。
正低頭撥著號,「嘩啦」,門又開了。還是剛才那小護士,探出半拉腦袋說:「女孩兒,6斤4兩!」
「砰!」門又關上了。
我愣了一下,沖裡面大喊一嗓子:「那4兩哪兒去了?」

閨女是剖出來的,我疼我媳婦兒,怕她受罪。
後來看了錄像才知道,小傢伙太可愛了,稱體重的時候一直在尿尿。大夫直說:「寶貝兒別尿了,再尿咱還得稱一回。」更絕的是,剪臍帶的時候,她那一雙小手緊緊抓住大夫的剪刀,賊大勁兒,掰都掰不開。
又過了大約5分鐘,一位護士抱著我閨女出來了,她閉著眼睛,睡得挺香。我向每一位醫生、護士鞠躬,認識不認識都謝謝。
「謝謝您把孩子洗這麼乾淨。」
人家忍俊不禁,說:「還沒洗呢,剖腹產本來就挺乾淨的。」
走廊上堆滿了朋友送來的鮮花,聲勢浩大,一溜排開,得有二十多米。不敢放在房間裡,怕孩子花粉過敏。結果護士們個個都過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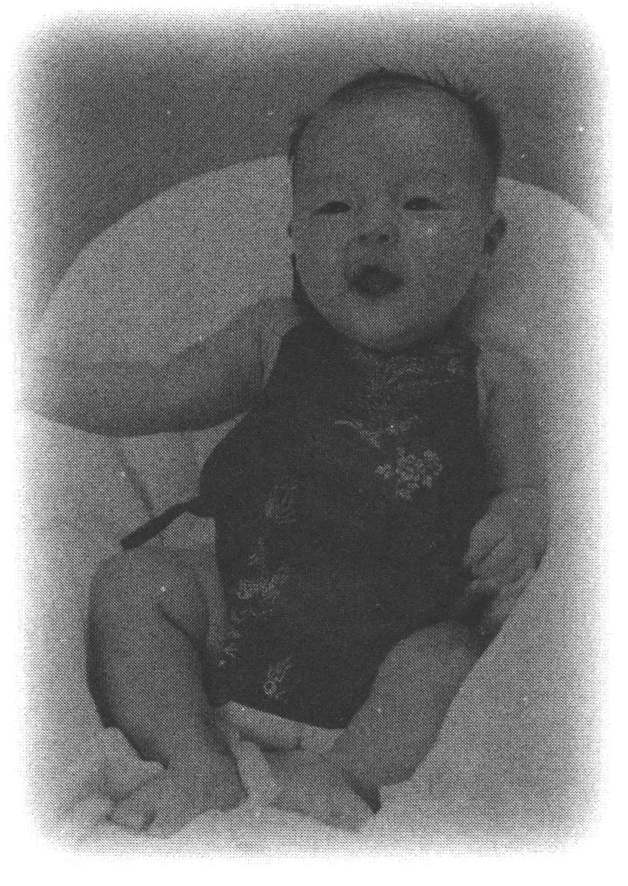
見到閨女,之前的一切疑慮全部打消。她,就是我想要的那一個!
我讓醫生先送孩子回房間,自己留下來等哈文。相濡以沫這麼多年,要是這會兒我只顧護著那個剛出世的小傢伙兒,也太不仗義了。老婆安全,才全家安全。
哈文精神很好,一點兒沒受罪。錄像顯示,當「金一刀」倒拎起孩子,「啪」一拍腳,「嘩」一擼臉,哭出聲後抱起來,放在她娘懷裡,讓她娘吻一下,哈文表情木然,完全沒找著當娘的感覺。她說:「太快了。」
陪哈文回到病房,望著她們一大一小,我的心像被什麼暖融融的東西緊緊地包裹住了,倆字:踏實。突然想到一個詞:大愛無疆。怎麼形容這種愛呢?它連邊兒都找不著,比無疆還無疆。
閨女真可愛啊,皮膚紅紅的,毛茸茸的。臉蛋比茶杯蓋兒大不了多少,小拳頭攥著,也就是個鵪鶉蛋。再比比小腳丫,還沒我小拇指長呢。
她長得多好看啊,小鼻子小嘴,就是眼睛還有點兒睜不開,睫毛也還沒長出來。她身上流著我的血,她就是我,我就是她。她笑我就笑,她疼我就疼。恍惚間,我彷彿看到了自己的重生過程。
我正趴小床邊全神貫注地看呢,「阿嚏!」小傢伙突然打個噴嚏,嚇我一跳。閨女,行啊!剛出來這麼會兒,打嗝放屁全無師自通啦!
中午,我把手機設置成免提狀態,接通了幾個清真大寺。按照穆斯林的習俗,電話那一端,大阿訇們誦起《古蘭經》,為我初生的閨女祈福。
閨女出生前,我們請過一位德高望重的阿訇為她取名字,個個寓意深遠,富貴吉祥。有「高人」指點我們說,閨女像她娘,陽氣足,挺倔,要選一個陰柔點兒的「壓一壓」。於是我們選了「法圖麥」這個女孩氣十足的名字。一個月以後,我偶識的另一位大阿訇才道出其中深意:法圖麥,就是聖人的女兒。
我倒吸一口冷氣:閨女,你這名字是真不賴。
愛,不是原因,而是結果
法圖麥像我,打從出生就懶。何以見得?
她娘奶漲得厲害,她小嘴吮不住,只好先用吸奶器吸,我再拿奶瓶餵給她。第一次給閨女餵奶,看到她嘟起小腮幫子起勁兒地吮吸奶嘴,一副很舒坦很滿足的樣子,我哭了。哈文後來告訴我,那段時間我莫名其妙總是流淚,頭回發現我挺多愁善感的。
奶瓶這東西好啊,不用吮,倒過來就往下滴。閨女躺在我胳膊彎裡,開始還猛嘬,後來發現了,不嘬也有,那就別受累了,張嘴等著吧。我就給她滴,她躺在下面挺愜意地吧唧嘴兒。
要不怎麼說青出於藍勝於藍呢?追求享樂和她爹如出一轍,悟性可比她爹高得多。享受了一回,第二回就知道了。隔了倆小時,又該餵奶了,我剛把她抱起來,奶瓶拿在手裡,人家直接把嘴張開等著了。
好,爹來給你滴!閨女面前,我就是沒原則,就是沒立場。
小孩兒出生頭幾天,一般就是吃了睡,睡了吃,很少睜眼。法圖麥不一樣。整個白天不睡覺,睜著眼睛到處看。醫學上講,新生兒視力很弱,只能看到很短的距離,也不知她整天整天地在尋摸什麼,倒是不哭不鬧的。
到晚上開始哭了,哭得那叫一個傷心,誰也哄不住,除了她老爹。
只要我把她往懷裡一抱,輕聲說:「小寶貝,我是你爹。」她立刻就安靜了,緊緊緊緊地貼在我懷裡,無比踏實。

對於成年人來講,自己的出生永遠是個謎,幻想的只有不可企及的童年。
哈文懷孕期間,每天晚上10點,只要我在家,一定準時進行胎教。開場白都是一樣的:「小寶貝,我是你爹。」她一聽見,馬上有反應。哈文的肚子開始起伏跌宕,這裡鼓一下,那裡鼓一下,看來玩得挺開心。
本來在那兒呆得挺好,愣被一下子提溜出來了,又亮又吵不說,剛出來就被打了好幾針,孩子能不委屈嗎?
三天以後,她周圍聲音太多,亂了。老爹的安撫也不靈了。鉚足了勁兒地哭,哭累了為止。
法圖麥降生以後,我的「寶寶日記」就寫不下去了。原因只有一個,我見到她了,了卻了「期待」,另一種全新的愛在心中蔓延開來。
閨女是爹前世的情人。我對她是看不夠,想不夠,疼不夠,愛不夠。她身上的味兒啊,比什麼香水都好聞,都親切。對我來說,從她在她娘肚子裡落腳,慢慢長大,到出生,成為我的親人,這個過程,彷彿與我和她娘從相識相知到執手偕老,如出一轍,沒有任何改變。我心裡只有深深的幸福,深深的感恩。
當了爹我才發現,心靈感應這回事,絕對是有的。記得法圖麥一歲的時候,我去外地出差,從出家門開始就莫名其妙覺得不舒服,有哪兒不對。
飛機落地後剛停穩,我就打開手機給家裡打電話,問閨女好不好,他們說:「沒事兒,忙你的吧。」
整整一白天,我都心神不定,怪了,從來沒有過啊。我又給家裡打了幾個電話,還是告訴我沒事兒。
第二天一早,我搭最早一班飛機趕回北京,到家一問,果然!小阿姨一眼沒看住,法圖麥在茶几上磕了一下,嘴唇被牙硌破了,流了不少血。
小阿姨一邊說,一邊抽抽搭搭哭起來。我大為光火,要不是她哭,我連動手打人的心都有。她當時也就是個20歲出頭的孩子,估計嚇得不輕。
現在想想,小孩子嘛,磕磕碰碰都正常。可哪個當爹的不護犢子啊?
法圖麥週歲生日那天,我們請了攝影師來為她拍照。在樓下的小區裡,攝影師讓我把她悠起來,像坐飛機一樣,「呼啦」飛起來,「呼啦」落下去,把她樂得啊。她一樂,我也有點兒得意忘形,再一飛,用力過猛,整個身子都歪過去了,基本上與地面呈45度角。
摔一傢伙是必然的了,關鍵是怎麼摔。說時遲那時快,我當即把整個胳膊都墊在閨女身子底下,選擇了一個她絕對安全的角度,轟然倒地。她沒事兒,我整個胳膊都劃爛了,那場面,慘不忍睹。
哈文在旁邊看著,來了一句:「嗯,你像個爹。」
我老婆不愧是。O型血啊,就這麼冷靜,完全沒有別人家老婆可能表現出的驚慌失措。說她是表揚你吧,話裡話外聽不出任何感情色彩。說她是挖苦你?也不是,這評價相當有高度了。
只能說,愛是裝不出來的。我就是她爹,而且是親爹!
人類基因真厲害。法圖麥不會爬,愛打岔,話癆,行動能力差,全是我的遺傳,不用教!
都說小孩子「三翻六坐,七撓八爬」,我這閨女什麼都會,就不會爬。哈文一度感到擔心,怕她是「發育遲緩」,我拍著胸脯向她打保票:
「看我!看你老公!有問題嗎?有毛病嗎?我小時候就先學走後學爬的,告訴你啊,沒事兒!老話說,不會爬的孩子聰明,知道嗎?」
我從小愛給大人打岔,爹娘經常警告我:「大人說話,小孩兒不許插嘴!」但我耐不住,不讓我說我難受。
現在,我閨女跟我一樣一樣的。有時候你說正事,她「光」地插一槓進來,聽上去還挺有禮貌,「我能發表一下我的意見嗎?」
「行,行,你發表。」急不得惱不得。
再有就是話密,天知道她的話怎麼那麼密。思維還倍兒跳躍,老得關注她的話頭兒在哪兒,一會兒就蹦了。她說話特早,早得我都害怕。八個月會叫爹娘,十個月能和大人簡單交流,一歲兩個月就自己唱卡拉OK了。
等她長到五歲,我們倆湊一塊兒逗貧,我就逗不過她了。越逗不過還越想逗,把她逗急了就這樣:
「法圖麥,你爹最大的特點是什麼?」我眉眼擠作一堆,諂媚地問。
「軸唄!」一臉的不屑。
「那,你覺得爹是什麼類型的人?」
她白眼一翻,「找抽型!」
到底是親爹,咋說我都沒脾氣。
逗她玩兒,實際上是給自己解悶兒。有時候我在書房工作,特別是錄節目之前,準備文案,一件特較勁的苦差事。我行動能力差呀,凡事能拖則拖,拖到不能拖為止。我可能會說服自己起個大早,沖完澡,狂喝幾杯咖啡,然後在書房裡坐下,看看書,看看盤,把整個白天都耗過去了,晚上才來開夜車,頭懸樑錐刺股!

「法圖麥,你爹是什麼類型的人?」「找抽型!」
法圖麥還添亂,在外面發出各種聲音。我在屋裡聽著,心裡癢癢啊。本來我就糾結得厲害:「我是出去呢?不出去呢?」

看不夠,想不夠,疼不夠,愛不夠。
琢磨半天,下定決心出去了,跟她逗會兒,跟家人聊會兒,又進書房。
剛坐定要幹活兒,她又弄出響動了,我又開始掙扎:「我是出去呢?不出去呢?」
這麼著,一天就過去了。
晚上哈文下班回來,我問她:「你說我這樣對不對?」
還沒等她開口,我自己回答:「我覺得是對的。」
然後,輕手輕腳溜到法圖麥的臥室裡,去和她道晚安。
「哎呀,爸爸你又來啦!真煩真煩真煩!」
「不許煩,過來!」
我把閨女摟懷裡,親額頭,親鼻尖,親嘴唇,親下巴,親脖子,親左臉蛋,親右臉蛋,一共七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