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精神若找不到可以長久安頓的「家園」,也就談不上「歸屬感」,那人生只是一次漫無目的的漂泊,看似四海為家,其實無家可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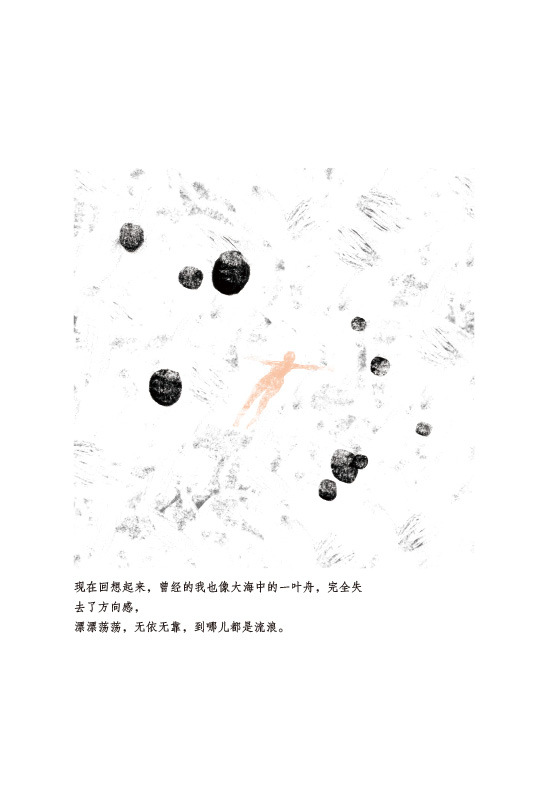
怎樣的人生才算成功?
我為什麼而活?
有一個朋友,多年前的一天將近凌晨的時候,我接到他的電話,電話中他的聲音明顯有種並不多見的憂傷。他說他輾轉反側、難以入睡,乾脆就起床在陽台上站一會兒。眼前黑暗中的一切景物都是他再熟悉不過的,閉著眼睛也能分毫不差地說出那些圓樓頂、方樓頂的具體位置。他覺得那會兒四周黑魆魆的寧靜應當有助於醞釀睡意。可事與願違。不知道為什麼,那天的他只是覺得一切離他那麼遠,所有的黑影看起來都是那樣的空洞。他突然問我:「這個世界到底跟我有什麼關係?我究竟是為了什麼活著?」
我的朋友感到有種難以名狀的害怕,於是逃也似的躲進房間,可是那種陌生感、疏遠感卻並沒有被他鎖在陽台門外,而是陰魂不散地緊跟著他,瀰散在房間的每一個角落,籠罩於每一樣物件之上。「房間裡什麼都不缺,可我為什麼覺得自己一無所有?有什麼東西是真正屬於我的?」他問我,可我覺得那更像是一句自言自語。
在我們這些普通人眼中,他算得上一個不大不小的「成功人士」,相貌堂堂,性格開朗,有房有車,工作穩定,收入可觀,時不時會在歐洲某一個怡人的海邊小鎮出現,然後安逸地小住數日。可他卻依然感到「一無所有」。
的確,隨著對哲學研究的深入,當發現一直以來心嚮往之的「成功」——比如聲望、財富、地位——所具有的魅力在我眼中逐漸淡褪時,我也曾陷入對生命意義的沉思。
我所經歷過的最接近「痛苦」的感受,大概就是那個階段——由於找不到自己「安身立命」的根基,我越來越感覺寸步難行。如果自己不確定想走的路在何方,那麼怎麼走都是歧路;如果辨不清哪裡是人生的目標,又談何「前進」或「後退」?現在回想起來,曾經的我也像大海中的一葉舟,完全失去了方向感,漂漂蕩蕩,無依無靠,到哪兒都是流浪。同樣的,人的精神若找不到可以長久安頓的「家園」,也就談不上「歸屬感」,那人生只是一次漫無目的的漂泊,看似四海為家,其實無家可歸。
我的朋友那一晚困頓之下提出的問題一如多年前我自己所遭遇的困擾。我很高興他當時通電話的人是我,但我貧乏的人生經驗就像一個簡陋的工具箱,很難翻出什麼工具來為他人鬆一鬆「心結」。我依稀記得我聽他傾訴了許久,自己也分享了一些心得。印象較深的是,我對他說「不是世界離你遠了,是你離自己的心遠了」。
「自我錯位」:其實我不懂我的心
我的一個學弟也算一位青年才俊,他十分勤奮,也不乏吃苦耐勞的精神,所以陞遷得很快。之後他兩年的時間裡跳槽兩次,收入翻了兩番。有一次,他給我的手機發來了這麼一條短信,「如果讓你選擇:A是現在的生活,B是做一個月為所欲為的國王,你可以實現任何夢想,無論多麼不靠譜,但是一個月之後你必須去死。你怎麼選?」我認真地想了想,回復給他:「我選A。你選的是B吧?」他沒有立刻回答我,其實也沒必要回答。我覺得所有面對這樣的選擇題有過糾結的人,已經明白無誤地選擇了B。過了幾天,他又發來一個短信「看來,我還是沒有找到自己的位置」。——果然,他還是那個我所認識的擅長自醫自救的人。他說的「位置」,就是自我定位;他說的「沒找到自己的位置」,就是他針對「自己不滿意現在的生活」這一症狀而得出的診斷結果:「自我」不安於現在的「位置」,「自我」出現了「錯位」。
我們或許還記得,年輕時常抱怨父母不理解我們的心聲,不懂我們的心志,卻一心將我們推上他們精心篩選的「人生軌道」,把他們為我們構想的「美好」前程強加給我們,要我們按照那樣的藍圖自我定位。比如我身邊的一個熱衷於繪畫攝影的女孩,被父親逼迫著年復一年參加司法考試。我們知道這是他們為我們「定錯了位」,因為那不是我們內心真正渴望的人生,那不符合我們對自己的定位。所以,當他人不瞭解我們的內心時,他們就很可能會給我們定錯位。同樣,當我們不真正讀懂自己的內心時,我們也會在生活中定錯自己的位置,這時就出現了「自我錯位」。
說到底,他的困擾和前面那個朋友的問題,如出一轍——當一個人與他的心疏遠了,心也就認不出他來了。當我們生活富足、衣食無憂,別人會羨慕我們;當我們功成名就、身居高位,別人會懼怕我們、巴結我們;當我們成為社會公認的「成功人士」,大家都對我們微笑、稱讚我們。可是,即使全世界都覺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就真的幸福嗎?如果我的心不認識我了,如果我所做的一切,都不能引起我內心由衷的歡樂和溫暖,我的幸福又該去何處找?
你說的「成功」,是「成就外功」還是「成就內功」?
一個比我年長的朋友曾與我分享他的一段見聞。他每天早晨要去一個路邊攤吃豆漿油條,倒不是因為有多麼百吃不厭,而是因為他特別喜歡賣豆漿油條的那一對小夫妻,一個炸油條,一個盛豆漿、擦桌子。一來一往之間,兩人常常相視一笑。不言不語,卻心照不宣,令他深受感動,忍不住感歎:他們活得多有意思!比我成功多了!
他說的「成功」,到底指的是什麼?
我們不妨從「成功」二字最膚淺的字面意思來考察。毫無疑問,「成功」當屬於真正的「有功者」,唯有真正「下功夫的人」才配得上享受「成功」。那麼如何來定義「功」?
我小學時最喜歡的枕邊書就是金庸、古龍或者梁羽生寫的武俠小說。雖然對「功夫」至今一竅不通,但至少有這麼一個粗淺的印象:「功夫」並不簡單,可分為「外功」與「內功」。初入江湖、舞刀弄槍的俠客們往往努力修煉外功,以此「成就外功」;而真正的武林高手和那些深藏不露的武學泰斗卻格外注重修煉內功,因為唯其如此,才能「成就內功」。換言之,武俠書裡那些江湖中的「成功人士」大致可粗略地分成兩種類型:要麼成就外功,要麼成就內功,姑且不論兩者間是否存在什麼內在聯繫。
基於對生活的觀察和思考,我覺得現在的「成功」仍可分為「成就外功」和「成就內功」。或許現代的江湖,與古老的江湖,總體而言,大同小異;此時的「成功」與彼時的「成功」也不無可比照之處。畢竟,我們每天見到的這個太陽、這個月亮,也正是在那個遙遠的年代,我們的祖先所看到的同一個太陽、同一個月亮,即使斗轉星移、物是人非,有些東西照舊萬古不變。正如英國偵探小說系列《馬普爾小姐》中那位主人公馬普爾小姐一邊織著毛衣、一邊若有所思地說:「過去或現在,人性總是相通的。」這或許就是中國哲學裡所稱的「人的本心」——洗盡鉛華後最樸素的那顆赤子之心。
那麼,若「成功」可分為「成就外功」和「成就內功」,「外功」與「內功」應該如何定義?各自的評判標準又是什麼呢?
所謂「成就外功」,其評判依據自然是「外在的標準」,即「外在於我的東西」。「外在於我的東西」有很多,大致可分成兩類,一類與我無關,比如天地山河,比如風霜雨雪,比如別人的生活;另一類與我相關,是「我所擁有的東西(What do I have)」。這兩者當中,當然只有後者關乎我的「成功」。換言之,我們評判一個人是否「成功」,外在的標準是看他擁有什麼。一般而言,一個人所擁有的東西越多,在旁人眼中他就越成功。
在我們擁有的所有東西中,最彰顯於外的就是那些我們看得見摸得著的、有形的東西,一般是物質的東西,比如房子、車子、錢、名牌服飾、昂貴的首飾、堆積成山的山珍海味;其次便是那些看似無形、卻能用來交換有形之物的東西,比如存款、利潤、股份等。這些東西通常被我們稱為「功利」。當然,如果一個人主要憑借一己之力能擁有這些功利的好東西,必有過人之處,要麼特別勤奮踏實,要麼智商極高,要麼運氣極佳,這的確是一種無可爭議的「成功」。普遍而言,我們的社會對「成功」的評判標準十分接近這一種——以「功利」論成敗。不可否認,確有其合理性。
除了這些有形的、物質的東西,還有另一類東西,也是我們能擁有的。它不能為我們直接帶來物質享受,卻比物質享受更溫暖一些、更有內涵和親和力。通常我們稱之為「修養」。修養包括「修身」與「養性」兩個方面。「修身」作用於「身體」,體現為我們擁有健康的體格、勻稱的體型、姣好的容貌;「養性」作用於「性情」,指的是我們擁有良好的氣質、翩翩的風度、友善的態度。一個人若擁有健康的體格,即使他不名一文,不能享受奢侈消費的快感,但他有健步如飛的自由;一個人若擁有翩翩的風度,縱是一介草民,不具「號令天下」的權威,卻能時時討人歡喜、處處受人欣賞,飽受讚譽。按照美國作家愛默生的說法,「風度是一種力量」,也是一張最獨一無二的個性名片。
擁有這些東西的人,當然在另一種意義上成就了他們的「外功」。他們何嘗不是「成功人士」?只是,很多時候「修養」這種東西顯得十分低調、不易察覺,所以當大眾討論到「成功」標準時常常將它忽略。但是,如果我們看看當前社會大眾趨之若鶩的種種風尚:人們一擲千金、購買昂貴的健身卡來強健自己的體質,參加五花八門的舞蹈課、瑜伽班來塑造自己的形體,用護膚品、去美容院來保養自己的面容,報名各種各樣的情商課、國學班來提升自己的氣質、培養自己的儀表風度,就足以見得大家其實在不知不覺中,已然發自內心將「修身養性」作為了一種值得追求的「成功」。
以上羅列的「成功」,不論是「功利之功」還是「修養之功」,我都將它歸為「成就外功」。當然,後者遠比前者更貼近我們的內在,不過,兩者有一個共性:它們或多或少是可以用錢「買」來的。另一個更為本質的共同點則是:雖然我們能擁有它們,但是它們並不真正屬於我們,我們無法永遠佔有,我們注定會失去。
這該怎麼理解呢?我嘗試借用英文的語法來解釋這個問題,希望這樣能使我自己理順,也使人易於理解:在英文中,這些我們能擁有、能佔有、能稱之為what I have的東西,都是有一天我們會失去的東西。要知道「to have(擁有)」與「to lose(失去)」是一對雙胞胎,從來相生相伴。
比如功利層面說到的權勢、金錢、財富——從長遠來看,它們始終在人與人之間川流不息,永不常駐。權勢從來都是從這個人流向下一個人,從這一朝輪轉到另一朝,人們今天上任,明天卸任,權勢卻一直虛位以待,它不屬於任何一個朝代,更不屬於任何一個人。金錢的流動速度更是驚人,從西方流到東方,從這個市場湧向那個市場,從這個人口袋裡平移到那個人銀行賬戶上,它就像作曲家比才筆下極具魅力的女子「卡門」,人人都愛她,她也不拒絕所有人,但她從不屬於任何人。
雖然第二層面談到的那些我們能擁有的東西,看起來與我們關係極為密切,比如「美貌」「強壯」「氣質」,好像它們是真正屬於我們的東西,即使他人羨慕嫉妒恨,終究無可奈何,這一點與功利層面的那些東西大不相同,顯得實在了許多。可是,我們在自信的同時,卻忘掉了這樣一個事實:別人拿不走的,時間統統能帶走。不論我們是否意識到、是否願意,時間幾乎能無情地捲走一切,包括你和我,哪怕現在的你很美,此刻的我很健康,但「驍將漸衰,美人易老」,世上最憂傷的事莫過於此。這些東西看似屬於我們,其實是我們從時間那裡借來的,只有一定年限的使用權,卻從來沒有所有權。
由此,我們或許能更理解上文所說的:那些我們能擁有、能佔有、能have的東西,不會在我們身上常駐,它們終究不屬於我們,終究會流逝。基於此,它們是「外在於我們的東西」。
那麼究竟什麼是「內在於我們的東西」?那些真正屬於我們,能常駐而永不流逝的東西?有這樣的東西嗎?它們會是些什麼呢?
德國哲學家叔本華在談論人的本質時,為人區分了三個不同層次。最外層是「我在他人那裡是什麼評價(What do I look like in other people's eyes)」。這一層最為普遍,是絕大多數人最常關心的問題,即「別人覺得我怎麼樣?」「他們覺得我美嗎?」「在他人看來,我幸福嗎?」——用我們東方人的「面子」二字便可一言以蔽之。在這一層次,與其說我們關心自己的感受,不如說我們在乎的是外界的評價。
中間的層次是「我擁有什麼(What do I have)」。我們前面對它已經說了很多。這一層次上的我們將關注點集中於自己的實際所有。
最內層是「我是誰(Who am I)」。探入到這個層次的人相對而言最少,只因它埋得太深,能給出答案的人在人類歷史上鳳毛麟角。即使說它是一切智慧的起源,也不為過。我們知道兩千年前在古希臘德爾菲神廟的石柱上就鐫刻著這樣一句神秘的箴言,像是一個神諭,或是一個咒語:人啊,認識你自己——由此開啟了古希臘輝煌燦爛的哲學世界。
到達「我是誰」這一層的人,追問的是自己的本質,那是一些看起來不清不楚卻至關重要的東西:即我的心靈、我的精神、我的靈魂、我的人格。一個學生問過我一個很有趣的問題:「老師,怎麼才能有人格魅力?」我想了想,回答:「很多人看到『人格魅力』四個字,關注的是『魅力』,而忽略了『人格』,這是本末倒置。實際上,人格魅力,根本在人格——一個人的人格有多高,決定了其魅力有多大。前者是因,後者是果,因果必然。」這一層次上那些看不見摸不著、玄之又玄的東西,幾乎決定了我們看得見摸得著的一切。而且它們超出了時間的掌控力,即使死亡也無力剝奪。我還記得回答這個問題時的最後一句話:「人格力量超越時空。即使有一天,人不在了,人格還在,魅力還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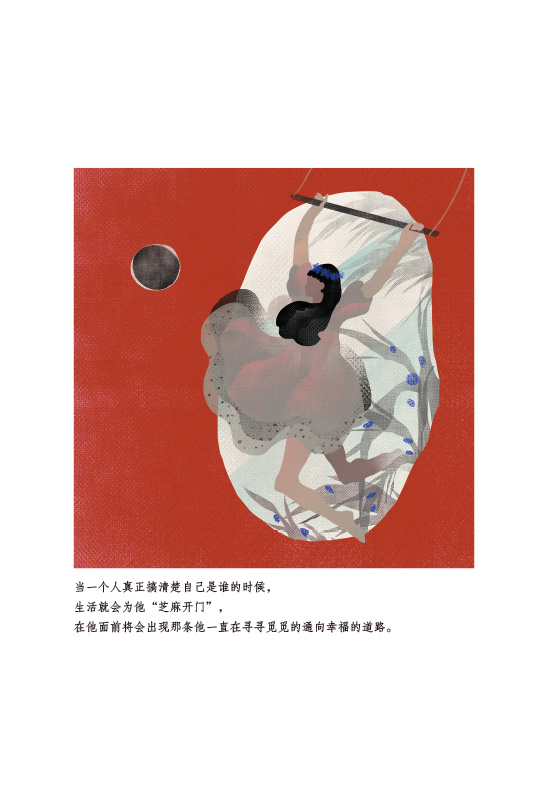
最高的成功,莫過於內心的幸福
有關「人」的問題數以億計,不論我們從其中的哪一點出發,最終總會指向「我是誰」,就像「條條大路通羅馬」。一個人只有知道了「我是誰」「我是個什麼樣的人」,才可能知道「我該往何處去」。「我是誰」是人生拋給每個人的謎團,外人回答不了,慾望越攪越亂,只有真正瞭解自己內心的人才能揭開謎底,活出自己。而當一個人真正搞清楚自己是誰的時候,生活就會為他「芝麻開門」,在他面前將會出現那條他一直在尋尋覓覓的通向幸福的道路。這裡的「芝麻開門」,平時我們稱之為「覺悟」。
「我是誰」,這就是那個真正「內在於我們的東西」,它決定了我們的心靈、精神、靈魂、人格,它們真正屬於我們,常駐而永不流逝。別人拿不走它,因為它深深地流淌在我們的血液裡,瀰漫於我們週身,逗留在我們的凝視中;時間也無法捲走它,因為「心靈永遠不會有皺紋」6。那是一種神聖的幸福。就算沒有財富,他可以憑著自己的德性而幸福,像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阿爾伯特·史懷哲博士,他主動放棄了殷實富裕的生活投身於非洲的醫療救助,長達50年;就算失去自由,他可以為人格的完整而深感幸福,像南非前總統曼德拉,被囚禁27年卻依然笑容可掬、熱愛生活;就算面對死亡,他可以因為此生大節無虧而幸福地離開,像孔子臨終前反觀一生,自覺可安然去也。「幸福顯然就是一件最神聖的事情」7,因為它來自心靈的確認與熱愛。實現了這樣的幸福,也就真正成就了最高的「內功」。
「功利之盛」能壓倒人,「修養之美」能愉悅人,「靈魂之高貴」能拯救人。「內功」是「成功」的精髓,唯有它能使人發現並創造幸福。我相信,真正的「成功」必然內含著「幸福」,而人生最高的「成功」莫過於「內心的幸福」!
當然人各有志,對每個人而言,各自心目中真正的「成功」到底是「成就外功」還是「成就內功」,見仁見智,不盡相同。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要成為一個全面發展的「成功人士」,恐怕還是應當盡力既成就外功,也成就內功。正如一個美好的女子往往「秀外」且「慧中」。這是一樣的道理。我們的祖先推崇一個人在生活中應當盡可能「內外兼修」——「修煉外功」以保障「物質生活」的充實與豐富;「修煉內功」以欣賞「精神世界」的海闊天空,實現靈魂的安寧與幸福,那是至高的、純粹而甘美的歡樂。
在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當我們因為追求成功的人生而逐漸疏遠心靈時,當我們在功利世界迷路而找不回自我的精神家園時,當我們在財富的激情飆升後感受不到幸福的溫柔時,或許我們需要常常這樣提醒自己:「幸福是人的最高利益」8。
風度不是造作,而是內在氣度的自然流露
風度,是一個人所具有的美好人格修養自內向外的映射,是強大而自信的精神力量的自然滲出。正因為他的心靈生活是如此豐富如此充實如此飽滿,以至於不經意間有一部分不由自主流溢於體膚之上、表露在對外的言行舉止之中,就像容器裡的水裝得太滿了,就會溢出容器外。這就是我們平時所謂的「溢於言表」「自然流露」。
風度透露了你的精神力量
在日常生活中,這樣的一些情況屢見不鮮:有時候一些人對自己曾經面對危機如何保持冷靜、在絕境中巧妙周旋最終力挽狂瀾的經歷說得頭頭是道,聽者無不信以為真、心生敬佩,那一刻我們以為遇見了一位「超人」,結果卻證明此人不過是一個誇誇其談、平庸無奇的俗人,就像一個小男孩向同伴們描述他是如何毫不畏懼地應對十條狼的圍攻,事實卻是當時的他被一隻惡犬嚇得魂飛魄散,一路連滾帶爬、疾奔逃亡;有時候一些人漂亮的履歷上羅列著他曾經參與的重大項目、高峰會議,他在其中扮演的不可取代的重要角色,旁人瞭解之下才得知他當時的角色不過是端茶送水、例行公事,並無可圈可點之處,更談不上什麼特殊的貢獻……這些情況有一個共性:名不符實——明明其內是「一」,卻欲放大成「十」;明明事實是「十」,卻竭力想喬裝成「百」。
對於一個真正有風度的人,情況往往相反,如果我們感受其「一」,那麼定然其內有「十」;我們感受其「十」,那麼定然其內有「百」。他們有很多過人之處,但往往羞於誇耀自己。這不難理解,自己誇自己本來就是一件讓人尷尬的事情。寫到這裡,想起了多年前看到的一個電影橋段。一個少不更事的年輕人向他的老師——一位德高望重、備受敬重的英國紳士提問:「他們說英國盛產紳士和淑女,那麼你是紳士嗎?」當時看到這裡,我心下沉思,這是一個多麼難以回答的問題——你若坦然承認自己是紳士,似乎多少顯得驕狂自負,而印象中紳士應當是謙遜低調的;如果你說你不是紳士,那麼對於眼前這位真誠求教、心懷期待的年輕學子,又將是一件多麼讓人沮喪的事情啊!結果,那位老師沉默片刻,回答:「I am always trying……(我從未停止過努力成為一名紳士)」——完美的答覆。
真正有風度的人,亦如這位紳士先生,他們的一言一行往往平易近人卻不失尊嚴、客觀公正卻飽含仁慈,舉手投足之間總帶著對事的慎重與明理、對人的理解和關懷,這令我們大多數人或驚奇、或欽佩、或若有所悟、或感慨萬千。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的判斷總是正確的、他們的決定總是最明智的,他們也會犯錯,和其他人一樣。因為他們是凡人,和其他人一樣,而凡人難免犯錯。但是和其他人不一樣的是,他們雖羞於誇耀自己的才能與貢獻,卻勇於承擔自己的罪責與過錯,他們會發自內心表達誠摯的歉意,更竭盡全力、想方設法予以補救,這常常使他們更容易得到旁人的理解與寬諒。然而,當他們的過失造成了對無辜者的傷害,他們對自己的寬恕相比於別人的,往往來得更遲更艱難。這件事在他們的記憶中留下的疤痕相比於別人的,也往往更久更深刻。小時候,長輩常說「做一個人,終歸要對自己有點要求」,而這些人相比常人,對自己的要求特別高。曾在某一本書裡讀到傅雷夫婦的故事,書中記述他們夫婦二人迫於種種絕望的處境,決定與這個世界告別,於是將自己裝扮一新,待夜深人靜時,先後撕下被單在鐵窗橫框上自縊而亡,其中有一個細節,他們把厚厚的被褥鋪在地板上,生怕深夜動靜太大影響到別人。有些人對自己的要求特別高,即使是死,也是如此優雅。
真正的風度具有一種令人心悅誠服的強大精神力量,這吸引了少數幾個潛心修行的人和一大批圖慕虛名的人。前者經年累月、上下求索、專心致志、修成正果;後者求成心切、心浮氣躁、不求甚解,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覺悟不到「風度」的真精神,所以只學會了一些不得要領的「皮毛」,就自顧賣弄、四處兜售了。既然是「皮毛」,當然是「表面文章」,經不起仔細的推敲和深入的研究。後者為了避免自己破綻百出,只能像上文提到的那些名不符實的人那樣盡力「以一充十」「以十當百」,通過虛張聲勢、故作姿態來彌補那虧空的「90%」,就像穿上了一件本不屬於自己的衣服,難得擺擺造型尚可,真活動起來往往捉襟見肘。真正的風度是一個人自然而然流露出來的精神世界的豐富和充實,而喬裝出來的風度則是一個人在竭力掩飾他內心的空虛和貧乏。
道德是孕育風度的種子
風度之美並不在於其流露在外的「翩翩姿態」或者「優雅舉止」,不在於那一揮手一抬眼一低頭,這只是「風」。風如過雨,倏忽即逝。風度之美之所以能讓人如沐春風,之所以能深入人心,風度之「風」之所以如此「養眼」,全在於其下之「度」是如此「養心」。
記得多年前一個學生在期末考試的試卷上寫下這麼一句話:一流高手之間比的總是胸襟氣度。我深感認同。一個人的風度本質上取決於他的胸襟氣度;一個人外顯的「大家風範」,歸根到底源於他內有堅強的意志和溫柔的心。這使得他能憑一己之力理解費解之事、忍耐不耐之苦、放下難放之懷;也使得他在任何情況下都會心懷公正、待人仁愛,對旁人的歡樂感同身受,對他人的苦難不忘將心比心。「對強者,他將他們視為自己的兄弟;對弱者,他將他們視同自己的孩子」9。追根溯源,風度源於一種最古老也是最偉大的力量:道德。風度之優不在於言辭之間的滔滔不絕,不在於舉手投足中的風流倜儻,風度的本質是一種震懾人心的道德力量。
人的「氣度」「尺度」「高度」「寬度」「深度」「風度」最終會化為一個人「信手拈來」「自然流露」的天性,而非有意識地矯揉做作,但這並不意味著它們完全「自然天成」「天性使然」。「風度」的成因絕不是隨隨便便、不假思索的本能,而是基於對德性深刻之思考、對舉止審慎之取捨;「風度」固然最終外化為一種無心之舉,但這樣的「無心」恰恰來源於長久的「良苦用心」。「無所在等於無所不在,無心意味著無處不用心」。真正的「風度」必須是經過深思熟慮和嚴格教養而修成的正果。教養的內容:公正與仁愛。教養的核心:道德。
我們常誤以為「道德」是一種精神的約束力,限制著我們不敢恣意狂放,卻不知「道德」實在是美好人格的驅動力,正是它在滋養著我們的「風度」,使之擺脫虛偽與低級,超越自私與惡意,既蘊含有一份溫柔動人的單純與慈悲,又能釋放出一種震懾人心的痛快與力量。就像斯蒂芬·茨威格筆下的蘇格蘭女王瑪麗·斯圖亞特在臨刑前的最後一句遺言便是:「我寬恕你們。」
如果「風度」是一朵優美的花,那麼道德便是孕育它的那顆神奇的種子。正因如此,風度可能是樸素的或者華麗的,但絕無可能是卑微的、做作的、驕縱的、傷人的;風度可能是深沉的或者飛揚的,但絕無可能是無知的、膚淺的、小家子氣的。真正的「風度」對人性的明與暗有著很深的洞見和同情,對生命的喜與悲有著透徹的領悟和釋懷,在歡樂中它是對歡樂的銘記和珍惜,在痛苦中它是對痛苦的承擔和寬恕,痛過之後還是善,苦過之後還是熱愛生活,像極了木心先生所說的「不知原諒了什麼,誠覺世事皆可原諒。」
真正的風度沒有大小之分,它只能是大的——大胸襟、大氣度、大心量、大覺悟、大關懷……而在這卓然高貴的姿態背後,是道德廣博深厚的大愛。
要自信,不要自負
自信者與自負者
跟很多人一樣,我欣賞自信的人。一個充滿自信的人不僅能使其他人在與之親近的過程中不由自主對他抱以信任,而且他往往具有一種難以抗拒的影響力,其他人如果長期在他身邊,耳濡目染他遇事時的冷靜沉著、待人時的不驕不躁,常常會不知不覺深受其感染,在自己的待人接物中也會自發地以他為效仿的榜樣。
同時,跟很多人一樣,我不喜歡自以為是的人。我們也稱他們為自大者、自負者、剛愎自用者。他們總是堅信自己的判斷、自己的才幹、自己的選擇,即使旁人能提供與之相反的明顯的客觀事實或提出另一些頗有價值的方案,他們依舊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固執己見、一意孤行。他們給我們的印象毫無疑問也是「自信」的,但是當我們在團隊或者集體中遇到此類人時,我們總覺得這樣的「自信」很多時候不是「明智」,而是「無知」;不是高瞻遠矚的「達觀」,而是閉目塞耳的「狹隘」;不但無助於高效地解決問題、帶來整體的「發展進步」,而且以盲目的獨斷阻撓問題的根本解決,造成毫無價值的「內部消耗」,甚至直接導致關鍵時刻的失敗。
美國陸軍史上最年輕的「西點軍校校長」麥克阿瑟,這位天賦異稟、贏得最多美國獎章的軍事將才,這位像迎接每一天升起的太陽那樣迎接戰爭的五星上將,這個「勇敢者中之最勇敢」的英雄人物,就因為他拒不承認錯誤的「傲慢自負」、絕不容忍批評的「目空一切」而在朝鮮戰爭中慘遭潰敗,造成了無可挽回的歷史過失,最終被總統杜魯門忍無可忍地解職。

自負是「變了質」的自信
我們每一個人都渴望成為一個自信的人,而沒有一個人願意被他人指摘為「自負」。但是很多時候,我們又會發現「自信」與「自負」之間的界限似乎並不像其字面上看起來那樣涇渭分明、清晰可辨。
在青年學生中常有這樣的情況,初入文學、哲學領域,對盛名遠播的前輩學者方才略知一二、其人其作還不明究竟,就開始誇誇其談、指手畫腳、評點江山。大多數情況下,這些學生只是暴露了自己的「才疏學淺」和「自命不凡」。我的老師們凡是碰到這樣的學生,就會向他推薦一兩本相關的著作或文章,有時會淡淡地補上一句「你似乎太過自信了……」言下之意,應該是在暗示對方犯了「自負」的毛病。我們很多時候看起來自信滿滿,說起話來鏗鏘有力、擲地有聲,事實上不過是夜郎自大、自視過高罷了。
我們常把「自負」誤當成「自信」,因為它們有著一個共同的前提:「自信」毫無疑問意味著「相信自己」,「自負」也是一樣,指的就是對自己深信不疑、執意堅持。它們的關係十分微妙,就像由同一束光投射而成的「明」與「暗」;就像同一張塔羅牌正立與倒立之間區分的「好運」與「厄運」;就像同一枚硬幣隨意拋向半空,落地瞬間不可預測的「正面」與「反面」;就像麥克阿瑟的前半生,卓越的才能為他構建起無可撼動的「自信」,這「自信」助他成就了無與倫比的輝煌,但是伴隨著一枚接一枚沉甸甸的勳章在他的胸前閃閃發光,民眾迎接他時一浪高過一浪的歡呼吶喊,他的「自信」逐漸充滿「負氣」而不斷自我膨脹,膨脹的力量如此巨大,以至於傾翻了一名職業軍人最為看重的軍紀,排斥了上上下下所有人的意見和建議,最終不惜與自我的理性為敵。「一個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運」10,冥冥之中他的命運就這樣在後半生被神秘地翻轉,璀璨漸入暗淡。應該說,麥克阿瑟是幸運的,因為他總是那麼自信,但不幸的是,他的「自信」過了頭。
現在我們仔細想想其中的道理,就不難發現:所謂「自信」與「自負」,其實呈現在外的表象十分接近,都是「相信自己」,而它們的本質差別則在於「程度」相異。若「自信」保持「適度」,才是真正的「自信」;一旦「自信」過度就變質成「自負」了。
日常生活中我們常常會忽略「度」的差別,以為那是無關實質的小問題,卻不知古人所說的「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是何等的真理,絕大多數的「質變」都起始於點點滴滴而漸行漸遠的「量變」。
就像我們對孩子的愛,「適度」便是真愛,「過度」就成溺愛,不但無益於孩子的身心成長,還有損於他們健全人格的塑造;美其名為「愛」,卻早已在「過度」之中偏離了「愛」的本質,反受其「害」;口口聲聲「為他好」,卻已然成為了無形之刃,切割了他最為寶貴的「自由意志」。同樣的道理,「自信」一旦過度就會變質,「自負」便是那「變質」了的自信,就像變質的牛奶不再是單純的牛奶,而多了好多奇怪的化學物質,不再是人體所需的營養,而是危害健康的毒藥。當「自信」過度而變質為「自負」,就與真正的「自信」全然無關,那不再是人格的閃光點,而是鑄成了個性的污點,不但不利於人,對己也相當有害。
沒有「自知」,就沒有自信
那麼到底是誰在「自信」與「自負」之間畫下了不可逾越的邊界?又是什麼「度」區分了所謂「適度」與「過度」?
古話說「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日常生活中我們常以「明智」二字用來讚美頭腦清醒、舉止得體的人。而人們將「明」放在「智」之前雖可能是一時無心之作,卻似乎包含了一種奇妙的直覺和天然的邏輯:不明,何以能智?看不清楚、看不真切,何以能想得明白、想得透徹?因此要達到「智」,必先要「明」。
何以明?——「自知者明」!
我們前面提到的「自信」也好,「自負」也好,有一個相通之處:相信自己。而它們兩者的不同之處恰在於:是否「自知」?是否自明?也就是,對自己有無清醒的認識?
換言之,「自信者」首先當是自知者——冷靜地看清自己的能力,公正地評判自己的水平,包括自我之所長、自我之所短,然後相信自己能揚長避短、取長補短;「自負者」則相反,往往是不自知者——看不清自己的真實水準,掂不出自己幾斤幾兩,所以無法客觀公正地評價自己,於是過高地估計自己,盲目地相信自己無所不知、無所不能。
由此可見,「自信者」與「自負者」的本質差別就在於——「自知」。古話又說:人貴有自知之明。「自知」竟然被祖先前輩們視為「高貴」之事,可見不是什麼唾手可得的易事。那麼,「自知」究竟貴在哪裡,又難在何處?一個自信的人應當自知些什麼?或者說,一個自負者與真正的自信者相比,他的「不自知」到底體現在哪裡?他不自知些什麼?如果我們找到了這個答案,或許也就能順籐摸瓜,發現「自信」的秘訣。
「自知」,無可厚非,就是要「知我」。那麼一個真正自信的人應當要「自知」些什麼?首先,當然是「知我所能」——我的專長、我的優勢、我的強項。自知了這些,才能擺脫自卑,建立起初步的「自信」。
但單單是「知我所能」,看到自己力所能及之事、過人之處,卻不知「我所不能」,看不到自己力所不能及之境、不可企及之人,就會變得故步自封、妄自尊大,真以為自己「無所不能」,久而久之,錯把自己當神。一個人一旦成了「神」,就意味著「與天齊高」「逍遙法外」,這就是典型的「無法無天」。眼中無法,意識上也就關閉了理性,心內無天,精神上也就拋棄了敬畏。喪失理智則近乎瘋狂,無所敬畏則難逃自我毀滅。「上帝要誰亡,必先使其狂。」這正是「自負者」的癥結所在——不夠全面、不夠完整的「自知」——知我所能,卻不知我所不能,進而誤以為自我無所不能。肉體凡胎,注定有喜怒哀樂、悲歡離合,不正是因為沒人能真正做到無所不能嗎?
自負,說到底,往往是井底之蛙無知而盲目的自欺欺人。更何況,人與人的愛好、志趣、理想各不相同,一個人如果能專心致志於自己情有獨鍾之事,盡其力、顯其能,已是很大的幸運、非常的幸福,又有什麼必要追求事事皆通、無所不能呢?
「能」與「不能」之間的人生自在
我所欣賞的自信,基於完整的自知——不但知我所能,而且還要知我所不能。兩者缺一不可。單是「知我所能」會使人狂妄自大、自負驕傲;單是「知我所不能」又會使人盲目自卑、妄自菲薄。這兩者都偏離了清醒的自知,進而遠離了自信。「自信」既不自卑,也不自大,恰是這「自卑」與「自大」兩個極端之間那個近乎完美的平衡點,那條不偏不倚、恰如其分的「中道」,所以有時我們給自信一個別稱——「不卑不亢」。
「極端」如同「黑白」,非此即彼,太過極致純粹,「中道」則如「灰」,有近乎白略帶黑的淺灰,有接近黑而少摻白的深灰,其間還有各種比例調和之下的這灰那灰種種灰,層次不同,變化多端。
「我所能」與「我所不能」不論孰多孰少,總會貫穿每一個凡人的一生,每一個人都有「我所能」與「我所不能」,無一例外,差別只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能」與「不能」的調配比例、具體內容,比如有的人相對而言更全能一些,五花八門皆有涉獵,有的人則專注一些,不懂經濟金融、時尚流行,卻精通醫術。
就像蘇格拉底所說:「我知道得越多,我所觸及的未知領域也越廣闊。」換言之,隨著我們知識的深入、閱歷的增長,我們會發現越來越多的「我所能」,而同時,「我所不知」「我所不能」的領域也在隨之無限擴大,世界並不因為我們漸趨充分的「認知」而變窄變小變無趣,相反,它會隨著我們視野的高遠、心胸的開闊而越來越寬廣、越來越奇妙,於是「自信」便成了我們在「能」與「不能」之間流轉游移的人生自在。
當然,「自信」不只是基於清醒的「知我所能」與「知我所不能」的知性認識,也不僅僅停留在為人處世的過程中自我心態張弛有度、收放自如,「自信」還需落實為一些更具可操作性、有益於更多人的東西,我稱之為「行動」與「事實」。
「知我所能,我所能者,盡善盡美」;「知我所不能,我所不能者,虛懷若谷」。
真正的自信者,會用一生的時間來探索什麼是力所能及之事,對於它們,我要盡可能做到完善,不是敷衍、不是應付、不單求完工交差,而是要言之必行、行之必果、竭盡全力、善始善終;同時,真正的自信者,每一天會用一定的時間來反省自己的不足之處,對於我不懂、做不好的東西,我要保持謙遜、保持尊重、保持風度。
這是我勾畫出的「自信」和「自信者」的精神樣貌。不過,「知我所能」指的不僅是知道什麼是在可見的能力範圍之內、我做得了的事,比如搬柴送水、灑掃應對,更至關重要的是,「知我所能」意味著深入挖掘自我尚未展露的潛能、瞭解自我內在的天分,然後盡己之力使潛能得以充分發揮、天賦獲得最大程度的施展。
就像小鳥知道自己是小鳥,它的天分、它的「所能」是「飛翔」,廣闊的天空和靜謐的樹林是它心之所屬的那片精神的故鄉;小魚知道自己是小魚,它的天分、它的「所能」是「游泳」,在潮流洶湧的江河湖海中隨波逐浪便是它生命的歸宿。
對於每一個擁有自然的、獨特的天分的人,他的內心深處都靜臥著一塊無可忘懷、欲罷不能的人生舞台——在那裡,我願意像火一樣縱情燃燒、似煙花般極盡綻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