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路易十四建造了這座凡爾賽宮,法國的宮廷其實就移出了巴黎城,來到了這座位於巴黎西南二十二公里的小城,也就是法國政府搬了家的意思。在這裡,革命前的波旁王朝經營了一百多年。
聽上去,一百多年真是夠長的。可是,當我們在凡爾賽宮內,看著不斷交替出現的,革命前的最後三位法國國王的油畫肖像,總是感到很驚奇:怎麼法國會在這麼短短的歷史過程中,濃縮地演出了一出經典的王朝盛衰的戲劇。這齣戲劇的主角是如此典型:野心勃勃、建立專制集權盛世的路易十四;昏庸無度、坐吃山空、戰敗失地而迅速衰落的路易十五;以及在頹勢中試圖改革和重振、開明卻又軟弱、最終被自己參與革新的局面失控而斷送的路易十六。整個歷史過程的演出,總覺得似曾相識,好像在其他國家的不同時代也曾經有過類似的線索。可是,在別的地方,這樣的過程往往很長,甚至一拖千年之久,中間會出現許多無趣的「夾塞人物」。而像法國這樣,將眾多跌宕起伏的情節,很有邏輯地集中在百年之內,在真實的歷史舞台上演,而且演得驚心動魄,真讓我們感歎不已。就是請莎士比亞之類的戲劇大師給精心安排,大概也不過如此了。
而這場戲劇的主場景,就是我們眼前的這座凡爾賽宮。
在路易十四的年代,他把舊制度的強盛推到了一個頂點。這個舊制度就是上層對於下層平民的權力。平民個人權利的增減是沒有制度保障的,是以一種上層「恩賜」的形式給予的。正因為是「恩賜」,所以,今天給你的權利,明天不需任何理由就可以收回。一個人生活在貴族領地裡,他是幸福還是淒慘,完全依仗他遇到的是一個「好老爺」還是一個「壞老爺」了。
舊制度向新制度的轉化,就是底層平民有越來越多的申訴渠道,有保障自己權利和決定自己命運的機會,並且這種機會被逐步地制度化。路易十四的時期,經濟發展了,疆域擴大了,可是,波旁王朝的欣欣向榮所傳達的似乎是「強國」的信息,卻掩蓋了它逆歷史前進方向而動的深刻危機。
這個危機,在路易十四的父親在位的時候就啟動了。當時路易十三還是個「兒童國王」,就由他攝政的母親做主,解散了王權之外的平衡力量——三級會議,造成三代君王,一百六十年不開三級會議。路易十四又進一步扼殺了僅剩的、來自高等法院的對王權監督的企圖。王權以外的意願表達被徹底窒息。路易十四也許過於迷信了自己的力量,而小看了先人的智慧,在1685年,他取消了亨利四世的對新教徒的赦令,重開對新教徒的高壓迫害。在這種狀況下要維持絕對王權,只能把警察、司法、軍隊、行政、財政,統統一手捏住。可是,那隻大權在握的手,無法不感受到日益強勁的社會進步形成的反彈的張力。
這樣一個由強盛的外表所遮蓋的實質倒退,使法國在強盛中深深植入了社會動盪的隱患。波旁王朝後世災難的起源,並不是繼業的王室後裔沒有一隻同樣強有力的手臂。而是他們的祖先路易十四,堵住了所有宣洩壓力的渠道,把一隻底下還在加火的封閉蒸汽壓力罐,生生強塞到了他們手中。這種由強力維持的社會穩定,是一個危險的狀態。初期壓力不大的時候,假如想改變,還敢打開蓋子。拖的時間太久,一開就該炸了。

路易十五
路易十五是路易十四的曾孫。1715年他繼位的時候,和他的曾祖父當年一樣,也只有五歲。這個新的兒童國王也有過一個攝政公爵代理政務。他就做過降壓洩洪的嘗試:重新宣佈停止迫害新教徒和恢復巴黎法院的各項權力,等等。可是,其他宮廷顯貴還沉溺在路易十四的強權美夢中,遠沒有這位攝政公爵的歷史眼光,在他們的反對下,這些嘗試被收回。剛打開的蓋子又被封上了。
五歲的路易十五接下了凡爾賽宮連同一個大花園,一定十分開心。可是,幾乎是應著一條冥冥之中的規律:一份成功家業的繼承人,往往是個敗家子。沒有制度保障的「強國夢」都是虛幻的。強與弱,都只能隨由著一個主事者的個人性格和運氣。一個不巧,就只能大家跟著一塊兒大起大落了。
舊制度中的主事者更容易只顧及自己。「朕即國家」的意思,就是拿國家當私產了。法國在路易十五眼中,不過就是一個放大了的凡爾賽而已。當路易十五成年以後,他並非沒有看到歷史發展的趨勢,否則就不會有他的驚世名言:「我死後哪管它洪水滔天」了。可見,他首先知道將可能「洪水滔天」;其次,他關心的只是自己,是高於一切的今日手中的權力,以及由權力所保障的,凡爾賽宮廷的浪漫生活。
同時,人類在進步。這種進步常常是由看不見的思想產生的。思想這樣虛無縹緲無可捉摸的東西,在發展到一定的時候,竟然會動搖一個強大的實體,這實在是世上最大的奇觀。
思想會呈現五色繽紛的面貌,這就是文藝復興時期真正的作用。那些描繪著人體的繪畫和雕塑,那些韻律柔美的音樂和詩歌,那些手工精巧的工藝,那些仿古羅馬時期的建築,這一切似乎只是愉悅感官的「奇技淫巧」,常常使得一些嚴肅的思想史學者看著不耐煩。是啊,文藝復興之後帶來的藝術氛圍,幾乎淹沒了整個凡爾賽宮。連路易國王們都認為,這些人類的精神產品,這些由他們「豢養」著的藝術家們,奇妙地製造出來的玩意兒,顯然是上帝為了裝點凡爾賽這樣的宮廷,為了豐富他們悠閒的生活,才打發藝術家們來為他們創造的。
思想的發展有一個過程,精神成果對社會產生的影響往往是滯後的。路易王朝的國王們,誰也沒有想到,這些看上去只為取悅他們而存在的藝術,使人的心靈因此從粗野麻木而變得多愁善感;在包含著藝術在內的文明進程中,人們開始能夠細微地體驗痛苦和美好,對於幸福的理解開始超出了一塊黃油和麵包;感性的體驗開始交織理性的思考;人們的精神需求開始增長,自由、人道,這樣曾經和平民百姓無緣的字眼,逐漸成為一些人無法迴避的思考內容,甚至成為一些人捨身追求的目標;一些人,甚至是貴族,他們關懷的目光終於有可能開始超越自己。而這種看不見的變化,會在有朝一日顛覆一個持續千年的舊制度,顛覆他們腳下的凡爾賽宮。
所以,體驗著作為十七世紀藝術成果的凡爾賽,我們似乎必須承認,這個文明進程在法國,是宮廷和貴族們無意識地在共同推動的。同時,他們本身也在不可避免地被文明所改變,被進步的潮流所推動。在變革的關口臨近的時候,即使以最保守的方式去看待他們的歷史局限,他們也絕不是抱成一團抵禦變革的歷史絆腳石,他們中間有相當數量的優秀者,甚至有意識地站到了歷史進步的一面,參與顛覆他們世襲的優越。
路易十六就是在變革臨近的時候,接下這個王位的。非常可悲的是,專制強權的路易十四整整在位七十二年,昏庸無能的路易十五在位五十九年,而在二十歲繼位,最有希望配合變革的一個相對開明的君王路易十六,不僅接下一個爛攤子,而且大革命之前留給他的時間只有十五年。
今天再去看革命之前幾十年的法國,感覺很不合我們在東方歷史中所推理的常情。相對於中國的宮廷,法國王室的浪漫氣息越來越甚。一大群貴族沒有對王室「應有的」畏懼。當年的凡爾賽宮並不是我們想像中的那樣壁壘森嚴。今天,在凡爾賽的大門外,固然有著兜售廉價明信片和小「艾菲爾鐵塔」模型的小商販,而在當年,照樣有著一些類似的小商業。那是一些出租帽子和佩劍的小鋪,以供那些已經敗落的貴族進宮前租用,以保持他們起碼的貴族「風度」和臉面。甚至,凡爾賽宮人來人往的駁雜,還使得宮內經常混入小偷。
對於游離於王室之外的知識階層,宮廷對他們已經不僅是寬容,簡直是縱容了。我們今天可以如數家珍地數出一串串的十八世紀法國思想家,大談啟蒙運動和百科全書派,談到他們對於人類進步的貢獻,對於法國革命的影響等等。可是要知道,他們可都是被宮廷給「寵」出來的。他們在一生的學術生涯中,可能經歷幾個月的監禁,如狄德羅被路易十五關押了三個月,可能有短暫的某本書被查禁;如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被路易十五所禁,可能一時不得意而流亡他鄉。可是,他們在很長時期裡,已經沒有立斬午門的性命之憂。不僅如此,他們甚至在不同的時期出入宮廷沙龍,和他們要反對的舊制度的代表人物高談闊論。
這種「離奇」的狀態,又一次印證了東西方文化的最初的那點分岔,在後面會產生多麼遙遠的距離。知識的迅速積累,思想的飛躍,是以法國知識階層獲得了思想的寬鬆環境為前提的。而這個思想環境,就是凡爾賽宮為貴族開放的大鏡廊和凡爾賽花園之類的東西所提供的:先有了王室和貴族在歷史上久遠的平等關係,先有了文藝復興提供給他們的共同趣味和他們之間的平等交流,才能夠有以貴族階層為緩衝的,法國宮廷對知識階層的寬容狀態。貴族對知識修養和藝術趣味的迷戀,使他們離不開這樣一個沒有貴族頭銜,卻有著精神上的貴族光環的群體。當宮廷對這樣日益肆無忌憚的離經叛道忍無可忍的時候,貴族卻成了二者之間的一個龐大的免費遊說集團。而他們遊說的成功,又離不開宮廷本身對於知識、文化、哲學、藝術,以及各種此類不切實際、花裡胡哨玩意兒的歷史癮頭。東方皇上過來看一眼的話,準會搖著頭不屑一顧:君不君,臣不臣的,成何體統!
思想的先行,制度的陳舊,還有什麼比這個更危險的呢?當自由、平等、博愛已經被廣泛地、充滿激情地反覆詠歎,當舊制度在民間的歷史宿怨從來沒有消散,而社會向宮廷提出自己要求的渠道卻被長期強制切斷,在這個時候,人們還能指望什麼呢?
今天的凡爾賽,大家都知道有宮廷和花園兩個部分。宮廷的開放部分,是在進門以後的右側,其實,在宮廷的左側,還有一個很大的展廳。這個展廳還要另外買票。大家走到這兒,往裡一探頭,發現黑乎乎的一片,外面又寫著說這是「國會」,實在想不通王宮裡怎麼會出來一個「國會」,聽到還要買票,一般就向後轉了。所以進去的人遠比宮內其他地方的遊人要少。
我們還是決定進去。裡面先是一條大走廊,是以文字圖片組成的歷史介紹,其中的文字部分當然都是法文。然後就是那個黑乎乎的會場了。這是一個結構相當完美的國會會場,問題是今天的法國人決定用幻燈的形式來向大家介紹這個地方,因此,就必須遮擋光源。會場內的大多數時間都是漆黑一團。即使在打出燈光來的時候,空氣的自然來源還是隨同光源一起被堵住。人工通風又顯然不足。於是,坐在裡面,馬上就有些缺氧的感覺。可是,看一眼還是很值。這裡,就是1789年法國大革命後的第一個「國會」會場。也就是法國的「古代國會」三級會議,在整整中斷了一百六十年以後,在路易十六手上重新開會,改為立法會議以後的會場。法國大革命著名的《人權宣言》,也就是在這裡通過的。
今天打開歷史書,去重溫這段歷史。一般都說,路易十六並不是一個願意改革的人,他是在壓力下,被迫召開這個停頓久遠的會議。可是我想,假如身臨其境,大概輪到再積極的改革者,都不會很自願地去打開這個蓋子的,這是求生的本能。沒有人會樂意去打開一個悶了一百六十年的炸藥包的。

被砍頭的路易十六
路易十六接下的法國,本來就不是一個風調雨順的狀態,而是路易十五準備由它「洪水滔天」的。他除了面臨種種變革前夕的壓力,還面臨巨大的財政困難。這種財政困難自然有種種原因:王室傳統的揮霍,路易十六對美國革命的財力支持,等等等等。可是,最終還是可以歸到一點,就是舊制度把國產當做家產,沒有有效的監督制度。錢用到哪裡是國王的事情,旁人不可以說三道四。制度弊端形成的敗家,沒有剎車裝置,敗開頭就可能一敗塗地。三級會議之前,路易十六試過改革,也預料到舊制度的大量規則已經必須廢除。可是,積重難返,一旦付諸行動,就碰壁回頭。而法國當時的社會狀態,已經分崩離析。所謂的三個等級,僧侶、貴族和平民,以及會議的召集者宮廷,已經久久沒有溝通。換了四個財政大臣,也無法讓這些分散的力量整合起來,協助宮廷讓法國渡過難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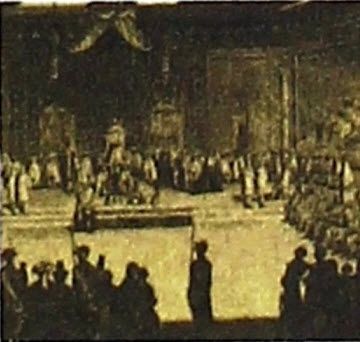
凡爾賽的國會大廳
這個時候,路易十六決定把三個等級的代表都請到凡爾賽宮來,期望他們達成一個協議。路易十六懷著緩進改良的希望,希望他們之間能夠協調出一個三方四面都能接受的改革方案來。今天我們坐在這個「國會」大廳裡,回想當時的局面,不知路易十六對這只炸藥包的能量到底做了怎樣的估計。我們甚至覺得,路易十六在作出重開三級會議決定的那個晚上,他實際上已經給自己簽署了死刑判決書。正像托克維爾說過的那樣,「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
炸藥包就這樣在凡爾賽宮由路易十六親自拉響。
距離上一次會議已經一百六十年過去了,三個等級本身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尤其是第三等級,是僧侶和貴族之外的一切力量,複雜得一塌糊塗。時間太久,人們只記得有過這樣一個古老的民主雛形的傳統。可是已經沒有人知道,會議應該按照什麼規矩開,他們之間的關係又應該如何。上兩個等級還端著舊制度的架子,卻已經沒有多少實力。具有實力的第三等級,又把必須的遊戲規則等同於舊制度本身予以唾棄。
對於第三等級來說,實力就是一切。他們已經等候了太久,憑什麼要做讓步妥協。然而,不論是過去、今天,還是將來,沒有讓步妥協就不會有協議,有的就是暴力革命了。路易十六從凡爾賽宮的窗子裡向外看,看到會場外面的宮廷廣場上,已經擠滿了從巴黎迢迢趕來支持第三等級代表的民眾,人聲鼎沸。
這是他所期待的漸進改革,還站在開端,就開始走向毀滅的一刻。

塞納河畔(作者手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