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盧瓦河流域走了好幾個地方,不論到哪裡,最後都會回到不同河段的盧瓦河邊。現在閉起眼睛,那凝重的、亮灰色的河水,似乎還在眼前流淌。
盧瓦河谷是城堡之谷。去那裡之前,我們正好在巴黎遇到一個英語書店。在美國看英語書,總覺得遠不如看中文書來得順溜,可以一目十行。可是在法國,不論進什麼博物館,文字說明都是法語的。半猜半將就,常常還是不得要領。記得在法國南部坐火車,廁所裡的標識牌有四種語言,法語、德語、西班牙語和意大利語。雖然英語世界來旅遊的人很多,還是沒有英語。不知是不是當年和英國人打了一場百年戰爭,打得印象太深刻的緣故?所以,久違自己熟悉的語言,當了一陣半瞎子之後,看到一個英語書店,就分外高興了。

盧瓦河
書店的主要庫存就是旅遊書。出來的時候,我就捧著那本有關盧瓦河城堡的書《盧瓦河城堡及其周圍環境》(The Chateaux of the Loire and Their Surroundings)。這本書的文字部分過於簡潔。對我們來說,書裡對於葡萄酒特色的介紹,似乎太滔滔不絕;對歷史的介紹,又太吝惜筆墨了。可是,我們還是很高興在去盧瓦河之前,能夠得到這樣一本書。因為薄薄的一本書,裡面有差不多近一百個城堡的彩色照片,而且印刷精美。最關鍵的,是書裡對所有城堡的開放狀況和開放時間,都有說明。
盧瓦河的城堡沿著兩岸,被一個個小鎮簇擁著。租一輛車自己開著一個個城堡跑,大概是最方便的了。但是,我們還是選擇了坐火車。我們想比較悠悠地走幾個城堡,覺得看城堡和看博物館的展品是一個道理,一下子看多了,沒準就把自己給噎住了。
法國的火車准點,幾乎分秒不差。它速度快,車廂窗明几淨並且舒適,無可挑剔。火車票可以在兩個月內有效,當然不能來回重複使用。在每個火車站的站口,都有一個自動檢票機,沒有檢票員。上車前自己在檢票機前夾一下票就行。所以,上火車就像上公共汽車一樣,即便是巴黎這樣的大車站,都是如此。找準自己要上的車,上去就是了。買票就買到最遠的一站,中途一次次下來,順序使用同一張票。這比一站站地買短途票要便宜得多。
我們翻著這本書,選了幾個城堡,就像大多數遊客一樣,我們首先選擇了最著名的兩個皇家城堡:香波荷和雪儂墅。然後,我們選了一個人們很少光顧的地方:默恩·蘇·盧瓦城堡(The Chateau of Meung-sur-Loire)。我們手頭一直有一本導遊書,是來法國之前朋友們送的,他們說得不錯,這確實是眾多導遊書中最著名最好的一本。只是上面也沒有這個城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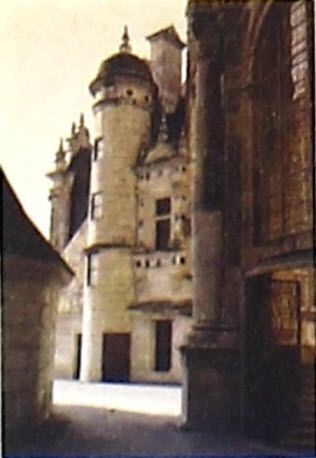
盧瓦河上最大的城堡香波荷
默恩·蘇·盧瓦是一個小城市,這裡是中世紀蠻族入侵和歐洲歷史動盪的見證。公元406年,旺達爾人(Vandales)橫掃而過,不僅毀了最初的城堡,還殺了個雞犬不留、一百年後,才有一個叫聖利伐的教士,在這裡帶領人們重新建起家園。他在公元565年死去後,這裡就建了一個紀念小教堂。此後三百年的家園建設,又在諾曼底人入侵的時候被搗毀。小城以頑強的生命力再次慢慢恢復。教堂和城堡都在屢毀屢建中,越建越大。百年戰爭期間,這裡又被英軍佔領,並在附近發生了多次戰役。默恩·蘇·盧瓦生存下來,至今只有六千二百多個居民。

盧瓦河邊最壯觀的城堡香波荷(作者手繪)
從十二世紀到法國大革命為止,這個城堡就一直是奧爾良(Orleans)教區紅衣主教的住宅。因此,教堂一直是城堡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可是,歐洲漫長的政教合一歷史,使得地區主教還兼為地區的行政和司法長官。於是,執政官員住宅,又兼為司法和執法機構,甚至包括監獄。在十二世紀到十七世紀,這裡兼為奧爾良地區的正式監獄。這樣一個中世紀城堡住宅,具備了如此典型的綜合功能。這就是默恩·蘇·盧瓦把我們吸引到那裡去的原因。
默恩·蘇·盧瓦就在火車的主幹線上,所以坐火車去特別方便。我們是從安布瓦斯倒回這裡,下火車還是清晨,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個可以問路的人。順著她的指點,我們向市中心走去。路途不遠。最後,走到一條小小窄窄的老街,迎面是一個岔道口,分岔點上是一棟西班牙式的、木結構外露的小樓房,樓下的燈光暖暖的,映照著一個同樣溫暖的小小麵包房,這是清晨的法國小城鎮最繁忙的地方了。越過這小街小樓,默恩·蘇·盧瓦城堡外相連的教堂,就已經可以看到了。

默恩·蘇·盧瓦的小麵包店,左下角露出的就是默恩·蘇·盧瓦城堡
我們走到跟前,看到的是一片灰色。外面是灰色的大教堂。緊閉著的城堡大門裡面,越過一小塊空地,是連綿延伸的灰色的中世紀城堡式住宅。問題是,大門不開。我們先到教堂裡面轉了一圈,然後走向旁邊的咖啡館。老闆對我們說,城堡肯定會開門,就是時間還沒到,還差半個小時。我們定下心來,守著城堡喝咖啡,好像生怕它一轉眼就跑了。
半小時過去了,門還是不開。我們甚至懷疑是不是另有一個大門,於是,就繞著古老的石頭圍牆走起來。這一走,才知道它的領地範圍很大。繞著繞著,我們就又繞到了小城的街裡,這才發現,這是一個水鄉小城。盧瓦河的支流在這裡被悄悄引進,在一片片春天的粉彩中穿行。有時,河水流淌在整齊的、兩邊佈滿花壇的溝渠裡,有時,河水又被緊緊地夾在住宅的陡峭石牆之間。石牆上蔓延著青苔,攀援著無名的野花。河水又湍急地穿過拱形的石橋洞。石橋都很小,而兩岸石牆上小窗洞的窗台上,都有著一盆盆的亮麗的花兒在開放。千百年石塊的蒼老,使今日春天的輕盈並不失去底蘊,無盡的有生命的水流穿行而過,默默地在連接著古今。怪不得,這裡還是大仲馬寫《三劍客》的背景地。在如此美麗的畫面裡徘徊,使我們差點忘了那個沉重的灰色城堡。直到最後,進了一個漂亮的小院,才發現自己歪打正著,正好來到這個小城的旅遊信息中心。
在那裡,一個熱情的年輕女士告訴我們,這個默恩·蘇·盧瓦城堡,今天是一個私人財產。它確實對公眾開放。但是,裡面的接待人員很少,又是旅遊淡季,所以,它每小時只開放一次。由一個接待員出來,領著大家進去,轉身就把大門又攔上了。錯過這個點兒,就要等下一個小時了。聽到這裡,我們趕緊匆匆告別,急急地向城堡再次趕去。
這次看懂了。城堡的大門上掛著一個紙做的鐘,上面的指針所指,就是下一次的開放時間。這次,再也不敢走開了。
到點了,接待的女士姍姍來遲。跟著她,我們五六個遊人終於跨過那根標誌著領地界線的粗粗繩索,進了城堡的範圍。可是,她領著我們向院子裡走,卻是反著城堡建築的方向。大家納悶地隨著向右拐進一個小岔道。她突然站住,停在一個叫我們莫名其妙的地方。這是花園的一部分,微微隆起一個類似地窖的東西。我想,這大概又是法國人的驕傲——大酒窖了。她打開一扇低矮的歪歪斜斜的大門。看進去實在不像是酒窖。裡面可以站人的空間似乎很小、很暗,唯一的光線來源就是這扇剛剛打開的側門。假如關上門,裡面必定是漆黑一片。她一邊鼓勵猶豫著的我們輪流進去看看,一邊介紹說,這是當年中世紀監獄的一部分,是一個無期徒刑的囚室。
我們還沒有反應過來她說的是什麼意思,就迎著前面出來的人,交替著走了進去。一進去,就遇到一段齊腰高的類似石牆的圍欄。昏暗中看去,圍欄裡面是一個地窖,地窖中間是一個黑乎乎的洞,深不見底。我們突然之間明白了,這就是我們帶在旅途上重讀的那本書——雨果的《九三年》中描寫的中世紀城堡地牢。
今天人們來到歐洲遊覽中世紀城堡,都會禁不住地帶著欣喜讚賞這樣輝煌的建築歷史遺跡。它的造型是如此獨特,堪稱完美;它的石築工藝是如此精湛;它所攜帶的歷史沉澱是那麼豐富。你幾乎不可能不讚歎。因為它不僅作為建築藝術在感動你,而且它只屬於遙遠的中世紀。可是,讀了雨果,你也無法不記住,城堡是中世紀舊制度的象徵。它的沉重遠不限於它厚重的石牆和灰色的視覺壓力。這個在中世紀曾經非常普遍的地牢形式,才是城堡文化最沉重最觸目驚心的一個部分。
我們來到這個城堡的時候,預想過我們也許會看到一些什麼,可是,一點沒有料到,就在我們一進城堡大門,就突然遇上了由雨果在1873年描述過的典型中世紀地牢。
正如雨果所描寫的,真正屬於牢房的這部分是沒有「門」可以走進去的,受刑者是被「脫得精光,腋下繫著一根繩子」,從我們被擋住的這半截石牆上「被吊到下面牢房裡去的」。在我們看到的這個地牢,規定每天只放下一大罐水和一大塊麵包。不論裡面有多少囚犯,食物和水的數量永遠不變,而且通常是短缺的。被關在下面的渾身赤裸的人們,就廝打著搶奪這有限的維持生命的資源。
最恐怖的,是中世紀地牢的典型設計,它只進不出。那就是我們看到的地牢中間的那個「洞」的作用。那是一個四十五英尺深的,按雨果的說法,「與其說是一個囚室,不如說是一口井」的地方。上層的囚徒終日在黑暗中摸索,誰從這個洞口「跌下去,就不能夠再走出來。因此,囚徒在黑暗中必須小心。只要一失足,上層的囚徒就會變成下層的囚徒。這一點對囚徒很重要。假如他想活著,這個洞口意味著一條死路;假如他覺著活得厭煩,這個洞口就是出路」。那些終於搶不到麵包和水的囚徒,就會很快進入下一層。而上一層的囚徒,就始終在這個洞口的恐怖中苟延殘喘。你無法想像從這些囚徒身上,還能找到一點作為「人」的感覺。
這不僅是雨果對地牢的描述,這是他對舊制度的評介:「上面一層是地牢,下面一層是墳墓。這兩層結構和當時社會的情形相似。」
不論在什麼地方,留下來的往往總是上層的歷史,而芸芸眾生常常是被忽略的,越早就越是如此。在野蠻的年代,從歷史記錄的角度,不會有人關注普通的生命。甚至直到我們自己經歷過的歷史,假如幾十年後的今天,我們要從書中去重讀,就會發現,今天的歷史學家依然是在熱衷於剖析上層的路線鬥爭,派別的此起彼伏。我們目睹的主要歷史場景在書中會大塊大塊的消失。因為,幾乎很少有學者再願意耗費自己寶貴的學術生命,去關注和記錄那些無以計數的、被碾為塵土的最底層的個人生命。
法國的中世紀,幸而留下了這樣的地牢。看到它,人們就必須看到裡面曾經有過的生命。
對面不遠,就是城堡住宅的入口。我們接著就參觀了城堡內部的上層生活。上品的古董傢俱,精美的掛毯、繪畫和工藝品,滿架滿架的書。雖然,我們看到的這部分內容的主人,已經是最後鄰近法國革命前的主教。在那個時候,隨著歷史本身的進步,這裡已經是純粹的住宅,不再兼有司法的功能。但是可以想見,在地牢依然在使用的時候,這個城堡裡的生活品質也是如此優雅的。
我們從會客室、餐廳、書房、臥室,等等一路看去,最後,來到了寬大的廚房。在廚房的旁邊,是一個浴室,雖然是幾百年前的洗浴設備,但是在當時就算是很舒適的了。就在浴室裡,導遊突然帶著我們從一個入口往下鑽。粗大的石階,粗重的石壁,一路向下。我們終於停在一個地下的廳裡。在這個時候,我們的四周,我們的上面和下面,都已經只有石頭了。這彷彿是一個陰冷而粗笨的巨大石棺。這就是囚犯們進入那個地牢之前必須先到過的地方。假如說,地牢是典型的中世紀執法部分,那麼,這裡就是典型的中世紀的司法。
我想起,我在雨果的另一本書裡,也讀到過這樣的地方,那是《笑面人》,雖然被他生動描寫的中世紀司法是屬於英國的。可是,中世紀的歐洲是那麼不分彼此。他們的疆域經常是變換的,他們的宮廷經常是近親,他們的法庭經常使用著相似的定罪方式。我們進入的這個地下石庭的一部分,被柵欄隔開,就是尚未認罪的囚犯被關禁的地方。認罪之後,就投入先前我們看過的地牢了。那麼,中間這一步司法怎麼走呢?這就是大廳的另一部分:刑訊。那裡,至今陳列著中世紀遺留的刑具,粗大的木質刑架,還有強行灌水的裝置。站在這裡,我們知道,根本沒有人會懷疑,是否會有人不認罪。都會認的,只是時間的長短問題。

 默恩·蘇·盧瓦城堡地下刑訊室的中世紀刑架默恩·蘇·盧瓦城堡地下刑訊室的中世紀刑具(灌水裝置)
默恩·蘇·盧瓦城堡地下刑訊室的中世紀刑架默恩·蘇·盧瓦城堡地下刑訊室的中世紀刑具(灌水裝置)從窗子裡,主教和他的客人們,在瞭望花園的時候,就可以看到那個地牢的入口。他們躺在熱氣騰騰的浴缸裡,也知道地下室正在發生些什麼。這一場景使我想起中國類似的衙門與府第的結合,所謂前官後府。前堂庭審時刑具鋪列的肅殺之氣,和後花園的書卷安閒,閨房繡閣,居然有機地統一在一起。人類在同一個大時期,竟會有如此驚人的異曲同工之作。不同的是,歐洲的中世紀以政教合一玷污了宗教精神,我們以政儒結合毒害了本應是獨立的學者階層。而對於殘忍的普遍認同,對於苦難的漠視,是那個時代的基本特徵。
在幾百年前,在中世紀,甚至延續到文藝復興以後,人類在文明的最根本基點,在人性的普遍覺醒上,還遠遠沒有出現自覺的本質進步。不僅是上層的殘酷,整個社會上上下下,沒有人會把犯人當人。這就是雨果在《巴黎聖母院》設置的一幕,能夠強烈震撼人心的原因。卡西莫多在中一世紀巴黎聖母院的廣場上,被捆綁在刑架上當眾鞭打。在他淒聲呼渴的時候,滿廣場鐵石心腸的圍觀者個個幸災樂禍,不為所動。直到一個吉卜賽姑娘艾絲美拉達站出來,提著一罐水,目不斜視地向不幸者走來,人們才可能開始思考,究竟什麼才是所謂的「人」。

陳列在雨果故居的《巴黎聖母院》插圖
站在中世紀的刑訊室,默恩·蘇·盧瓦城堡的導遊告訴我們,認罪後的囚徒之所以會進入那個地牢,是因為要適應法國中世紀政教合一的「國情」。主教既要主管司法,又有教義不得殺生和見血。所以,才出現了這樣的地牢設計。所有他不願饒恕的犯人,都「緩」為這樣的無期監禁。可是,事實上,這裡的生命是短促的。從來只有人進去,沒有人出來。死者都在那口中間的「井」裡,在四十五英尺深的黑暗井底「消失」了。
可是,就在我們所看到的這個地牢裡,史無前例地走出來過一個囚犯,他就是法國最偉大的抒情詩人——弗朗索瓦·維永(Francois Villon,1431?-1463以後)。
維永是個孤兒,從小被一名姓維永的教士撫養長大。1452年在巴黎大學獲文學碩士學位。三年之後,他在一場鬥毆中刺殺一名教士,以及涉案盜竊等,被兩次逐出巴黎。就在這段時間裡,他出版了詩集《小遺言集》。他開始浪跡四方,大概是破罐子破摔了,他接連數度入獄。又不知為了什麼,在1461年,被關入這個默恩·蘇·盧瓦城堡的地牢。也許因為正當身強力壯的三十歲,他在這個活地獄裡居然熬過了五個月。最後,被路過此地、剛剛登基的法王路易十一赦免救出。

維永木刻像
我們看到,其實中世紀的司法狀況一直延續到文藝復興之後,更延續到後來的專制時期。就在這個城堡,這樣的狀態就持續了五個世紀,跨越中世紀後期和文藝復興,直到十七世紀才結束。雖然人類緩慢的進步在推動著對人性的思考,可是從制度層面上著眼,文藝復興並沒有立即觸動舊制度本身。因此,作為詩人的維永,有可能會被一個愛好詩歌藝術的國王赦免,而這個地牢本身,卻絲毫不被質疑。在維永被赦免以後,默恩·蘇·盧瓦的地牢還被持續使用了整整二百年,跨越了整個法國文藝復興時期。
這一段經歷,給維永留下了深深的印記。此後,他的詩集《大遺言書》,風格變得更為深沉。雖然他依然沒有擺脫他與生俱來的麻煩,兩年後又因鬥毆被判過一次死刑。後來經過上訴,改判又一次逐出巴黎。他從此消失,再也沒人知道他此後的經歷。
我們今天讀維永的詩,透過發脆的紙頁,仍然可以看到他五個月在地獄裡掙扎的日日夜夜。他在五百年前,痛切地發出當時還很微弱的呼籲人類對弱者、對囚犯,甚至對死囚犯的同情心。他用懸掛在絞刑架上的死囚的口吻說:
在我們之後,依然活著的人類兄弟不要硬著心腸背棄我們假如你能憐憫我們這樣的不幸者或許上帝會更厚愛你你看,我們,五個六個,被懸掛在這裡
那不久以前,我們還很喜歡的肉體被吃掉,被腐爛掉,而我們的骨頭歸於塵土,但願沒人把我們當做笑料請祈禱上帝寬恕我們
不要感到受辱,因為我把你稱作兄弟,即使法庭判了我們死刑,你要理解,並不是每個人都有同樣一副好腦筋在基督面前,為我們說幾句吧,既然我們自己已經無法開口他對我們的仁慈會源源而來使我們避免地獄之火的煎熬我們已經死去,願沒人再嘲笑我們請祈禱上帝寬恕我們
大雨在沖淋和洗刷我們太陽在曬乾和曬黑我們鴉鵲啄著我們的眼睛摘取我們的鬍鬚和眼珠我們再也無法靜止站立一會兒在這裡,一會兒在那裡,任憑風隨心所欲地擺動我們鳥兒啄出麻點,我們還不如一個縫紉頂針所以,別落到我們這一步,請祈禱上帝寬恕我們
墓督王子,萬能的主啊不要讓我們淪落地獄我們除了準備去那裡,已經沒什麼別的可做人們啊,已經沒什麼可嘲笑的了,請祈禱上帝寬恕我們
默恩·蘇·盧瓦城堡是水平呈一字型伸展開的。在走進院落大門的時候,我們只能看到城堡展開的一個立面,而在縱向穿越之後,我們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景象。這裡的監獄功能是在十七世紀撤銷的。城堡大修的時候,主人把當時典型的十七世紀住宅風格生生「貼」了上去。所以,今天的默恩·蘇·盧瓦城堡,有著與眾不同的建築面貌,它的一面是一個灰色的中世紀城堡,另一面卻是一個粉紅色的十七世紀豪門住宅。雖然在做這樣結合的時候,看得出建築師已經費盡心機,盡可能糅合得自然。可是,這個主人的要求本身實在是勉為其難。這兩種建築風格格格不入,從建築的角度來看,原來的風格整體性,已經被完全毀壞。
可是,這棟建築物的外觀,卻成了一個時代的象徵。文藝復興以後的法國,就像這個城堡呈現出的風格面貌。它是在中世紀的基礎上,開始柔化,有時甚至是粉飾,而沒有從根基開始的制度質變。所以,法國很順利地就在文藝復興之後,又完成了走向專制集權的過程。散漫的法蘭西走向了大一統的大法國。

默恩·蘇·盧瓦城堡的另一個立面嵌入了粉紅色的住宅,兩個立面風格完全不同
在法國大革命之前,默恩·蘇·盧瓦城堡經常聚集著以路易十五的前財政部長為首的一群王公貴族,還有自文藝復興以來,他們周圍就從來沒有缺少過的詩人、畫家,建築師和各種藝術家。必須承認,時代是在進步。至少,自詡文明的人們,已經不可能在耳邊隱隱感覺地下受刑者呻吟的同時,吞嚥佳餚美餐和猩紅透明的葡萄美酒了。可是,在監獄撤離後的很長一段時期裡,要他們中間的優秀者,將目光完全超越自身,落到底層,還幾乎沒有可能。但是,從文藝復興開始的、作為抽像精神產品的人文主義,已經在慢慢生長,既攪動著底層的岩漿,也推動著上層優秀人物的反省。雙方都在尋找出路。文明本身在發展,正是它,使得本質的變革將成為必然。
當參觀默恩·蘇·盧瓦城堡住宅的書房時,我們看到滿牆深色精裝、皮面燙金的古籍,都是當年主人的遺物。導遊特地走到一個書架面前,向我們指出其中的一本詩集,當年,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這本詩集就在城堡的書房裡了。
書脊上雋印著作者的名字:弗朗索瓦·維永。

凡爾賽宮的樹林(作者手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