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8月17日是我的公公陳樂素教授百歲冥誕,他是現代宋史研究的奠基者之一。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他不但發表了許多高質量的宋史論著,還培養出了一批著名的宋史專家,如宋晞、徐規、程光裕、陳光崇等;他的第二、第三代弟子更是遍佈海內外。2002年11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浙江大學、暨南大學在廣東珠海市聯合舉辦紀念他百歲誕辰的國際學術討論會。我作為他的兒媳,希望以我淺薄的認識,從我親見親聞的角度,介紹他的人生經歷、學術成就和為人處世的風範。
一、第一印象
20世紀50年代末,我帶著簡單的行李,經過長途跋涉,終於在北京前門火車站下車。智超已經是第二次來接車了,因為旅途疲憊,我在武漢休息了一天,耽擱了一天的行程。我們雇了三輪車到達陳家的時候,已經是晚上十點多鐘了。樂素先生和夫人洪美英女士為了等我的到來,還沒有休息(後來才知道,他們一般晚上十時就寢)。我走進陳家門,第一眼就發現,他們的形象與我想像的完全不同。他們一點都沒有架子,對我這個遠方來的小客人親切慈祥。美英女士性格外向,端詳著我,問我一路上的情況。樂素先生比較內斂,只是摸摸我的頭,拍拍我的肩膀,說長途旅行已經累了,要我早點休息。看他們待人那麼真誠、隨和,我也就沒那麼拘謹了。
當我定下心來,環視室內的佈置時,與我想像的大不一樣。這裡不是花園洋房,而是帶套間的兩間舊平房,坐北朝南。外間大約二十多平方米,三面牆排滿了書架,書一直堆到屋頂,大部分是線裝書。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套盒裝的二十四史。一抬頭,映入眼簾的是一幅十八寸的大照片,是樂素先生與朱文叔向毛澤東敬酒的場面。室中還有一排書架,兼作屏風之用,兩邊分別是兩老的書桌,樂素先生的書桌上堆滿書刊。一進門有張餐桌,配了幾張方凳,還有一對舊沙發和一個碗櫃。裡間是臥室,大約十四平方米,擺著一張舊雙人床,一個衣櫃,一張放檯燈的小桌子,一個有自來水管的洗臉池。廁所在院子裡,距住房五米開外,是公用的。沒有廚房,一個蜂窩煤爐擺在門外的屋簷下,到冬天就將爐子搬進屋裡,安上煙筒,兼作取暖之用。另外還有一間十平方米左右的小屋,在同一排,但隔了幾戶人家,是兩個上大學的兒子週末回家時住的地方,現在成了我的臥室,他們回來,我在大屋搭個鋪。這樣簡陋的陳設(以後又看到周圍幾家都大同小異),就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高級知識分子生活的真實情況。一位受人尊重的歷史專家,物質生活如此簡樸,卻兢兢業業地為教育事業辛勤耕耘,他有著多麼崇高的精神境界啊!

1956年2月3日,在全國政協晚宴上。中為朱文叔。
第二天,美英女士帶我到全院走了一圈,我才知道這裡原是乾隆皇帝的一座公主府。一進大門是一個很大的荷花池,院內還保留有當年的戲樓,現在成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大院。兩座較新的樓是辦公樓,其餘的則是職工宿舍,我們住在大院的最北面,一排平房,住著十餘戶人家,都是樂素先生的同事。慈祥而稍帶嚴肅的樂素先生,除了書籍之外,只有簡樸傢俱的陋室,這就是當年我的第一印象。
我在這裡住了兩年,經過高中補習,考上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搬到了學校。後與智超結婚,成了陳家媳婦,與公公、婆婆共同生活了十幾年,對他們的瞭解與敬愛與日俱增。
二、父親的熏陶教育
陳垣先生二十二歲時得子,為他取名博,樂素之名是後來改的。當時陳垣先生在廣州與友人潘達微、高劍父等合辦《時事畫報》,負責報中文字工作,用“謙益”等含有反滿意味(滿招損,謙受益)的筆名發表了許多反對清朝專制統治、反對列強侵略的文章。為躲避清政府的迫害,他經常轉移住處,因此將兒子留在家鄉由妻子扶養,直到樂素先生五歲時才把他接到廣州。
樂素先生雖然只在家鄉生活了五年,但對家鄉始終懷著眷戀之情。上世紀80年代他曾經回鄉,指著故居右上角的一間廂房,動情地對同行的親友說:“我就出生在這間房子裡。”他還把從新會帶回的茅筆(陳白沙曾用茅草札筆寫字)送給我和智超。
我曾經不止一次地聽見他用濃重的鄉音吟誦陳白沙的詩句:“記得細時好,跟娘去飲茶。門前磨蜆殼,巷口挖泥沙。而今年長大,心事亂如麻。”他閉著雙目,拖著長長的音調,兒歌式的詩句,把他帶回到多年前的童年。他說,這是四五歲時在家鄉學會的,現在已經是六十多歲的人了,但兒時誦讀的詩歌,至今沒有忘記。
1907年樂素先生五歲,陳垣先生把他接到廣州,住在“陳信義”藥材行中,和店員同桌吃飯,學習到了一些有關藥材的知識。他先在“陳寧遠堂”的家塾中學習過一段時間,然後進了教會辦的聖心書院和嶺南小學。他曾幾次談到在廣州這段時間給他印象最深刻的兩件事。他七歲的時候,陳垣先生給了他一套《三國演義》,並讓他把每一回中首次出現的人名和地名寫在書眉上,把他們記熟。這樣閱讀《三國演義》,既鍛煉了記憶力,又接受了中國文史的啟蒙教育。另一件事發生在辛亥革命前不久。有一天,他和比他小兩歲的弟弟仲益,趁父親不在打開他的抽屜,竟發現藏有一把手槍。他們當時只覺得好玩,搶著來玩。不料手槍走火,子彈擦著他的耳邊飛過,砰然作響,好險啊!此事如果走漏出去,還將有殺身之禍。後來還是由一位族叔買了一張船票,在開船前將手槍從廁所中扔進珠江,全家人才算鬆了一口氣。兩兄弟也模糊地感覺到了父親的革命黨人身份。
陳垣先生在民國二年(1913)當選為眾議員,從此到北京定居。樂素先生十四歲(1916)小學畢業,陳垣先生把他接到北京上匯文中學;1918年,又把他和仲益送到日本留學,當時他十六歲。
樂素先生在日本就讀的是東京的明治大學,專業是經濟學。陳垣先生不斷通過書信瞭解他的學習情況,又讓他利用留學的機會,多去聆聽學者的學術報告,並到圖書館幫助他搜集有關歷史的資料。現在還保留著一冊樂素先生當年為陳垣先生抄寫的一部宗教史資料。封面是陳垣先生題的書名“兩眼考”,還有他的批語:“一九一八年六月博兒鈔於東京帝國圖書館”。樂素先生在陳垣先生的熏陶、教育下,逐漸對歷史與文學產生濃厚的興趣,也在記憶力和讀書方法上得到鍛煉,再加上自己的刻苦努力,終於成為眾多弟妹中唯一從事歷史研究與教學的人。
三、從投筆從戎到以筆作槍
在日本留學四年後,樂素先生回國,先後在廣州的南武、培英等中學講授歷史和語文,這是他正式從事教育事業的開始。另外,在課餘時間他系統閱讀了二十四史和《資治通鑒》等基本史籍,為日後從事史學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樂素先生從小就敬仰孫中山先生。1926年北伐前夕,廣州成為當時的革命中心。青年的樂素先生受當時高漲的革命形勢的影響,毅然放棄教職,參加了國民革命軍,在第五軍任政治宣傳員,宣傳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和革命理論。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不但大批共產黨人遭到屠殺,國民黨左派人士也遭到迫害。樂素先生在徬徨苦悶中到達上海,先在民眾煙草公司暫時棲身,不久正式開始了歷史研究工作。
他最初的研究領域是日本古代史和中日關係史。1929年,他出任新成立的《日本研究》雜誌的主編,先後發表了《魏志倭人傳研究》和《後漢劉宋間之倭史》等論文。他所以選擇這個領域,是因為在日本留學時,一方面,對日本學術界重視中國文化,深入細緻研究中國歷史、地理,刻苦鑽研的精神,深為佩服;另一方面,他也覺察到,有些日本學者的研究目的大有問題,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充當日本軍國主義的工具,為日本侵略中國以至亞洲製造輿論。在史學領域,這種情況尤為明顯。他要透過自己的研究,恢復日本古代史和中日關係史的真面目。
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又使他將研究方向轉至宋史。由於當時的當權者採取“不抵抗主義”,東北三省很快就被日本侵略者佔領,而且還步步進逼,華北岌岌可危。中國面臨亡國威脅。作為一名愛國的歷史學者,樂素先生深感有責任從歷史上尋找救亡圖存的借鑒。過去他通讀中國歷史時就已注意到,宋代是一個“外患”頻繁的朝代,有許多情況與當時的現實相似。於是他發憤鑽研,寫出了他的第一篇宋史論文《宋徽宗謀復燕雲之失敗》。文章指出,後晉石敬瑭甘當“兒皇帝”,將幽、雲等十六州割讓與契丹,自嘗惡果,至出帝被擄而亡國。宋徽宗謀復燕雲之舉,在於恢復原有之疆土,“此種思想絕不能謂為謬誤”。至於謀復燕雲之失敗,則在於“當時之君臣實闇弱庸陋”,“事先無縝密之計劃與充分之準備”,非戰之罪。文章還批判了當時的反對派以為在遼金之戰中採取中立態度即可保無事的觀點,反問道:“然則金既滅遼,宋能否遏止其南侵之野心?”宋徽宗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昏君,但對他謀復燕雲之舉,樂素先生作了全面客觀的分析與評價。反觀作此文時的現實,文章的針對性是很明顯的。
在此以後,他又先後在北京大學《國學季刊》和《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上發表了《徐夢莘考》和《三朝北盟會編考》兩篇長文。這些論著奠定了他作為現代宋史研究開拓者之一的地位。
四、艱難歲月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後一個月,又發生“八·一三事變”,日寇進攻上海。樂素先生帶領全家六口匆匆離開上海到香港,這是八年抗戰中的第一次大逃難,當時二兒子剛剛滿月。到達香港後,經許地山先生介紹,樂素先生在英華女子中學得到了一個教職,講授歷史和國文。為了維持一家七口(1939年小兒子出世)的生活,每週授課時間至少二十幾小時,有時甚至更多。即使在這樣繁忙的教學生活中,他仍保持充沛的精力,樂觀的態度。他愛好運動,特別是游泳,能從九龍游到香港。他還抓緊教學之餘的時間,開始了《宋史藝文志考證》一書的寫作。智超曾回憶,在香港的這段時間,父親還讓他們姐弟查閱《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每人分幾卷,將其中提到“宋志”或“宋史藝文志”的地方用紅筆標出。標完之後,交換複查,凡有查出遺漏的,發一件小禮品。有時父親還帶著他到圖書館幫著抄資料。當時他年齡小,不能理解資料的內容,所以就只當作寫字練習。
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並在東南亞全線出擊。原駐守在九龍的英軍全部撤到香港島,從廣州南下的日軍一時還沒有到達,九龍出現了幾天政治、軍事上的真空時期。地痞流氓把這當作千載難逢的發財機會。他們大呼“勝利啦!勝利啦!”劃分地盤,挨戶搶劫,九龍陷入恐怖之中。
樂素先生全家住在九龍通菜街二三八號三樓,這時他的兩位姑姑以及弟弟一家三口都來避難。劫匪把住樓門口,從一樓搶起。樂素先生聽到劫匪從二樓上來,主動把門打開。後來談起這件事,他說這叫“開門揖盜”。因為你不打開門,他們會把門砸開,財物照搶;主動開門,還可以把門保住。劫匪進門,看見滿屋都是書,不禁皺起眉頭,大聲喊道:“你們把錢藏在書裡,叫我們怎麼找呀!”書、輸同音,他們認為不吉利。樂素先生事先已有準備,主要的錢財確實夾在書中,但也在抽屜等明處放了些財物。他聽到劫匪們的談話,突然說了一句:“鄉里,我們以後還有見面的日子呢。”小頭目問道:“你是哪裡人?”答道:“新會石頭。”小頭目不出聲了,匆匆搜索了一下就轉到對門一家葡萄牙人家中繼續搶劫了。全家人正稍稍定下心來,忽然又聽到拍門聲,不知又會出什麼事。開門一看,劫匪下樓了,留下一小袋米。“米來了”,廣東話諧音“不來了”。劫匪以後真的沒有再來過,而附近有的人家被反覆搶劫多次,甚至連牙刷也不放過。樂素先生的從容鎮定,保住全家免遭更大的損失,也令親友欽佩不已。
日軍佔領香港後,學校停課,生活來源斷絕。為了維持一家的生活,樂素先生只好到半山私人別墅裡教授日語。日軍經常突然實施戒嚴,濫殺無辜,他每次去講課,都要冒風險。即使是在這樣艱險的環境下,他也盡力幫助別人。那次劫匪走得匆忙,一大袋放在樓梯腳下的白米居然免遭劫掠,這在當時真是全家的救命糧啊!但當袁同禮先生來訪,久久沒有去意,詢問之下,才知道他家中缺糧,出來找米,又難以啟齒,樂素先生慨然以米相贈。當他知道陳寅恪先生家中斷炊,又帶了一袋米送去。為了順利通過日軍的關卡,他還把當時年僅七歲的智超帶在身邊以作掩護。陳寅恪此後十分念及這段舊情,曾在樂素先生臨離香港前把自己在英國演講時所穿的一套西裝贈送給他,留作紀念。
1942年底,樂素先生應浙江大學竺可楨校長之聘,到當時內遷至貴州遵義的浙大史地系任教。他帶領全家七口,離開日寇佔領下的香港,開始了第二次大逃難。他們經澳門、廣州灣,跨過寸金橋,進入大後方,然後輾轉到達遵義。他在浙大史地系開設了唐宋史、日本史、中國目錄學史等課程。儘管當時物質匱乏,資料又缺,但他精心講授,循循善誘,深得學生的愛戴。
1945年上半年,是內地公教人員最艱難的時候。大學教授的工資只能買米七斗。樂素先生五個子女,四個輟學,孩子們每天幫助美英女士在街邊擺攤出賣家中僅存的舊衣物。儘管生活如此艱難,家中生活偶有改善,他也必定把那些家在淪陷區、生活來源斷絕的學生找來共享。多年以後,這些學生已成為白髮蒼蒼的老人,還懷念老師、師母當年請他們吃的“營養菜”。其實這不過是捲心菜、西紅柿、胡蘿蔔再加少量五花肉而已,但在當時已是難得的佳 ,並飽含了他對學生的一片真情。
,並飽含了他對學生的一片真情。
五、“文革”厄運
抗戰勝利的第二年,浙江大學全校復員回杭州。1952年大學院系調整,浙江大學的文、理學院和之江大學合併,改名浙江師範學院,史地系撤銷,樂素先生任圖書館館長。1954年,他從杭州調到北京,擔任人民教育出版社歷史編輯室主任,同時在新成立的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二所兼任研究員和學術委員。1956年,他主持並和鞏紹英、邱漢生、汪籛、王永興等專家共同精心編寫的高中中國歷史課本正式出版,受到史學界、教育界和全國歷史教師與學生的高度評價,同年2月他還作為教育部三位代表之一受到毛澤東主席接見。
正當他準備和同事們進一步修改、完善全國統一的中小學歷史教科書,並撰寫歷史研究所重點項目“中國史稿”的宋代部分時,“文化大革命”爆發了。“文革”對全中國人民都是一場災難,知識分子是首當其衝的一部分。樂素先生在“文革”中經受過多次衝擊。
“文革”一開始,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樂素先生被定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而且還是“反動權威”陳垣的“孝子賢孫”。當時造反派還追問一件事,這樣的“反動權威”怎麼會鑽到“林副主席”身邊?原來,1962年左右,歷史所按中央軍委的要求,選了幾位研究人員為林彪的妻子葉群講歷史課,樂素先生也去講了幾次。這件事當時嚴格保密,智超和我都不知道。到林彪折戟沉沙之後,它又變成了“投靠”林彪的“罪行”。

樂素、仲益、約、容四兄弟在興化寺街5號院,時為1950年。

1954年調至人民教育出版社,與夫人及女蓮波、子智仁、智純合照於北京。

1957年5月攝於北京香山香爐峰。

1962年回廣州,與弟合照。

1959年攝於興化寺街5號院內。陳垣先生抱者為曾孫超英。
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樂素先生有一天突然失蹤了,美英女士焦急萬分。後來才知道被出版社的造反派“隔離審查”了,就關在大院的洗澡房內。緊接著就是兩次抄家和封存辦公室,許多珍貴書籍至今沒有下落。這一關就是四個月,罪名是“國民黨特務”。原來樂素先生在浙大的一位老同事,在杭州大學,“清理階級隊伍”時被屈打成招,把浙大教授會的成員都供作特務。
因為查無實據,造反派只好把他放出來,但馬上又被打發到安徽鳳陽教育部“五七干校”去接受勞動改造。當時他已年近古稀,但白天要挑幾十擔水供全連(干校按軍事編制)使用,還要送報送信、夜裡則經常要到稻田值班看水。有一次挖開田埂放水,因為天黑,鐵鍬傷腳,血流如注,傷口見骨,他忍痛堅持到天亮接班人的到來。
1971年“九一三”林彪自我爆炸以後,樂素先生接到勒令退休的通知。他想回北京,但當時領導干校的軍宣隊宣佈,只能安置到縣以下的地方。最後考慮到他年紀已大,才“開恩”讓他回到曾經工作、生活過多年的杭州。
雖歷經種種磨難,他身體不垮,精神不倒,因為他自信一生無愧,把這些磨難當作對身體和意志的鍛煉。回杭州後,幾乎天天步行十幾里到浙江圖書館看書,繼續進行《宋史藝文志考證》的寫作。
六、老當益壯
1976年“文革”結束,“四人幫”垮台,知識分子得以在比較寬鬆的環境中工作。1978年,浙江省為一批老知識分子重新安排工作,樂素先生是名單中的第一位,擔任杭州大學宋史研究室主任,並被選為浙江省歷史學會會長。次年又照顧他葉落歸根的願望,把他調到新復校的暨南大學,以後又請他負責籌辦古籍研究所。1980年他被選為中國宋史研究會副會長,1982年擔任國務院古籍整理規劃小組顧問。1984年他到香港參加宋史國際研討會,與闊別多年的浙大老學生宋晞重逢,還會見了海外一些久慕其名的中青年宋史研究同行。

1976年自杭州來北京看書,攝於智超家中。

1976年與智超合照。

1976年與智超、慶瑛合照。

1978年與智超合照於毛主席紀念堂前。

1978年與智超、慶瑛合照。
“文革”以後樂素先生進入了他一生的第二個創作高峰,發表了《宋代客戶與士大夫》、《流放嶺南的元祐黨人》、《袁本與衢本〈郡齋讀書志〉》等十幾篇論文,結集出版了《求是集》一、二集兩本論文集,並對《宋史藝文志考證》作最後定稿工作。
1979年他調到暨南大學時已是七十七歲高齡,他不只一次滿懷信心地對人說:“今人八十不算老,我至少還要再干十五年。”我原來對此也是很有信心的,因為我親眼看到,樂素先生與同年齡時期的陳垣先生相比,健康狀況要好得多,而陳垣先生即使經歷“文革”的磨難,也享年九十一歲。但萬萬沒有想到,樂素先生竟在1990年7月20日還差一個月八十八足歲時,因肺部感染而病逝了。事後細想,樂素先生如果能適當考慮自己年事已高的現實,量力而為,壽命超過他父親是沒有問題的。
樂素先生一生喜好運動,青年時還練過健美運動,很少生病。直到晚年,還堅持每天至少步行萬步。登山爬樓,許多中青年都趕不上。有的人是“不知老之將至”,他則是“不知老之已至”。逝世後檢查他的遺物,沒有發現任何遺言,他根本沒有考慮有朝一日的身後事。這反映了他的灑脫,也反映了他對自己身體狀況的高度自信。
七、我的遺憾
無論是在我和智超結婚之前,還是以後成為他的兒媳,樂素先生都把我當做他的子女。我考入中央民族學院,他和美英女士親自送我到民族學院報到,而他們自己的兩個兒子入學,都是自己扛著行李去學校報到的。我大學畢業走上工作崗位,他又把自己珍藏多年的一套線裝《資治通鑒》送給我,勉勵我好好讀書、工作。
回顧我和公公相識、相處的三十多年,有三件令我終生遺憾的事。
第一件事發生在我到北京後不久,樂素先生和美英女士真誠、親切,很快就消除了我當初的懼怕和拘謹。但當時我年紀還比較小,在一個與我過去經歷完全不同的環境住下來之後,又感到難以適應。即使像吃飯這樣的生活常事,我是雲南人,喜歡吃辣,口味也比較重;他們是廣東人,口味清淡。吃飯時,兩老自然是用他們習慣的廣東話交談,剛開始時我簡直像聽天書(後來我正是透過這種餐桌談話聽懂了廣東話)。諸如此類的事使我想家鄉,想同學,心情不好。以致有一天我把自己關在小屋子裡,蒙頭大睡,不吃不喝。美英女士急性子,見我不出來吃飯,給我送飯,我不理。第二天,她急得不行,把樂素先生搬來,我還是不理。他說:“小瑛,不吃飯可不行。我把飯放在窗台上,你自己拿去吃。”我還是不理,飯在窗台上擱了兩天。鄰居孫士詒先生也是位老編輯,他看不過去了,跑來敲我的門說:“你知道你在跟誰發脾氣嗎?樂素先生是我們全社都尊重的老專家,誰都不敢、也不會去頂撞他。你這黃毛丫頭,他給你送飯都不吃!你再不出來,我就把門砸開!”聽了他的話,我終於覺悟到自己太任性了,於是開門吃飯。樂素先生見我走出來,一句責備的話都沒有,只是說:“你還年輕,要好好愛護自己。”使我感到無比溫暖,也深深自責。
第二件事是我與他發生的唯一一次衝突。那是在“文革”爆發以後,原來安詳寧靜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大院,一時變得殺氣騰騰。造反派在揪斗“走資派”、“牛鬼蛇神”,大中小學都停課鬧“革命”,紅衛兵四處串聯,小孩子則跟在大人後面瞎鬧,以後更被某些別有用心的人當做整人的工具。“牛鬼蛇神”的孩子說了一句當時的“錯話”,造反派就借此對他們的家長大肆討伐。
我的孩子還小,在家待不住,總喜歡跑到大院去玩,時常被大孩子打罵。樂素先生心疼孫子,也怕他“闖禍”,要我每天把他帶去上班。我們學校也無例外地在鬧“革命”,不讓帶孩子上班,我只好把他放在學校附近的月壇公園,讓他在那裡看小人書,下班時再把他帶回家。頭三天總算平安無事。第四天下班後我到公園去接他,四處不見人。一個士兵看見我焦急的樣子,問我是不是找孩子,我說是。他帶我到一個拐角處,指著縮成一團的兒子說:“是他吧!你怎麼不好好管教他?他鑽進電視轉播塔裡,這是機密重地,要不是看他年紀小,早就把他抓走了!”他要我把單位、姓名、地址等登記下來,才讓我把兒子帶走。回家路上,我看孩子滿面淚痕,問他是不是挨打了,他點點頭。我心裡非常難過,我無可奈何,我只有把他留在家裡。第二天我去上班,樂素先生見我沒有把孩子帶走的意思,提醒我把他帶走。我說以後就讓他留在家裡。他說:“不行!你沒有看見大院亂成什麼樣子!”我再也忍不住了,邊哭邊訴說昨天的事,並說:“有家不讓待,還算什麼家?要把他放在大街上,你去放好了!”他沒有再說話,我一甩門就走了。不久他就被造反派抓走,孫子的事想管也管不了。事後回想,我雖然無可奈何,但對他當時的處境和苦衷也理解不夠,總有負疚之感。樂素先生歷經風浪,每次在危急關頭總是鎮定從容。但“文化大革命”在許多方面都超出了常規,使他無所適從。他處境已經險惡,還要盡力保護老父、愛妻、子孫,至少也要使他們免遭新的打擊及迫害,於是處處小心,處處提防。但在當時的大背景下,這些努力總是徒勞。這不僅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整個知識界的悲劇。
第三件事是我未能見他最後一面。智超是1990年7月18日得到他病重的消息的,連夜從北京趕飛廣州,到家已是19日凌晨。19日白天智超都在病床邊,樂素先生談話雖然吃力,但精神還不錯,沒有想到20日上午便離開人世了,當時我在巴黎進修,智超在電話中告訴我這悲痛的消息,我半晌無言,只能在萬里之外默默地祝他走好。
2000年11月,我和智超到江門市參加紀念祖父陳垣先生誕生一百二十週年的學術討論會,以及陳垣故居被批准為新會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揭幕式。我們約定,歸程一定要在廣州停留一天,以了卻我十年來的一樁心願。我們去了銀河公墓,在公公靈前獻上了一束遲來的鮮花,以表達我的思念之情。
這麼多年又過去了,這篇短文,就是我獻給他的一炷心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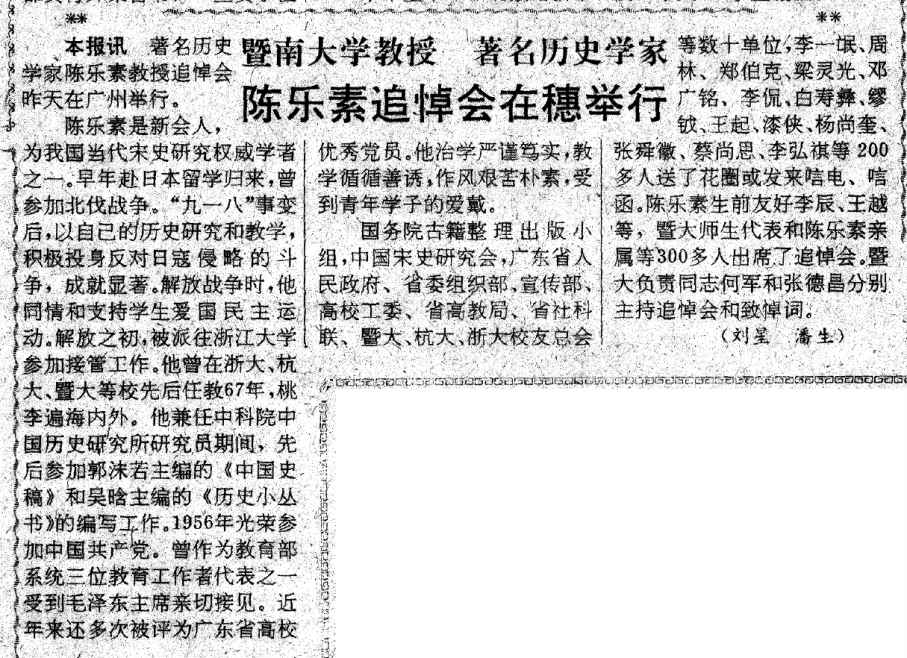
1990年《羊城晚報》報道追悼會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