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須有」,是南宋奸臣秦檜等人陷害民族英雄岳飛所創造出來的一個詞,多年來一直與岳飛冤案相伴,今天有人將此與王世襄在「三反」等運動中遭受冤屈相比較。其實,細究「莫須有」這三字的含義,是指可能有也可能沒有的意思,而王世襄是被查明確實沒有者,故使用這樣一個詞彙似有不妥。妥與不妥,反正王世襄在遭受長達十四個月「莫須有」的審查和監禁之後,已經是身染重病並被逐出了他矢志為之奉獻的故宮博物院,而不得不自謀出路了。

王世襄編著的《中國古代音樂目錄》
關於王世襄的自謀出路,不知道還有誰不是從那紙開除其公職的通知上進行字面理解的,筆者不反對從字面上理解為尋找一份工作之意,但是卻更願意解釋為王世襄自謀事業和人生的出路,這從他隨後矢志研究中國文化的歷程與成就中可以得到印證。不過,從下面開始王世襄不得不將正業圈定在中國古代音樂研究上,雖然他的副業即除了音樂之外的文物學等才是他所謀的真正出路,但是此後八年間他必須將正常工作時間交付給中央音樂學院民族音樂研究所,因為這是暫時「收容」他的「避難所」。
1954年,遭受人生和事業重大挫折的王世襄,一度在心靈和身體的病痛中掙扎,經過一番極為沉痛的深思熟慮後,遂決定「把終生為故宮服務的志願,改為終生研究中國文化」,這是王世襄人生中的第二次轉變。關於這次人生轉變,筆者在首次拜訪王世襄王老時就曾聽其講述過,雖然看似一次風生談笑,但隱約中還是能夠聽出一絲遺憾在老人心中飄蕩。
舊事畢竟過去了半個多世紀,今天的回憶只為了這種回憶今後不再發生,所以現在還是進入本章正題為好。是的,就在王世襄調養身體和人生病痛的一年間,中央音樂學院民族音樂研究所由天津遷到了北京西北郊的學院路,所長楊蔭瀏和副所長李元慶得知王世襄與著名古琴家管平湖先生交往深厚,遂找到他介紹其進入該所成為研究員,不久又聘請王世襄為該所副研究員。從此,王世襄開始了他歷時八年之久脫離專業文物學研究之正途,而暢遊在民族音樂的歷史長河中。
既然被民族音樂研究所「收容」,王世襄便根據研究所的工作性質並結合自身對文物古籍較為精熟的優勢,主要從事中國音樂史方面的整理與研究。比如用時三年編著由人民音樂出版社陸續出版了《中國古代音樂史參考圖片》(一輯至五輯),從而為中國古代音樂史研究提供了一套極為珍貴的圖片史料。對此,筆者不能在本傳中為讀者提供這些圖片欣賞,只能從王世襄進入民族音樂研究所不久後參與佈置古代音樂史料陳列室一事中,找到他開始從事中國古代音樂研究的一些軌跡。
就當時國情而言,圍繞中國音樂史中一些較為重要的問題,按照時代順序通過實物、樂譜、書籍和圖片等內容的綜合陳列,必要時配以播放錄音的方式,來展示中國音樂文化的發展與成就,還是一件沒有任何比照的前所未有的新工作。不過,王世襄豐富實際的陳列經驗和勇於開拓的工作精神,使他很快就理清了佈置這一陳列室的工作思路,那就是除了序幕之外,將中國音樂發展史上起殷商下逮清末,分五個部分選取各具代表特色的文物和史料,對中國音樂發展成就進行全方位的形象陳列和展示。比如,在表示殷商時期中國音樂已經發展到一定高度的這一問題上,不僅在陳列的最前面擺放了從山西荊村發掘出土的新石器時代原始陶塤這種樂器的照片,以說明殷代的塤等樂器有著久遠的歷史淵源,還選取有關音樂的甲骨文字摹制拓片及其卜辭內容,來闡明古代樂器及樂舞的應用等關係;比如,在兩周和春秋戰國時期的陳列中,主要從先秦的音樂思想和兩周的樂律成就、樂器發展、音樂機構、樂隊及聲樂等方面,從古代有關典籍中爬梳出史據翔實而權威的解說和展示,特別是通過故宮博物院所藏戰國宴樂漁獵壺,以及中國科學院從河南輝縣發掘出土的銅鑒等實物上繪有樂隊演奏的畫面與花紋等,對當時樂隊敲擊鐘磬等樂器的這種演奏場景進行了真實寫照;比如,在表現秦漢至南北朝時期音樂成就的展示牆上,懸掛有包括漢畫像磚拓片及敦煌和麥積山北朝壁畫摹本等諸多有關音樂的照片,給人以比較全面直觀的印象;比如,在表現中國古代音樂發展輝煌大氣的隋唐時期,不僅通過一些樂器實物和壁畫、繪畫摹本等來說明這一時期中國音樂之偉大成就,還將中國音樂對諸如日本和朝鮮等周邊國家的深刻影響,進行了比較生動的說明和展示;比如,關於五代至清末中國音樂發展方面的成就,除了以突出地位陳列了中國第一部音樂百科全書——宋陳暘的《樂書》等典籍外,還對戲曲、宗教音樂和昆曲等作了比較全面深入的陳列和展示。
如果細細梳理該陳列室之特點,雖然王世襄評價說這只是一個初步的嘗試,還有許多需要修改和補充的內容,但是即便拿今天的眼光來看,也不失為一個脈絡清楚、重點突出、豐富多彩的比較成功的陳列和展示。
不過,既然王世襄認為這只是一個初步的嘗試,那麼必然還有他認為需要完善和充實的地方,而完善和充實的方式則來源於實際調查,這完全符合毛澤東那句當時乃至如今都遵行不悖的真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意旨。因此,一場歷時五十天的民族音樂普查活動首先從湖南展開,王世襄作為三個普查小組中的一員隨隊前往湘南。是的,遭到冤獄之災後一直生活在沉悶中的王世襄,實在需要到外界特別是北京這個政治氣候濃烈的首都之外去呼吸一下新鮮空氣了,這是他發憤向學以來第一次放鬆心情回到他昔日鍾愛的遊樂之中。說是遊樂,這完全可以從《我愛江華》這一回憶文章中體味得到。
1955年11月成立的江華瑤族自治縣,位於沱江支流東江與一條小河交匯處的湘南山區,是一個有山有水自然景致秀麗的好地方。當時王世襄等人從道縣前往江華,步行三天的時間才到達。但是這一點兒也沒有讓他感到辛苦,反而讓他留下了這樣一段記述當地風情的優美文字:
第三天,只剩四十里路,心情輕鬆得多,大家放慢了腳步,瀏覽路上風景。東江裡的船隻,有滿載貨物卻輕如一片葉子的下水船;有六七人背纖、四五人跳在水中抵住船身與激流搏鬥的上水船;有由幾百根杉木紮成向下溜去的木排。最安閒的要算漁船了,篷上及兩舷蹲著黑色的大魚鷹子,有的縮著頭睡覺,有的用嘴梳理翎翅,它們要到夜晚才開始一天的工作。一路植物茂盛,絕大多數叫不出名字。有一種秋海棠,石壁上一長就是一片,它的花葉比普通人家種的都要細弱些,但花莖瘦長,風姿很幽媚。還有野荼蘼,白色繁花,像一匹輕紗似的搭在三四丈高的樹上,爬過樹梢,又倒垂下來,低拂水面,江風吹過,香氣散滿山林。
在這種今天已經難得一見的鄉野風情中,王世襄等人來到了當時還不足一千人的江華縣城,隨後在縣文化館館長謝琦的陪同下,前往一個名叫屋背沖的瑤胞聚集區訪查。在這裡,王世襄一行受到了瑤族同胞盤盛朝全家及鄉鄰們溫馨而熱情的接待:
女主人端出洗臉水請我們洗臉,搪瓷臉盆是新的,雪白的手巾,胰子盒裡還放著香皂。過一陣,又請我們去洗澡。浴室是用杉木圈成的一個圍子,西北角有一個大水桶,竹筒引著山泉日夜往桶裡流;東邊有一座專燒洗澡水的灶頭;中間放著浴桶,有半人多高,洗澡水冒著熱氣。我們在長沙時就聽民族事務委員會的同志講過,瑤胞請客人洗澡是表示親熱之意,客人一定得接受這種邀請,否則,就會被主人認為見外的。
天還沒有大黑,主人點亮了蓋著白玻璃罩的大煤油燈,掛在堂屋中央,接著就擺出一席豐盛的晚餐:兩大碗臘肉,一碗臘雞,四碗豆腐和一碗和著蒜泥的辣椒醬。味道很美。每人面前還有一盅紅芋酒,微苦,咽後卻又回出甜味來,還帶一些烤白薯的香味。白米飯,每碗盛得出尖。主人慇勤讓客,我們毫不拘束地大嚼了一頓。
飯後飲了主人自己焙的綠茶。江華的茶是有名的,味像龍井而還要猛一些。這時,屋背沖的幾家鄰舍都來了,堂屋裡坐滿了一圈人。他們聽說我們是從北京來採訪音樂的,很快就組織了一個精彩的晚會。盤盛朝的本家哥哥盤盛興是這村的嗩吶名手,幾個小伙子,夾著鑼鼓鐃鈸,隨著他來了。他先給我們奏了幾支瑤族嗩吶曲,其中有火熾歡騰的《萬馬過橋》,抒情的《蜜蜂過嶺》和《毛票花》等。曲調和漢族的嗩吶曲雖有相似之處,但還是有它自己的高亢開朗的風格。
大家越玩越高興了。盤代清(盤盛朝的納贅女婿)從箱子裡取出傳家的民族服裝來給跳長鼓舞的人穿。瑤胞的民族服裝可真好看呀!頭帕、褂子、圍裙和褲子是一套,在那深藍色的粗布上用紅綠白線繡著各種花紋,很美麗,也很諧調自然。長鼓舞是瑤胞在舉行盛大儀典「盤王宴」時跳的舞,由四人或兩人集體表演。舞者穿著美麗的服裝,一手拿長鼓,一手打節拍,並做出蓋頂、圍肩、纏腰、繞膝種種舞姿。這時樂隊奏起嗩吶,敲著鑼鼓,曲聲、鑼鼓聲由徐而疾,舞蹈也跟著逐節發展;到達最高潮後,忽然又慢了下來,終於回到了輕盈婆娑的步伐。這種有著悠久傳統的民族舞蹈,充分表達了瑤胞熱愛生活的快樂健康的感情。
長鼓舞舞罷,接著唱起《盤王歌》來,曼長而嘹亮的歌聲,非常動人。我翻了一下《盤王宴歌書》,它是用瑤語和漢語夾雜寫成的,雖不能完全看懂,但約略可知書中大意。開始是講瑤族祖先的歷史,記述他們如何與自然災害作鬥爭;後面則是平時愛唱的山歌。我記出這樣一首:「後生年少少年時,不作風流到幾時?不信便看黃竹葉,落了何曾轉杵(上)枝?」這首歌詞難道不能和著名的古詩《金縷衣》——「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媲美嗎?
晚會進行到深夜才曲終人散。熱情的主人把最好的兩間臥室讓我們住。新棉被,新褥子,初夏的山中夜晚,還是用得到的。這晚我睡得很香甜。
黎明的時候,山鳥叫醒了我,披衣走出房門,不禁大叫起來。看吧,面前是茫茫的雲海,吞吐著無數峰巒,一陣山風吹過,白雲飛來了,山峰露了面。又一會兒,忽又飄來一幅輕紗,緩緩地舒展、舒展,在山邊邊上繞了一個圈子,而後和山峰下升起來的雲霧連成一片,整個山空,又給籠罩了起來。雲霧的動盪使人覺得峰巒也在搖晃,一切都彷彿是幻境,然而卻是大自然的真實。
試想,在如此真實而美妙的音樂采風中,王世襄的心情怎能不歡暢起來,他的心靈又怎能不得到純淨呢?當然,敬業的王世襄在歡愉中從來也沒有忘記自己的責任,那就是通過此次音樂普查對中華民族音樂進行系統的整理和研究,所以便有了連載於1956年11月1日、2日《光明日報》上的一篇調查報告。在這篇題為《普查民族音樂的開端——記湖南音樂的普查工作》一文中,我們不難看出王世襄對於民族音樂的喜愛,以及因為熱愛而取得的豐碩的研究成果。
在這篇文章中,王世襄總共記述了八個方面的普查內容,即歌曲、風俗音樂、宗教音樂、說唱、戲曲、器樂以及樂譜、樂器和有關音樂方面的文獻等,真可謂是琳琅滿目,美不勝收。比如,歌曲方面單是表現勞動生產,王世襄就羅列出了划船、挖山茶、插田、耒田、車水、鋤草、放牛、趕腳、扯爐、打鐵、捕魚、打獵、紡棉、採菱等形式;至於內容最為豐富的風俗音樂,王世襄重點列舉了婚慶喜歌,比如在文章中他這樣寫道:
婦女在出嫁前幾天就要舉行「坐歌堂」,來參加的是新娘的姊妹和女伴。到夜間,她們圍坐中堂,輪流歌唱,有的傾訴離別的感傷,有的感歎自身的遭遇,有的埋怨父母包辦婚姻,有的咬牙切齒咒罵媒人,曲調和歌曲都反映出過去婦女被壓迫的痛苦。突出的例子是嘉禾縣的《伴嫁舞》,連舞帶唱,全部過程要兩夜,傳統的歌詞有七首長詩,大膽而有力地抨擊了舊社會不合理的制度。出嫁,在過去的母女看來就是生離死別,所以有「哭嫁」的風俗,兩人互相遞唱,真是一字一淚。這些封建時代的東西,雖然早為新社會所遺忘,但是這次請來表演「哭嫁」的老婆婆,起先是一面笑一面裝著哭,漸漸回憶到以往的情景,悲從中來,不禁撲簌簌落下眼淚,終至嗚咽不能成聲,可見當時悲慘的生活是怎樣深深地隱藏在受過壓迫人的心中。男家的婚禮音樂如《迎親》《拜堂》《花燭贊》《捧茶歌》《賀新郎》等,有的是活潑的器樂,有的是朗誦性的讚歌,它們都洋溢著歡欣的氣息。
當然,對於風俗音樂的普查,王世襄等人沒有單純地將其分門別類,而是著重從生活的角度進行普查和研究,因此也就比較容易理解其產生與發展的過程。關於以往乃至現在依然不大被人們關注但卻最容易遭到否定的宗教音樂,王世襄等人在普查中明白,宗教音樂不僅反映了人民群眾對生活的要求,而且還與民歌有著極為深厚的淵源,甚至有的民歌如果不通過對宗教音樂的研究則無法釐清其來龍去脈。
另外,針對宗教音樂和風俗音樂正在逐漸消失的現狀,王世襄在文章中發出了呼籲:「現在已經到搶救的時候了,否則一旦絕響,將成為不可彌補的損失。」不幸的是,正如王世襄半個多世紀前所預言的那樣,不僅湖南的許多宗教音樂和風俗音樂已經消失無尋,而且在中國的諸多地方也可以說是已經絕響了。在這裡,還想列舉關於器樂方面一例,那時在湖南到處流行的吹葉,王世襄列舉了南瓜稈、麥稈、稻稈、酸桐管、棕葉、樹皮、號筒管(原註:一種植物,類似向日葵,梗子可以吹出不同的高音來。筆者以為,應該是名為「蒿桐管」而非「號筒管」,蒿桐是一種原注所描述之植物),等等,由此可見勞動人民確實是民族音樂的真正創造者。湖南的這次音樂普查,讓王世襄對民族音樂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和理解,也為他隨後對民族音樂研究起到了一種深化作用。不過,對癡心文物學的王世襄來說,他所從事音樂研究的路數依然不能脫離從文物與典籍方面著手,當然這也是極為正確且頗有成效的一種治學方法,因此下面不能不轉入他在這方面的研究成就。
1957年6月,王世襄與民族音樂研究所的同人前往河南信陽,對不久前河南省文物工作隊在此清理發掘的一座戰國楚墓出土的古代樂器進行考察。歷時十天的實地實物考察,由王世襄執筆的《信陽戰國楚墓出土樂器初步調查記》一文,發表在1958年第一期的《文物參考資料》上。
在這篇調查報告中,王世襄分「楚墓概況」「編鐘」「瑟」「鼓」和「結束語」五個部分對信陽戰國楚墓出土樂器進行了整理和研究,其中重點是中間三個部分。比如關於編鐘方面,王世襄對編鐘的形態、鍾架和鐘槌等實物進行了翔實記述與考證,還因為出土編鐘竟然沒有絲毫銹蝕,且數目與同墓出土竹簡中所記載的數目相符,而得以利用這些實物進行了比較精準的測試和錄音,這在以往考古案例中是難以想像的。比如在對出土三個瑟的研究上,王世襄參照以往出土實物和文獻進行了極為科學可信的研究,特別是對於小瑟上那精美絕倫的彩漆圖繪,王世襄寫有一段論述詳盡、考證宏博的文字:
瑟上漆畫,也採用樂舞場面作為題材,它的位置在額部的立牆上。作樂人殘存兩排。上排自右而左:第一人跪地吹笙,笙斗很小,吹口很長,極像《長沙古物見聞記》中所繪的楚匏。笙管用紅、褐兩色畫成,下聚上散。它與現在還有人使用的葫蘆笙頗為接近。以下三人,因漆皮殘缺,所事不詳。第五人手揮雙槌,作敲打之狀;在他的左側,還能看見一個鼓的上緣(鼓腔)及右邊(鼓皮面)的輪廓。鼓上有羽葆璧翣,形如飛龍,飄揚在這排作樂人的頭上。鼓的下部已殘缺,但從形狀來看,應該是一個中貫立柱的建鼓。第六為舞人,穿著紅色帶黃點的服裝,臂裊長袖,姿態翩翩,與漢東安裡畫像的舞人非常相似。下排第一人在彈瑟,白色的瑟弦和一手按弦的姿勢,都能看清楚。第二人似在拍手唱歌。第三人肩荷一物,可能是一具短瑟,因為肩後的紐狀一物,頗像瑟尾的木枘。第四人也好像拿著一件絃樂器,但形象已不全。第五人跪在一個架子下面,可能在打鍾或擊磬,也因漆片殘缺而無法肯定。這一塊漆畫殘片,和宴樂漁獵壺及輝縣出土銅鑒上的花紋,都是這一時代傳下來的極為可貴的音樂圖畫。
對於這座戰國楚墓中出土的兩個鼓的鼓腔殘片,王世襄從其上殘存的竹釘上可知當時蒙釘皮革的方法,還從一虎形木座上立有鷺鷥的圖案而明瞭鼓的裝飾及安置方法。
如果說王世襄對信陽這座戰國楚墓出土的幾件樂器之研究還嫌單薄的話,那麼他對漢代石刻畫像中樂舞方面的研究則大大推進或精深了一大步,這從現存中央音樂學院查阜西紀念室中由王世襄所撰的一曬藍本文章中可以獲證。在這篇題為《從漢代畫像中所見的一些古代樂器和奏樂舞蹈的場面》一文中,王世襄分別對古代樂器、奏樂場面和舞蹈場面進行了極為深入的研究與論述,不僅在文字上體現了其引經據典和考據翔實的一貫治學作風,而且在利用圖像方面也堪稱選例精當、豐富多彩。同樣,因為不易在此讓讀者獲見這些珍貴圖像的緣故,下面只好用文字將王世襄在這篇文章中所顯露出對樂舞方面的研究成果,進行一次不甚精當的粗淺簡述了。
對古代樂器,王世襄將其分為「金之屬」「石之屬」「革之屬」「弦之屬」「竹之屬」和「匏之屬」六類,每類又有細化之分,這使其中每種樂器能夠得到具體的闡述和考證,也使諸多今天已經絕見之樂器得以清晰地呈現在人們眼前。比如,「金之屬」中的「鐸」這種樂器,《論語》中有「天將以夫子為木鐸」之記述,其註解為:「木鐸,金口木舌。」對此,唐蘭先生在《古樂器小記》中詳細解釋說:
自漢以下,鐸之用甚廣。有施於牛馬者:著錄甚多,晉荀勖以趙郡賈人牛鐸定樂,即此類。有施於屋簷者:《古鑒》所著錄簷鐸是也。其制大率與鍾同,唯較小;且鍾上為甬,而鐸為環狀之紐耳。
因此,王世襄具體地指出:「所以鐸是掛懸的小鐘,其中有舌,由其本身的搖動與舌相擊而發音。」不過,在漢畫像中王世襄又發現與以上不同之情況,那就是肥縣孝堂山畫像中一種懸掛在兩面楹鼓之下的下口呈弧形的鐸,因為不知其中間有無舌之故,而不敢斷定「當名之為鐸抑小鍾」也。比如,在「革之屬」中王世襄真可謂是條分縷析,竟然將鼓分為「楹鼓」「車上的楹鼓」「船中的楹鼓」「獸鼓」「懸鼓」「鞞鼓」「鼗鼓」和「般鼓」等八種,並對每一種鼓都做出了極為詳盡的考釋。其中,關於「楹鼓」王世襄採信了陳暘《樂書》中「鼓之制,始於伊耆氏少昊氏,夏後氏加四足謂之足鼓,商人貫之以柱,謂之楹鼓」的說法,還聯繫建築術語中「楹」即為屋柱之意,將「楹鼓」解釋為「即鼓腔中貫立柱的鼓」,這就讓人們對此有了更為通曉明白的認識。與引經據典解釋一種鼓的歷史及形制有所不同的是,王世襄在解釋「獸鼓」時直截了當地說:「這是一個杜撰的名詞,指雙人騎在獸背敲打的那一種鼓而言。」至於今人幾乎從未聞知的「鞞鼓」和「鼗鼓」,王世襄在採信《詩經》中所述之基礎上,又參照現代聞人對其較為可靠之解釋,最後才謹慎地予以定論。比如在詮釋「鞞鼓」時,王世襄這樣寫道:
《詩經·有瞽》有「應田懸鼓」句,注稱:「應,小鞞也。田,大鼓也。」又稱:「田,當作朄,朄,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近人聞一多認為鞞是小鼓類的總名。所以,現在稱這一類小鼓為鞞鼓,或不致大誤。
至於「鼗鼓」,王世襄在採信《詩經·有瞽》中「鼗磬柷圉」之「鼗如鼓而小,有柄兩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註解外,還通俗易懂地指出「這實在與現在兒童所玩的撥浪鼓和北京賣布販所用的大鼗小鼗是同類的樂器」。關於「般鼓」,王世襄根據後漢傅毅的《舞賦》和唐李善的註解,得知平置於地上以供人在上面跳舞的鼓即為般鼓。由此,我們還可以從原載於1956年9月由人民音樂出版社出版的《民族音樂研究論文集》第一集中王世襄撰寫的題為《傅毅〈舞賦〉與般鼓舞》的文章裡,洞悉其善於觸類延伸的學術研究特點。既然本章標題中有「史話樂舞」一說,在此解析王世襄關於般鼓舞之研究,也就順理成章了。當然,王世襄在史話樂舞時確實非常諳熟從史料典籍中對般鼓舞進行詮釋,因此在這裡不妨先引錄其翻譯《舞賦》中一段關於曼妙歌舞的白話文:
當舞台之上,可以蹈踏出音節來的鼓已經擺放好了,舞者的心情非常安閒舒適;她將神志寄托在遙遠的地方,沒有任何的掛礙和拘束。舞蹈剛開始的時候,舞者忽而俯身向下,忽而仰面向上,忽而跳過來,忽而跳過去,儀態是那樣的雍容惆悵,簡直難以用具體的形象來形容。再舞了一會兒,她的舞姿又像要飛起來,又像在行走,又猛然聳立著身子,又忽地要傾斜下來;她不假思索的每一個動作,以至手的一指,眼睛的一瞥,都應著音樂的節拍。輕柔的羅衣隨著風飄揚,長長的袖子,不時左右地交橫,飛舞揮動,絡繹不停,宛轉裊繞,也合乎曲調的快慢。她的輕而穩的姿勢,好像棲歇的燕子,而飛躍時的疾速,又像受驚的鵠鳥,體態美好而柔婉,迅捷而輕盈,姿勢真是美妙到了極點,同時也顯示了胸懷的純潔。舞者的外貌能夠表達內心——神志正遠在杳冥之處遊行。當她想到高山的時候,便真峨峨然有高山之勢,想到流水的時候,便真洋洋然有流水之情;她的容貌隨著內心的變化而改易,所以沒有任何一點表情是沒有意義而多餘的。樂曲中間有歌詞,舞者也能將它充分表達出來,沒有使得感歎激昂的情致,受到減損。那時她的氣概,真像浮雲般的高逸,她的內心,像秋霜般的皎潔。像這樣美妙的舞蹈,使觀眾都稱讚不止,樂師們也自歎弗如!
單人舞畢,接著是數人的鼓舞,她們挨著次序,登鼓跳起舞來,她們的容貌服飾和舞蹈技巧,一個賽過一個,意想不到的美妙舞姿,也層出不窮,她們望著般鼓則流盼著明媚的眼睛,歌唱時又露出潔白的牙齒。行列和步伐,非常齊整,往來的動作,也都有所象徵的內容,忽而迴翔,忽而高聳,真彷彿是一群神仙在跳舞,拍著節奏的策板,敲個不住,她們的腳趾,踏在鼓上,也輕疾而不稍停頓。正在跳得來往悠悠然的時候,倏忽之間,舞蹈突然中止。
等到她們回身再來開始跳的時候,音樂換成了急促的節拍。舞者在鼓上做出翻騰跪跌種種姿態,靈活委婉的腰肢,能遠遠地探出,深深地彎下。輕紗做成的衣裳,像蛾子在那裡飛揚。跳起來,有如一群鳥,飛聚在一起;慢起來,又非常的舒緩。婉轉地流動,像雲彩在那裡飄蕩,她們的體態如游龍,袖子像白色的雲霓。當舞蹈漸終,樂曲也將要完的時候,她們慢慢地收斂舞容而拜謝,一個個欠著身子,含著笑容,退回到她們原來的行列中去。觀眾們都說真好看,沒有一個不是興高采烈的。
這種出神入化的舞蹈,王世襄在《舞賦》的詞語中得以享受,還從五幅漢畫像中尋找到了具體而生動的影像,從而使般鼓舞這種在唐代就已經不為人們所熟悉的舞蹈,重新被人們認識並對其產生濃厚興趣,更促成舞蹈家和音樂家把其潛心發掘出來。
既然寫到了舞蹈場面,還想就王世襄從漢畫像中對其他幾種舞蹈場面的研究作一介紹,比如長袖舞、百戲舞和雜舞等。在考釋這三種舞蹈時,王世襄主要從不同伴奏樂器這一角度進行了分類和考釋,比如他將長袖舞分釋為「琴伴奏」「琴笙伴奏」和「楹鼓伴奏」三種,將百戲舞分釋為「楹鼓、琴、笙、簫、鼗鼓伴奏」「楹鼓、琴、笙伴奏」和「楹鼓、簫、鼗鼓、應鞞伴奏」三種,將雜舞也分釋為「琴、笙、簫、鼗鼓、篪伴奏」「楹鼓、琴、笙、簫、鼗鼓、管、篴伴奏」和「獸鼓及他種樂器伴奏」三種。至於般鼓舞,王世襄則是從跳舞人數不等而進行詮釋其場面,很顯然這是一種較為合理和科學的分類研究法。
關於王世襄對漢畫像中奏樂舞蹈場面的研究述此即過,下面還是應該接續其通過漢代畫像對古代樂器之研究,因為在隨後解析的「弦之屬」「竹之屬」和「匏之屬」,王世襄還給今人帶來了許多聞所未聞的趣味的樂器知識。比如在「竹之屬」中,王世襄讓今天的人們見識了「篴」和「篪」這兩種罕聞之古代樂器,雖然在古字中「篴」與「笛」的音和義都相同,但是「篴」卻是一種豎吹的竹管樂器,而「笛」則是橫吹竹管樂器;至於「篪」這種樂器,王世襄在採信了《詩經·小雅·何人斯》及《樂書》等典籍中關於「篪」的形述之後,遂又進一步引錄了《律呂正義》中「出孔有翹者名篪,無翹者即笛,二器概相似」一句,使人們對於「篪」這種可能已經絕響的古代樂器,有了非常可感知與比較的認識。最有趣的是,王世襄在參閱大量典籍之後,告訴人們說古代所謂的「簫」並不是今天人們常見的那一根竹管之簫,而是由多根竹管排比構成的一種樂器。
關於從漢代畫像中研究奏樂場面,王世襄同樣將其分為獨奏與合奏兩個方面進行考釋。比如由一種樂器所進行的獨奏,王世襄就分列出擊磬、單人打楹鼓、單人打懸鼓和鼓船四種,其中關於人們不易理解的鼓船,王世襄則實事求是地說:「鼓船中的楹鼓,由兩人握雙槌敲擊。船上除搖櫓人外,還有兩人,背鼓而坐,並不在奏樂。……關於鼓船的文獻尚待查。」比如由兩種以上樂器合奏的場面,王世襄也分列出楹鼓簫合奏、鼓車的鼓簫合奏、琴篴合奏、琴鞞鼓合奏與琴笙簫鼗鼓鐘磬管等樂器合奏這五種形式。其中關於鼓車之說,他同樣只列舉肥縣孝堂山畫像之所見,至於《後漢書·循吏傳》中有「建武十三年異國有獻名馬者,詔以馬駕鼓車」一句,他則審慎地表明:「一時尚未查到更詳細的記載,不知漢光武帝所詔駕的鼓車,是否即孝堂山畫像中所描繪的那一種。」
王世襄最善於從典籍中考釋民族音樂,因此對其在考釋中國古代樂書方面的貢獻進行梳理,捷逕自然是要由淺入深,但所謂的深淺非指內容而單純指數量,即便其研究成果在完成時間上有先後,但筆者以為這並不妨礙對王世襄在這方面所取得突出成就的彰顯。
首先要解析的是王世襄對中國第一部音樂百科全書——宋陳暘《樂書》的解讀。關於《樂書》的作者陳暘(字晉之),王世襄之所以認為他是「一位刻苦有恆的學者」,主要是因為「他用了幾十年的工夫,才將《樂書》寫成」。那麼,多達兩百卷的《樂書》到底是怎樣一部「劃時代的、對文化學術有重要貢獻的」偉大著作呢?在這部卷帙浩繁的《樂書》中,作者陳暘根據內容將其分為「訓義」和「樂圖論」兩大部分,其中訓義部分佔據第一卷至第九十五卷,全部為文字,主要是對《禮記》《周禮》《儀禮》《詩經》《尚書》《春秋》《周易》《孝經》《論語》《孟子》這十種經書中關於音樂的章節逐條逐句進行解釋;佔據第九十六卷至第二百卷的樂圖論,主要包括樂律理論、樂器(包括樂隊)、聲樂和舞蹈雜技及典禮音樂(包括樂隊)等方面,可謂是內容豐富、圖文並茂。對於這樣一部音樂百科全書,王世襄主要從五個方面總結其重要性,即「內容豐富,體例分明」「注意歷史考證」「所收材料經過一定的調查研究」「不摒棄民間及外來音樂」和「文字之外附有插圖」。其中,關於佔據全書四分之一篇幅的「民間及外來音樂」,王世襄認為正是因為陳暘敢於衝破道學傳統之束縛,沒有遵循或迎合舊時道學先生們只看重廟堂雅樂之陳例,才使這部《樂書》成為最具研究價值的偉大著作。
當然,王世襄解讀《樂書》並沒有一味地停留在頌揚上,而是直言不諱地指出其存在的缺點和不足。比如,王世襄認為《樂書》的最大缺憾,就是作者陳暘沒有將音樂的最主要成分——曲調記錄下來。至於書中所體現出的極為濃厚的復古思想,王世襄也沒有因為作者廣肆收羅了民間和外來音樂,便對他認為的民間與外來音樂可有可無之觀點採取偏袒的態度,而是重點指出這正是該書的另一大缺憾。對於作者陳暘在引用前人文獻時竟然隨意增減或刪改的不審慎之態度,治學嚴謹的王世襄也毫不客氣地對其進行了批評。至於作者陳暘在採用材料時雖然注意調查研究,但是又對一些材料採取不夠客觀的採信,認為「這裡顯然違反了調查研究的精神」。
寫到這裡,實在不能不對王世襄與古琴之深緣進行一番探究了,這不僅因為在前文中曾多次提及他與古琴、他與古琴人的關聯,就連筆者在解析他研究漢代畫像中古代樂器時,也故意將「弦之屬」中的古琴給「忽略」掉了,這主要是因為關於王世襄與古琴著實有著太多的話要說。那麼,古琴是何種樂器,它具有怎樣的與眾不同的特點,王世襄與古琴及琴人有何淵源,對古琴曲譜又有何研究呢?
作為中國歷史最悠久的一種彈撥樂器,古琴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周代就已創製而成,古謂之為「琴」或「瑤琴」,而今還有「七絃琴」之稱。而王世襄在漢畫像中又發現有五絃琴、六絃琴和七絃琴之別,並說:「不知這是出於雕刻家的隨意增減,還是當時果有不同弦的琴。」其實,我們完全相信王世襄早已知曉古琴有下述之舊事,只是他審慎地提出這一疑問而已。確實,最初的古琴只有五根弦,後來周文王為了悼念他死去的兒子伯邑考,便增加一根弦為六絃琴,到了武王伐紂時為了鼓舞士氣,又增添了一根弦,故此古琴又有「文武七絃琴」之稱。
位列傳統文人「琴、棋、書、畫」四藝之首的古琴,無論是五弦、六弦還是七弦,其本身充滿了神秘的象徵色彩。比如,古琴身長三尺六寸五分,代表著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琴身寬有六寸,則象徵著六合;琴面上安有標示音位的十三個徽,表示一年十二個月與四年一次的閏月;弧形琴面與平形琴底,則分別代表著天與地,當然還有「天圓地方」之說;就連古琴最初的五根弦,也是按照宮、商、角、徵、羽這五聲設置,同時也代表著金、木、水、火、土這五種元素;乃至後來發展成為七絃琴時,也是上述五聲演變為宮、商、角、變徵、徵、羽、變宮這七聲之故。除了古琴本身的神秘色彩之外,傳統文人們還根據其特有的音質和品格,賦予其「奇、古、透、潤、靜、圓、均、清、芳」這衡量琴音的「九德」標準,以及包含有「清、微、淡、遠」這傳統文人所追求的審美意境。
至於古代所傳之琴譜,也因其以漢字簡筆記寫音位之特點,而致使同一樂曲在各派流傳中,出現了節奏無定、解釋不一的現象。因此,演奏者要想精確地理解樂譜,就必然要具備較高的文獻修養,否則被專業術語稱之為「打譜」的讀譜演奏,非造詣精深的琴家所不能為也。關於古琴打譜之難,王世襄曾在《試記管平湖先生打譜》一文中,記述了管平湖先生對此所作的一個比喻:
琴曲好比一個大盤子,中有許多大小不同的坑,每個坑內都放著和它大小相適合的珠子。打譜者開始摸不著頭腦,珠子都滑出坑外。打譜者須一次又一次晃動盤子,使每顆珠子都回到它該在的坑內。珠子都歸了位,打譜也就完成了。盤子須不斷地搖晃,要晃到珠子都歸位為止。打譜也須不斷地改正,改到對全曲的音律滿意為止。琴譜也不是絕對不能改,原作者也有把珠子放錯了位的時候。何況琴譜刊版時的徽位寫和刻也都難免會出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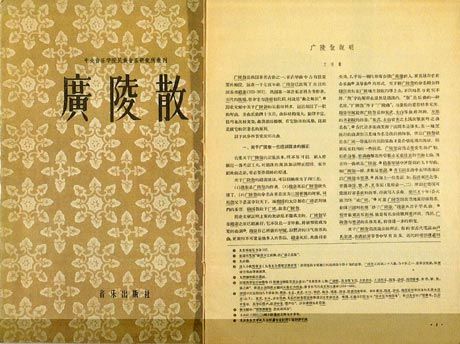
王世襄參與編寫的《廣陵散》
因此,王世襄在該文中將古琴大師管平湖先生所彈古琴曲分為三類時,就曾將其費時兩年半之久所打的《廣陵散》琴譜特別地提出來。那麼,古琴曲《廣陵散》是怎樣一首名曲呢?
關於古琴名曲《廣陵散》,實在有太多的謎題有待人們破譯,否則不會有前人汗牛充棟般的古籍文獻記載,也不會有王世襄《古琴名曲〈廣陵散〉》及《古琴名曲〈廣陵散〉說明》兩篇專文對其進行全方位的精深解析。在此,我們不妨先對《廣陵散》之命名與該曲故事作一說明。關於《廣陵散》之命名,有人將其附會為三國曹魏時司馬懿父子圖謀天下而在廣陵殘害魏國大臣,致使魏國散敗於廣陵之說。其實,這種附會不僅與史實不符,就連「散」字的解釋也出現了不諳樂曲術語之淺顯錯誤,因為曲名的「散」並非散敗之意,而是一種樂曲的名稱,即「廣陵散」相當於「廣陵曲」。據古籍記載,《廣陵散》是指在廣陵一帶流行的民間樂曲,這與左思在《齊都賦》中「《東武》《太山》皆齊之土風絃歌謳吟之曲名也」的註釋是異曲同工的。另外,從《廣陵散》多達四十五段的標題中還可以窺知,該曲描述的是戰國時期聶政復仇行刺的故事,並非前面附會三國曹魏散敗於廣陵之說,即便關於聶政行刺的動因與對象也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說法,但是這並不妨礙《廣陵散》名曲之正確命名。
那麼,《廣陵散》到底描述了怎樣一則歷史舊事呢?對此,王世襄在《古琴曲〈廣陵散〉說明》一文中記述了這樣兩種說法:
一、聶政為嚴仲子報仇刺韓相——韓國大臣嚴仲子與韓國宰相俠累有仇,為了要找人替他行刺,就結交聶政,卑躬折節地用財物去收買他。聶政竟不惜犧牲自己刺殺了韓相。韓國因不知刺客是誰,暴屍懸賞。聶政的姊姊不肯使弟弟聲名埋沒,前來認屍,並自殺在聶政的身旁。
二、聶政為父報仇刺韓王——聶政的父親為韓王煉劍,誤了期限,慘遭韓王殺害。聶政為報父仇,歷盡艱苦,入山學琴,十年工夫,學成絕技。韓王聽說國內出現了卓越的琴家,召他入宮演奏,但不知他就是要為父報仇的聶政。正在聽琴之際,聶政從琴中抽出刀來,刺殺了韓王。聶政怕連累他的母親,自毀容貌而死。韓國不知是誰刺死了國王,千金懸賞,求刺客姓名。聶政的母親為使兒子揚名前去認屍,並死在聶政的身旁。
對於這兩則故事,王世襄參閱了《戰國策》《史記》和《琴操》等典籍,以及樓鑰、張崇、耶律楚材等琴家所藏《廣陵散》琴譜與漢武梁祠石室畫像,並從情理上分析推理後認可了第二種說法。筆者細緻參閱有關史料,並對照王世襄所辨析之來龍去脈,也認為王世襄的辨析史據翔實、推測合理,故此不再贅述。
雖然《廣陵散》的命名與內容之謎得以澄清,但是這首古琴名曲的著作權卻出現了舛誤,而舛誤的緣由是因為早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出現了一位傑出的演奏家——嵇康。人們之所以誤認為嵇康為《廣陵散》的作者,並認定該曲在嵇康死後便已失傳,主要是根據《世說新語·雅量》中有「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的記載,這實在是一種誤會。對此,王世襄在《古琴曲〈廣陵散〉說明》中指出:
《廣陵散》早在嵇康之前已經流行;它不僅是一首琴曲,還被吸收成為笙的曲調。嵇康自己所作的《琴賦》,以讚許的口氣推薦此曲,更說明不可能是他本人的作品。嵇康死後,此曲並未失傳,幾乎每個朝代都有會彈《廣陵散》的人,而且發展成為合樂曲。
對於王世襄指出《廣陵散》早在嵇康之前就已流行且代有會操此曲之人的論點,筆者完全認同。不過,如果認為嵇康以讚許口氣推薦此曲就表明他並非此曲作者之論,似乎有些勉強了,因為自古以來推崇自己作品者不乏其人,比如王國維(筆者曾在拙作《王國維傳》中多次提及王國維對自己在詞學上所取得輝煌成就表示自賞)。
其實,如果人們獲知如今多達四十五段的《廣陵散》曲譜,是由最初的二十三段逐漸豐富發展而成的這一事實的話,也許不會對於該曲作者到底是誰窮根究底了,因為由此可知這是歷時數代由多位琴家接力創作完成的一首名曲。不過,從有關典籍中可知《廣陵散》曾經歷了二十三段、三十六段、四十一段、四十四段和四十五段這幾個發展歷程,但是現今發現七種琴書中所收《廣陵散》之譜本,實際上只有三種不同的譜本,即明朱權的《神奇秘譜》與明汪芝輯錄在《西麓堂琴統》中的兩譜(在此權且稱之為《西麓堂甲譜》和《西麓堂乙譜》),而據王世襄從三譜的標題內容、指法技巧、記譜方式及管平湖先生打譜之經驗來推論,古琴名曲《廣陵散》當以《神奇秘譜》本為最早,時間當在北宋或者更早些時候。
那麼,下面列舉《神奇秘譜》中《廣陵散》四十五段標題名稱也許不是多餘的廢話,因為今人接觸琴譜的機會實在寥寥,而對於結構龐大、旋律豐富、技巧複雜、曲調激昂的《廣陵散》名曲更是難得一聞。確實,多達四十五段的《廣陵散》名曲一共可以分為開指、小序、大序、正聲、亂聲和後序六個部分,具體則分為開指、止息一、止息二、止息三、井裡第一、申誠第二、順物第三、因時第四、干時第五、取韓第一、呼幽第二、亡身第三、作氣第四、含志第五、沉思第六、返魂第七、徇物第八、衝冠第九、長虹第十、寒風第十一、發怒第十二、烈婦第十三、收義第十四、揚名第十五、含光第十六、沉名第十七、投劍第十八、峻跡第一、守質第二、歸政第三、誓畢第四、終思第五、同志第六、用事第七、辭鄉第八、氣沖第九、微行第十、會止息第一、意絕第二、悲志第三、歎息第四、長吁第五、傷感第六、恨憤第七、亡計第八。那麼,《廣陵散》琴曲到底是怎樣一種曲調呢?既然無緣親聞此曲,不妨列舉三段琴家對《廣陵散》曲調內容較為細緻生動的描繪:
其怨恨淒感,即如幽冥鬼神之聲,邕邕容容,言語清泠。及其怫郁慨慷,又亦隱隱轟轟,風雨亭亭,紛披燦爛,戈矛縱橫。粗略言之,不能盡其美也。
——北宋《琴書·止息序》
暱暱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戰場!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喧啾百鳥鳴,忽見孤鳳凰,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
——北宋樓鑰
古譜成巨軸,無慮聲千百;
大意分五節,四十有四拍。
品弦終欲調,六弦一時劃;
初訝似破竹,不止如裂帛。
《忘身》志慷慨,《別姊》情慘戚;
《衝冠》氣何壯?《投劍》聲如擲。
《呼幽》達穹蒼,《長虹》如玉立;
將彈《發怒》篇,《寒風》自瑟瑟。
瓊珠落玉器,雹墜漁人笠;
別鶴唳蒼松,哀猿啼怪柏。
數聲如怨訴,寒泉古澗澀;
幾折變軒昂,奔流禹門急。
大弦忽一「捻」,應弦如破的;
雲煙速變滅,風雷恣呼吸。
數作「撥剌」聲,指邊轟霹靂;
一鼓息萬動,再弄鬼神泣。
——元耶律楚材
從以上三段文字中,我們可以想見古琴名曲《廣陵散》在表達幽怨時是那樣的淒婉清脆,在表達慷慨激昂時又有雷霆風雨戈矛殺伐之勢,而在泛音旋律中時而輕清自然,時而變幻莫測,有一種漫無拘束令人瞠目不辨的感覺。這樣一首神鬼莫測、勾魂攝魄之古曲,雖然歷代都有會演奏者,但是今人得以完整享受原曲之風格氣勢者,唯有管平湖先生打譜而成之《廣陵散》大曲。行文鋪墊至此,應該對管平湖先生與古琴之情緣特別記述一番了,否則將不足以解析王世襄為何與古琴有著深深情韻了。
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3月4日,管平湖出生在一個藝術世家,原名管平,字吉庵,號仲康,又號平湖,自稱門外漢,祖籍江蘇蘇州,父親管念慈(字劬安)是清宮廷如意館畫院院長,精繪畫,擅操琴。因此,管平湖自幼跟隨父親學習繪畫和彈琴,十三歲喪父後遂廣求名師,畫學師從王世襄的舅父金城金北樓先生,人物、花卉無所不通,尤其擅長工筆,雖然「他畫人物不能與當時年長於他的徐燕孫先生及年幼於他的陳少梅(雲彰)先生相抗衡」,但是他「研製色料,如石青、石綠等卻十分擅長而被人稱道」,繪畫的筆法秀麗新穎而不為成法所拘。在琴學方面,管平湖在父親去世後幸得其父同門師弟葉詩夢的多方照顧,並跟隨葉詩夢與張相韜繼續學習古琴,後來又拜在「九嶷派」創始人著名琴家楊宗稷(字時百)先生門下,僅僅兩年時間就基本上掌握了楊氏那種古拙嚴謹的演奏風格和指法技法,至於「九嶷派」的代表曲目如《漁歌》《瀟湘水雲》和《水仙操》等,也都能演奏得純熟流暢。
不過,今天談及管平湖先生極為高妙精深的演奏技藝和琴學造詣,有兩則關於他青年時外出拜師學琴的傳奇故事,不能不在此告知讀者。
一次,管平湖返回祖籍蘇州時,得知「武夷派」古琴名家悟澄和尚雲遊至此,並居住在蘇州郊外風景如畫的天平山上。於是,管平湖不顧旅途勞頓,立即前往拜師學藝,當他沿著崎嶇山路艱難行進時,一位年長樵夫勸阻說:「別往前走了,山裡經常有歹徒出來搶劫。」求師學藝心切的管平湖,笑別年長樵夫後繼續往山上攀行,忽然他聽到從不遠處樹林裡傳來一陣隱隱約約的琴聲,這不由使他激奮地加快了腳步。
果然,在密林深處管平湖發現了一抹紅牆,原來琴聲正是從紅牆內的一座寺廟裡傳來的。快步來到廟宇門前,管平湖沒有立即抬手敲門驚擾彈琴者,而是從兩扇緊閉著的破舊門扉中向寺廟裡尋聲觀望,只見一位長髯飄灑的老和尚端坐在佛殿前一株蒼松下,面對一張色澤蒼老的古琴正神情貫注地彈奏著,從曲調中管平湖聽出是古琴名曲《龍翔操》。
一曲奏完,管平湖急切地叩響門環,等那老和尚起身將門剛剛打開一條縫隙,他便搶步上前向老和尚誠懇地說明來意。老和尚上下打量了一番管平湖,引領他進入寺廟落座後又重新彈奏了一遍《龍翔操》,這一次管平湖看得清楚聽得真切,他完全被從老和尚那靈活穩健指法間流淌出的瀟灑動人之旋律驚呆了。待琴聲漸漸消散後,管平湖與那老和尚彼此作了介紹,原來這位老和尚正是「武夷派」名家悟澄老人。於是,管平湖當即跪求拜師,悟澄老人並沒有推辭,便將「武夷派」琴風指法悉授予他,從而使管平湖糾正了以往較為拘謹的指法缺點,古琴演奏技藝大為長進。
基本掌握「武夷派」精髓之後,管平湖告別悟澄老人從蘇州北上,這一次他慕名前往山東濟南拜訪「川派」古琴名家秦鶴鳴道長。有幸的是,管平湖果真在濟南尋訪到了秦鶴鳴道長,並向他學習了「川派」名曲張孔山創作的七十二滾拂《流水》,從此《流水》便成為管平湖具有代表性的演奏曲目,使其在中國古琴界聲名大震。另外,這首曾經因為春秋時期著名琴家俞伯牙的彈奏而與鍾子期結為知音的名曲,不僅在中國古琴史上承載了這一段流傳千古的傳奇佳話,還由於管平湖先生的演奏被美國於1977年8月發射的「航行者號」飛船送上了太空,從而帶著世人探尋地球以外天體生命的使命,到茫茫宇宙中尋求新的「知音」去了。
汲取了「九嶷派」「武夷派」和「川派」這三派古琴藝術精髓的管平湖,還善於從民間音樂中汲取有益養分,從而融會貫通並不斷創新發展,最終形成了在中國琴壇上具有重要影響的獨立一派——「管派」。見識或聆聽過「管派」古琴藝術演奏者,不難發現其指法穩重剛健、煞有神韻,演奏風格蒼勁古樸、剛柔相濟,音樂表現情感細膩、形象鮮明。在這一流派中,得到管平湖先生真傳者,有沈幼、袁荃猷、鄭珉中、王迪、許健等。
關於管平湖先生所演奏之琴曲,王世襄曾將其大致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已彈奏多年無須修改定型者,如《良宵引》《平沙落雁》《高山》《流水》《水仙操》和《墨子悲絲》等;第二類是不廣為人知彈者寥寥且有時還需修改者,如《欸乃》《洞天春曉》《長清》《短清》《梧葉舞秋風》《龍翔操》《烏夜啼》《大胡笳》《小胡笳》《秋鴻》和《羽化登仙》等;第三類只有《廣陵散》一曲。對於管平湖先生當年為《廣陵散》打譜一事,王世襄曾這樣記述說:
為打此譜,管先生必須從研究指法入手,至少用了半年多時間,等於一次重新學習。為了瞭解古曲所用指法,他查閱了若干種早期琴書,在明清琴譜中是找不到的。他先探索指法動作,再研究如何運用到實際彈奏中。在這段時間內只聽到他在琴弦上練指法的聲音,右手拇、食、中三指已經紅腫,左手拇指指甲也已磨出深溝。他在弄清指法並掌握了如何運用之後才開始打譜,打的是《神奇秘譜》本《廣陵散》,是現存最早的《廣陵散》譜。兩年之後才完全脫譜,可以不假思索,一氣呵成,彈完近三十分鐘(有人指出應為一小時三十分鐘)的大曲。風格氣勢,完全符合元人耶律楚材所作描寫《廣陵散》的長詩。不用說,在打譜的過程中說不清曾經有過多少次的修改。
當然,經管平湖先生打譜發掘而成古琴名曲的,不僅僅是這一首已經成為絕響的《廣陵散》,還有《幽蘭》《大胡笳》《小胡笳》《獲麟操》《烏夜啼》《長清》《短清》《離騷》和《白雪》等琴曲,也是經過他打譜整理後才重放異彩的。除此之外,管平湖先生,為了弘揚古琴藝術還先後參加、組織或創辦了「九嶷琴社」「風聲琴社」和「北平琴學社」(1954 年改稱為「北京古琴研究會」),並曾擔任過北京漢學專修館、國樂傳習所與北平國立藝術專科學校的古琴教師,有《古琴指法考》等著作傳世。1953年,管平湖先生經王世襄牽線引薦到中央音樂學院民族音樂研究所,專門從事古琴音樂教學和發掘打譜研究工作後,終於使他的音樂天才或者直接說古琴藝術天才得到了最充分的彰顯。綜上所述,可以肯定地說,管平湖先生對中國古琴藝術做出了起潛振絕般的雄偉功績。
對古琴藝術具有如此精深造詣和偉大貢獻的管平湖先生,還精於制琴和修琴,比如現珍藏在北京故宮博物院中的唐「大聖遺音」與明「龍門風雨」兩琴,就是經過管平湖先生修整完好的。至於王世襄原藏亦名唐「大聖遺音」伏羲式琴,也是經管平湖先生多次修整而完好如初的。對此,王世襄曾有這樣一段文字記述此事:
(唐「大聖遺音」伏羲式琴)傳世既久,深以足孔四周,漆多剝落,木質亦瀕朽蝕為慮。足端雖纏織物並嵌塞木片,仍難固定。張弦稍緊,且有扳損琴背之虞。幸平湖先生有安裝銅足套之法,屢次實施,效果均佳。為此特請青銅器修復專家高英先生為制銅套並仿舊染色,老友金禹民先生鐫刻八分書題記:「世襄荃猷,鬻書典釵,易此枯桐」十二字。又蒙平湖先生調漆灰,穩臥足套於孔內,不僅天衣無縫,且琴音絲毫未損。先生笑曰:「又至少可放心彈五百年了!」
由此可見,管平湖先生在修復古琴方面堪稱是「國手」了。管平湖先生對古琴的愛護,可以說是不惜付出生命的代價,這從時人的一則見聞中可以窺見。據說,一天晚上管平湖先生攜帶那張名為「清英」的唐琴,應邀到廣播電台錄製古琴曲。節目錄製完成後,管平湖先生獨自乘坐三輪車由電台返回寓所,當三輪車行至長安街西三座門(現已拆除,原址在今北京市第二十八中學門前)時,一輛迎面飛馳而來的卡車刮蹭在了三輪車上,三輪車被卡車撞翻的同時,管平湖先生也被猛地甩了出去。當管平湖先生不顧膝蓋和肘部多處被挫傷好不容易才爬起來時,發現那張琴依然完好無損地被他緊緊抱在懷裡。事後,管平湖先生笑著對友人說:「在翻車的一剎那,我更加用力地抱緊了琴,雖然我被拋出車外翻了一個滾兒,但是琴卻始終沒有著地。」說完這一險遇後,管平湖先生竟然發出了一陣爽朗的笑聲,這不由使聽者不能不為他愛琴如命的精神所深深感動。
遺憾的是,像管平湖先生這樣一位「琴癡」式的古琴大家,生活竟然一度陷入窮困潦倒之境地。新中國成立前,家徒四壁、囊空如洗的管平湖先生,僅僅依靠白天教琴、間或修琴和夜晚作畫出售所得微薄收入養家餬口,生活狀況極為窘迫困厄。據說,有時為了售賣一幅扇面,管平湖先生不得不從北城步行到南城榮寶齋,甚至還做過故宮博物院的油漆工。民國三十六年(1947)春,國樂傳習所停辦後,管平湖先生因失去這一份薪水不得不搬遷到北新橋慧照寺胡同內一間不足十平方米的小耳房內居住。這是一間既矮又破且後山牆上百孔洞穿的老舊房子,一張用薄木板支架成的床鋪緊靠在牆角處,床上是褪色破舊的陳年被褥,一張臨窗而立的兩屜舊木桌,權作是管平湖先生這位古琴大師的琴案了,而琴案用作他途時高貴的古琴又只好懸掛在桌子右方那堵陋牆上。即便如此,隨遇而安的管平湖先生,不僅沒有被生活重壓消磨掉藝術才華和創作意志,反而每天堅持彈琴打譜,這種數十年如一日獻身藝術的高貴精神,豈是今天無利不往的某些所謂藝術家所能望其項背?!
特別難得而又重要的是,管平湖先生在苦難境況中還自享其豐富的生活情趣。對此,王世襄在《冬蟲篇》一文中曾記述了這樣兩件趣事:
(20世紀)30年代,管平湖先生過隆福寺,祥子出示西山大山青,其聲雄厚松圓,是真所謂「叫頇」者。惜已蒼老,肚上有傷斑,足亦殘缺,明知不出五六日將死去,先生猶欣然以五元易歸(當時洋白面每袋二元五角),笑謂左右曰:「哪怕活五天,聽一天花一塊也值!」此時先生以鬻畫給朝夕,實十分拮据。1955年與先生同就職中國音樂研究所,每夜聽彈《廣陵散》。余於灰峪捉得大草白,懷中方作響,先生連聲稱:「好!好!好!」順手拂幾上琴曰:「你聽,好蟈蟈跟唐琴一弦散音一個味兒。」時先生已多年不蓄蟲,而未能忘情,有如是者!
當然,管平湖先生供職中央音樂學院民族音樂研究所後,生活更是有一種無憂無慮的愜意舒爽。對此,王世襄也有這樣一段讓人羨歎且饒有情趣的記述:
音研所的兩位所長李元慶、楊蔭瀏都是音樂藝術家,對管先生也以藝術家相待,給他一間房,既是工作室,也是臥室。工作就是彈琴或與古琴有關的工作。他有時整天彈琴到深夜,有時喝幾杯二鍋頭,稍有醉意,修整花草後,倚枕高臥。不論幹什麼,都不會有人打擾,說不定他的高臥正在思考某一指法的運用,某兩句之間如何連接,才了無痕跡且符合整曲的氣勢。
正是在這種適於藝術家生存和創作的情境中,管平湖先生才能將古琴或悲壯或雄健或幽深或古雅這一恍若隔世天籟般的千古妙音,從心田間徐徐地流淌而出。而與管平湖先生相識數十年後又朝夕相處長達五年之久的王世襄,無疑不僅在古琴藝術還在更多方面得到其教誨和熏染,這不能不說是王世襄成長為一代博才多藝大家的一份外緣。即便王世襄自嘲「儘管我五音不全,全無欣賞音樂的能力,聽琴只能當一頭牛」,但是這並不妨礙人們對他在古琴典籍整理上的成就表示敬仰,比如現存中央音樂學院查阜西紀念室中由他主持編寫的《琴書解題》。

1957年古琴「國手」管平湖先生與眾弟子合影(前排中間管平湖、前排左二袁荃猷、後排中間王世襄)
所謂《琴書解題》,就是王世襄將《風宣玄品》(十卷)、《太古正音》(琴經十四卷、琴譜四卷)、《杏莊太音補遺》(三卷)、《藏春塢琴譜》(六卷)和《松弦館琴譜》(兩卷)這五部古琴典籍進行「解題」,這是王世襄加盟民族音樂研究所後主持的第一個學術研究課題。通過《琴書解題》一書,我們從王世襄編寫該書的體例及方法中,完全可以看出其在古琴研究上的獨到見解。比如,王世襄在編寫過程中分為四個部分,即凡例、琴書目錄、解題和著者索引,重點當然是解題部分,故此他又將解題分為「全書提要」「分節提要」和「注」三個方面,雖然「全書提要」只記述書名卷數及作者、版本、小傳和內容,但是單單在內容一節中王世襄並沒有只羅列一書所收曲調之總數,而是對全書的特點及要點加以總結,至於在「分節提要」中,王世襄更是「逐節作提要並附考證或註解」,這豈是不精通古琴藝術者所能為之事?再具體比如說,王世襄在解析《風宣玄品》時因為「原本缺目錄首葉」,他便「將各細則依內容加以歸納,推測補寫目錄第一葉」,試想,如果他不諳該琴書之深蘊,何以能補寫出該書目錄之首頁呢?即便是現今作者已經忽略不計的「注」,有心者也不難發現王世襄不知要查閱多少各種典籍,否則就連湮滅在史料長河中那些不為人知的作者小傳也無從知曉,何況還要吹沙淘金般地將有關演奏指法的舛誤指正出來,這都絕非一般琴家所能夠完成。
遺憾的是,王世襄主持《琴書解題》這一學術研究課題,後來「因人事干擾,不得已而中斷」。不過,除此之外我們還能從王世襄與夫人袁荃猷根據定府葉潛舊藏本、傅惜華藏本與楊蔭瀏藏本,對自己儷松居舊藏本《松弦館琴譜》進行彙集補缺,特別是手錄匯而成帙後所寫的長篇題記中,可以準確瞭解到王世襄對於古琴譜的研究確實是造詣精深。
明萬曆年間七絃琴權威沈太韶曾言:「琴不通千曲以上者,不可以語知音。」如此,古琴大師管平湖先生視王世襄為知音,焉是對「牛」彈琴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