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存在之謎
一
如同一切「文化熱」一樣,所謂「昆德拉熱」也是以誤解為前提的。人們把道具看成了主角,誤以為眼前正在上演的是一出政治劇,於是這位移居巴黎的捷克作家便被當作一個持不同政見的文學英雄受到了歡迎或者警惕。
現在,隨著昆德拉的文論集《小說的藝術》中譯本的出版,我祝願他能重獲一位智者應得的寧靜。
昆德拉最欣賞的現代作家是卡夫卡。當評論家們紛紛把卡夫卡小說解釋為一種批評資本主義異化的政治寓言的時候,昆德拉卻讚揚它們是「小說的徹底自主性的出色樣板」,指出其意義恰恰在於它們的「不介入」,即在所有政治綱領和意識形態面前保持完全的自主。
「不介入」並非袖手旁觀,「自主」並非中立。卡夫卡也好,昆德拉也好,他們的作品即使在政治的層面上也是富於批判意義的。但是,他們始終站得比政治更高,能夠超越政治的層面而達於哲學的層面。如同昆德拉自己所說,在他的小說中,歷史本身是被當作存在境況而給予理解和分析的。正因為如此,他們的政治批判也就具有了超出政治的人生思考的意義。
高度政治化的環境對於人的思考力具有一種威懾作用,一個人哪怕他是笛卡兒,在身歷其境時恐怕也難以怡然從事「形而上學的沉思」。面對血與火的事實,那種對於宇宙和生命意義的「終極關切」未免顯得奢侈。然而,我相信,一個人如果真是一位現代的笛卡兒,那麼,無論他寫小說還是研究哲學,他都終能擺脫政治的威懾作用,使得異乎尋常的政治閱歷不是阻斷而是深化他的人生思考。
魯迅曾經談到一種情況:呼喚革命的作家在革命到來時反而沉寂了。我們可以補充一種類似的情況:呼喚自由的作家在自由到來時也可能會沉寂。僅僅在政治層面上思考和寫作的作家,其作品的動機和效果均繫於那個高度政治化的環境,一旦政治淡化(自由正意味著政治淡化),他們的寫作生命就結束了。他們的優勢在於敢寫不允許寫的東西,既然什麼都允許寫,他們還有什麼可寫的呢?
比較起來,立足於人生層面的作家有更耐久的寫作生命,因為政治淡化原本就是他們的一個心靈事實。他們的使命不是捍衛或推翻某種教義,而是探究存在之謎。教義會過時,而存在之謎的謎底是不可能有朝一日被窮盡的。
所以,在移居巴黎之後,昆德拉的作品仍然源源不斷地問世,我對此絲毫不感到奇怪。
二
在《小說的藝術》中,昆德拉稱小說家為「存在的勘探者」,而把小說的使命確定為「通過想像出的人物對存在進行深思」,「揭示存在的不為人知的方面」。
昆德拉所說的「存在」,直接引自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儘管這部巨著整個是在談論「存在」,卻始終不曾給「存在」下過一個定義。海德格爾承認:「『存在』這個概念是不可定義的。」我們只能約略推斷,它是一個關涉人和世界的本質的範疇。正因為如此,存在是一個永恆的謎。按照尼采的說法,哲學家和詩人都是「猜謎者」,致力於探究存在之謎。那麼,小說的特點何在?在昆德拉看來,小說的使命與哲學、詩並無二致,只是小說擁有更豐富的手段,它具有「非凡的合併能力」,能把哲學和詩包容在自身中,而哲學和詩卻無能包容小說。
在勘探存在方面,哲學和詩的確各有自己的尷尬。哲學的手段是概念和邏輯,但邏輯的繩索不能套住活的存在。詩的手段是感覺和意象,但意象的碎片難以映顯完整的存在。很久以來,哲學和詩試圖通過聯姻走出困境,結果好像並不理想,我們讀到了許多美文和玄詩,也就是說,許多化裝為哲學的詩和化裝為詩的哲學。我不認為小說是唯一的乃至最後的出路,然而,設計出一些基本情境或情境之組合,用它們來包容、聯結、貫通哲學的體悟和詩的感覺,也許是值得一試的途徑。
昆德拉把他小說裡的人物稱作「實驗性的自我」,其實質是對存在的某個方面的疑問。例如,在《不能承受的存在之輕》中,托馬斯大夫是對存在之輕的疑問,特麗莎是對靈與肉的疑問。事實上,它們都是作者自己的疑問,推而廣之,也是每一個自我對於存在所可能具有的一些根本性困惑,昆德拉為之設計了相應的人物和情境,而小說的展開便是對這些疑問的深入追究。
關於「存在之輕」的譯法和含義,批評界至今眾說紛紜。其實,只要考慮到昆德拉使用的「存在」一詞的海德格爾來源,許多無謂的爭論即可避免。「存在之輕」就是人生缺乏實質,人生的實質太輕飄,所以使人不能承受。在《小說的藝術》中,昆德拉自己有一個說明:「如果上帝已經走了,人不再是主人,誰是主人呢?地球沒有任何主人,在虛空中前進。這就是存在的不可承受之輕。」可見其含義與「上帝死了」的命題一脈相承,即指人生根本價值的失落。對托馬斯來說,人生實質的空無尤其表現在人生受偶然性支配上,使得一切真正的選擇成為不可能,而他所愛上的特麗莎便是絕對偶然性的化身。另一方面,特麗莎之受靈與肉問題的困擾,又是和托馬斯既愛她又同眾多女人發生性關係這一情形分不開的。兩個主人公各自代表對存在的一個基本困惑,同時又構成誘發對方困惑的一個基本情境。在這樣一種頗為巧妙的結構中,昆德拉把人物的性格和存在的思考同步推向了深入。
我終歸相信,探究存在之謎還是可以用多種方式的,不必是小說;用小說探究存在之謎還是可以有多種寫法的,不必如昆德拉。但是,我同時也相信昆德拉的話:「沒有發現過去始終未知的一部分存在的小說是不道德的。」不但小說,一切精神創作,唯有對人生基本境況做出了新的揭示,才稱得上偉大。
三
昆德拉之所以要重提小說的使命問題,是因為他看到了現代人的深刻的精神危機,這個危機可以用海德格爾的一句名言來概括,就是「存在的被遺忘」。
存在是如何被遺忘的?昆德拉說:「人處在一個真正的縮減的漩渦中,胡塞爾所講的『生活的世界』在漩渦中宿命般地黯淡,存在墮入遺忘。」
縮減彷彿是一種宿命。我們剛剛告別生活一切領域縮減為政治的時代,一個新的縮減漩渦又更加有力地罩住了我們。在這個漩渦中,愛情縮減為性,友誼縮減為交際和公共關係,讀書和思考縮減為看電視,大自然縮減為豪華賓館裡的室內風景,對土地的依戀縮減為旅遊業,真正的精神冒險縮減為假冒險的遊樂設施。要之,一切精神價值都縮減成了實用價值,永恆的懷念和追求縮減成了當下的官能享受。當我看到孩子們不再玩沙和泥土,而是玩電子遊戲機,不再知道白雪公主,而是津津樂道卡通片裡的機器人的時候,我心中明白一個真正可怕的過程正在地球上悄悄進行。我也懂得了昆德拉說這話的沉痛:「明天當自然從地球上消失的時候,誰會發現呢?……末日並不是世界末日的爆炸,也許沒有什麼比末日更為平靜的了。」我知道他絕非危言聳聽,因為和自然一起消失的還有我們的靈魂,我們的整個心靈生活。上帝之死不足以造成末日,真正的世界末日是在人不圖自救、不復尋求生命意義的那一天到來的。
可悲的是,包括小說在內的現代文化也捲入了這個縮減的漩渦,甚至為之推波助瀾。文化縮減成了大眾傳播媒介,人們不復孕育和創造,只求在公眾面前頻繁亮相。小說家不甘心於默默無聞地在存在的某個未知領域裡勘探,而是把眼睛盯著市場,揣摩和迎合大眾心理,用廣告手段提高知名度,熱衷於擠進影星、歌星、體育明星的行列,和他們一起成為電視和小報上的新聞人物。如同昆德拉所說,小說不再是作品,而成了一種動作,一個沒有未來的當下事件。他建議比自己的作品聰明的小說家改行,事實上他們已經改行了——他們如今是電視製片人、文化經紀人、大腕、款爺。
正是面對他稱之為「媚俗」的時代精神,昆德拉舉起了他的堂吉訶德之劍,要用小說來對抗世界性的平庸化潮流,喚回對被遺忘的存在的記憶。
四
然而,當昆德拉譴責媚俗時,他主要還不是指那種製造大眾文化消費品的通俗暢銷作家,而是指諸如阿波利內爾、蘭波、馬雅可夫斯基、未來派、前衛派這樣的響噹噹的現代派。這裡我不想去探討他對某個具體作家或流派的評價是否公正,只想對他抨擊「那些形式上追求現代主義的作品的媚俗精神」表示一種快意的共鳴。當然,藝術形式上的嚴肅的試驗是永遠值得讚賞的,但是,看到一些藝術家懷著唯恐自己不現代的焦慮和力爭最現代超現代的激情,不斷好新騖奇,渴望製造轟動效應,我不由得斷定,支配著他們的仍是大眾傳播媒介的那種譁眾取寵精神。
現代主義原是作為對現代文明的反叛崛起的,它的生命在於真誠,即對虛妄信仰的厭惡和對信仰失落的悲痛。不知何時,現代主義也成了一種時髦,做現代派不再意味著超越於時代之上,而是意味著站在時代前列,領受的不是冷落,而是喝彩。於是,現代世界的無信仰狀態不再使人感到悲涼,反倒被標榜為一種新的價值大放其光芒,而現代主義也就蛻變成了掩蓋現代文明之空虛的花哨飾物。
所以,有必要區分兩種現代主義:一種是向現代世界認同的時髦的現代主義,另一種是批判現代世界的「反現代的現代主義」。昆德拉強調後一種現代主義的反激情性質,指出現代最偉大的小說家都是反激情的,並且提出一個公式:小說=反激情的詩。一般而言,藝術作品中激情外露終歸是不成熟的表現,無論在藝術史上還是對於藝術家個人而言,浪漫主義均屬於一個較為幼稚的階段。尤其在現代,面對無信仰,一個人如何能懷有以信仰為前提的激情?其中包含著的矯情和媚俗是不言而喻的了。一個嚴肅的現代作家則敢於正視上帝死後重新勘探存在的艱難使命,他是現代主義的,因為他懷著價值失落的根本性困惑,他又是反現代的,因為他不肯在根本價值問題上隨波逐流。那麼,由於在價值問題上的認真態度,毋寧說「反現代的現代主義」蘊含著一種受挫的激情。這種激情不外露,默默推動著作家在一個沒有上帝的世界上繼續探索存在的真理。
倘若一個作家清醒地知道世上並無絕對真理,同時他又不能抵禦內心那種形而上的關切,他該如何向本不存在的絕對真理挺進呢?昆德拉用他的作品和文論告訴我們,小說的智慧是非獨斷的智慧,小說對存在的思考是疑問式的、假說式的。我們確實看到,昆德拉在他的小說中是一位調侃能手,他調侃一切神聖和非神聖的事物,調侃歷史、政治、理想、愛情、性、不朽,借此把一切價值置於問題的領域。然而,在這種貌似玩世不恭下面,卻蘊藏著一種根本性的嚴肅,便是對於人類存在境況的始終一貫的關注。他自己不無理由地把這種寫作風格稱作「輕浮的形式與嚴肅的內容的結合」。說到底,昆德拉是嚴肅的,一切偉大的現代作家是嚴肅的。倘無這種內在的嚴肅,輕浮也可流為媚俗。在當今文壇上,那種借調侃一切來取悅公眾的表演不是正在走紅嗎?

我們都是孤獨的行路人
從生存向存在的途中
獸和神大約都不會無聊。獸活命而已,只有純粹的生存。神充實自足,具備完滿的存在。獸、人、神三界,唯有夾在中間的人才會無聊,才可能有活得沒意思的感覺和歎息。
無聊的前提是閒。當人類必須為生存苦鬥的時候,想必也無聊不起來。我們在《詩經》或《荷馬史詩》裡幾乎找不到無聊這種奢侈的情緒。要能閒得無聊,首先必須倉廩實,衣食足,不愁吃穿。吃穿有餘,甚至可以惠及畜生,受人豢養的貓狗之類的寵物也會生出類似無聊的舉態,但它們已經無權稱作獸。
當然,物質的進步永無止境,倉廩再實,衣食再足,人類未必閒得下來。世上總有閒不住的闊人、忙人和勤人,另當別論。
一般來說,只要人類在求溫飽之餘還有精力,無聊的可能性就存在了。席勒用剩餘精力解釋美感的發生。其實,人類特有的一切好東西壞東西,其發生蓋賴於此,無聊也不例外。
有了剩餘精力,不釋放出來是很難受的。「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孔子就很明白這難受勁,所以他勸人不妨賭博下棋,也比閒著什麼事不做好。「難矣哉」,林語堂解為「真難為他們」「真虧他們做得出來」,頗傳神,比別的注家高明。閒著什麼事不做,是極難的,一般人無此功夫。所謂閒,是指沒有非做不可的事,遂可以自由支配時間,做自己感興趣的事。閒的可貴就在於此。興趣有雅俗寬窄之別,但大約人人都有自己感興趣的事。麻將撲克是一種興趣,琴棋詩畫是一種興趣,擁被夜讀是一種興趣,坐在桌前,點一支煙,沉思遐想,也是一種興趣。閒了未必無聊,閒著沒事幹才會無聊。有了自由支配的時間,卻找不到興趣所在,或者做不成感興趣的事,剩餘精力茫茫然無所寄托,這種滋味就叫無聊。
閒是福氣,無聊卻是痛苦。勤勤懇懇一輩子的公務員,除了公務別無興趣,一旦退休閒居,多有不久便棄世的,致命的因素正是無聊。治獄者很懂得無聊的厲害,所以對犯人最嚴重的懲罰不是苦役而是單獨監禁。苦役是精力的過度釋放,單獨監禁則是人為地堵塞釋放精力的一切途徑,除吃睡外不准做任何事。這種強制性的無聊,其痛苦遠在苦役之上。在自由狀態下,多半可以找到法子排遣無聊。排遣的方式因人而異,最能見出一個人的性情。愈淺薄的人,其無聊愈容易排遣,現成的法子有的是。「不有博弈者乎?」如今更好辦,不有電視機乎?面對電視機一坐幾個鐘點,天天坐到頭昏腦漲然後上床去,差不多是現代人最常見的消磨閒暇的方式——或者說,糟蹋閒暇的方式。
時間就是生命。奇怪的是,人人都愛惜生命,不願其速逝,卻害怕時間,唯恐其停滯。我們好歹要做點什麼事來打發時間,一旦無所事事,時間就彷彿在我們面前停住了。我們面對這脫去事件外衣的赤裸裸的時間,發現它原來空無所有,心中隱約對生命的實質也起了恐慌。無聊的可怕也許就在於此,所以要加以排遣。
但是,人生中有些時候,我們會感覺到一種無可排遣的無聊。我們心不在焉,百事無心,覺得做什麼都沒意思。並不是疲倦了,因為我們有精力,只是茫無出路。並不是看透了,因為我們有慾望,只是空無對象。這種心境無端而來,無端而去,曇花一現,卻是一種直接暴露人生根底的深邃的無聊。
人到世上,無非活一場罷了,本無目的可言。因此,在有了超出維持生存以上的精力以後,這剩餘精力投放的對象卻付諸闕如。人必須自己設立超出生存以上的目的。活不成問題了,就要活得有意思,為生命加一個意義。然而,為什麼活著?這是一個危險的問題。若問為什麼吃喝勞作,我們很明白,是為了活。活著又為了什麼呢?這個問題追究下去,沒有誰不糊塗的。
對此大致有兩類可能的答案。一類答案可以歸結為:活著為了吃喝勞作——為了一己的、全家的或者人類的吃喝勞作,為了吃喝得更奢侈,勞作得更有效,如此等等。這類答案雖然是多數人實際所奉行的,作為答案卻不能令人滿意,因為它等於說活著為了活著,不成其為答案。
如果一切為了活著,活著就是一切,豈不和動物沒有了區別?一旦死去,豈不一切都落了空?這是生存本身不能作為意義源泉的兩個重要理由。一事物的意義須從高於它的事物那裡求得,生命也是如此。另一類答案就試圖為生命指出一個高於生命的意義源泉,它應能克服人的生命的動物性和暫時性,因而必定是一種神性的不朽的東西。不管哲學家們如何稱呼這個東西,無非是神的別名罷了。其實,神祇是一個記號,記錄了我們追問終極根據而不可得的迷惘。例如,從巴門尼德到雅斯貝斯,都以「存在」為生命意義之源泉,可是他們除了示意「存在」的某種不可言傳的超越性和完美性之外,還能告訴我們什麼呢?
我們往往樂於相信,生命是有高出生命本身的意義的,例如真善美之類的精神價值。然而,真善美又有什麼意義?可以如此無窮追問下去,但我們無法找到一個終極根據,因為神並不存在。擺脫這個困境的唯一辦法是把一切精神價值的落腳點引回到地面上來,看作人類生存的工具。各派無神論哲學家歸根到底都是這樣做的。但是,這樣一來,我們又陷入了我們試圖逃避的同義反覆:活著為了活著。
也許關鍵在於,這裡作為目的的活,與動物並不相同。人要求有意義地活,意義是人類生存的必要條件。因此,上述命題應當這樣展開:活著為了尋求意義,而尋求意義又是為了覺得自己是在有意義地活著。即使我們所尋求的一切高於生存的目標,到頭來是虛幻的,尋求本身就使我們感到生存是有意義的,從而能夠充滿信心地活下去。凡真正的藝術家都視創作為生命,不創作就活不下去。超出這一點去問海明威為何要寫作,畢加索為何要畫畫,他們肯定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人類迄今所創造的燦爛文化如同美麗的雲景,把人類生存的天空烘托得極其壯觀。然而,若要追究雲景背後有什麼,便只能墮入無底的虛空了。人,永遠走在從生存向存在的途中。他已經辭別獸界,卻無望進入神界。他不甘於純粹的生存,卻達不到完美的存在。他有了超出生存的精力,卻沒有超出生存的目標。他尋求,卻不知道尋求什麼。人是注定要無聊的。
可是,如果人真能夠成為神,就不無聊了嗎?我想像不出,上帝在完成他的創世工作之後,是如何消磨他的星期天的。《聖經》對此閉口不談,這倒不奇怪,因為上帝是完美無缺的,既不能像肉慾猶存的人類那樣用美食酣睡款待自己,又不能像壯心不已的人類那樣不斷進行新的精神探險,他實在沒事可幹了。他的絕對的完美便是他的絕對的空虛。人類的無聊尚可藥治,上帝的無聊寧有息日?不,我不願意成為神。雖然人生有許多缺憾,生而為人仍然是世上最幸運的事。人生最大的缺憾便是終有一死。生命太短暫了,太珍貴了,無論用它來做什麼都有點可惜。總想做最有意義的事,足以使人不虛此生、死而無恨的事,卻沒有一件事堪當此重責。但是,人活著總得做點什麼。於是,我們便做著種種微不足道的事。人生終究還是免不了無聊。

我們都是孤獨的行路人
存在就是被感知嗎
「存在就是被感知」——這是貝克萊提出的一個很有名的命題。為了弄清這個命題的意思,現在且假定這位哲學家還活著,讓他來和我們進行一場對話。
貝克萊:此刻你面前有一隻蘋果,你看得見它,摸得著它。這只蘋果存在嗎?
答:存在。
貝克萊:你憑什麼說它存在呢?
答:因為我明明看見了它,摸到了它。
貝克萊:這就是說,它被你感知到了。好,現在你閉上眼睛,把手插進衣服口袋裡,看不見也摸不到這只蘋果了。我再問你,它現在存在嗎?
答:存在。
貝克萊:現在你並沒有看見它,摸到它,憑什麼還說它存在呢?
答:因為我剛才看見過它,摸到過它,我相信只要我睜開眼睛,伸出手,現在我仍然能看見它,摸到它。
貝克萊:這就是說,你之所以相信它仍然存在,是因為它剛才曾經被你感知到,這使你相信,只要你願意,現在它仍然可以被你感知到。現在假定在離你很遠的一個地方有一隻蘋果,你永遠不會看見它,摸到它,它存在嗎?
答:存在,因為那個地方的人能看見它,摸到它。
貝克萊:如果那是一片沒有人煙的原始森林,那只蘋果是一隻野生蘋果,在它腐爛之前不會有任何人見到它呢?
答:但是,我們可以想像如果那裡有人,就一定能見到它。
貝克萊:好了,現在我們可以總結一下了。我們說某個東西存在,無非是說它被我們感知到。即使當我們設想存在著某個我們從未感知到的東西時,我們事實上也是在設想它以某種方式被我們感知到。我們無法把存在與被感知分離開來,離開被感知去設想存在。由此可見,存在和被感知是一回事,存在就是被感知。
談話進行到這裡,缺乏經驗的讀者也許被繞糊塗了,而有經驗的讀者很可能會提出一個反駁:儘管我們無法離開被感知設想存在,但這不能證明存在與被感知是一回事。一個東西首先必須存在著,然後才能被感知。例如,一隻蘋果的存在是因,它的被感知是果,兩者不可混為一談。不過,針對這個反駁,貝克萊會追問你所說的「存在」究竟是什麼意思,當你談論這只蘋果的「存在」時,你的心靈中豈不出現了這只蘋果的形狀、顏色、香味等,所謂它的「存在」無非是指它的這些可被感知的性質在你的心靈中的呈現,因而也就是指它的被感知?那麼,它的「存在」和它的被感知豈不是一回事,哪裡有原因和結果的分別?
貝克萊的是與非
現在我們觸及「存在就是被感知」這個命題的真正含義了。貝克萊的思路是這樣的:對我來說,一隻蘋果的存在無非是指我看到了它的顏色,聞到了它的香味,摸到了它的形狀、冷暖、軟硬,嘗到了它的甜味,等等,去掉這些性質就不復有蘋果的存在,而顏色、形狀、香味、甜味、軟硬等又無非都是我的感覺,離開我的感覺就不復有這些性質。所以,這只蘋果的存在與它被我感知是一回事,它僅僅是存在於我的心靈中的一些感覺。當然,我可以設想一隻我未曾看到的蘋果的存在,但我也只能把它設想為我的這些感覺。在這些感覺之外斷定還存在著某種不可被感知的蘋果的「實體」,這是徒勞的,也是沒有意義的。這個道理適用於我所面對的一切對象,包括我所看見的其他人。所以,譬如說,我的父親和母親也只是我的心靈中的一些感覺而已,在我的心靈之外並無他們獨立的存在……
說到這裡,你一定會喊起來:太荒謬了,難道你是你的感覺生出來的嗎?是的,連貝克萊自己也覺得太荒謬了。為了避免如此荒謬的結論,他不得不假定,除了「我」的心靈之外,還存在著別的心靈,甚至還存在著上帝的心靈,一切存在物因為被無所不在的上帝的心靈所感知而保證了它們的存在。這種假定顯然是非常勉強的,我們可以不去理會。值得思考的是貝克萊的前提:我們只能通過感覺感知事物的存在,因此,對我們來說,事物的存在是與它們被我們感知分不開的。從這個前提能否推出「存在就是被感知」的結論呢?這裡實際上包含兩個問題:第一,事物的存在是否等同於它的可被感知的性質的存在?在這些性質背後有沒有一個不可被感知的「實體」,用更加哲學化的語言說,在現象背後有沒有一個「自在之物」?第二,事物的可被感知的性質是否等同於「我」(主體)的感覺?在「我」的感覺之外有沒有使「我」產生這些感覺的外界現象,用更加哲學化的語言說,在「主體」之外有沒有「客體」,在「意識」之外有沒有客觀存在的「對像」?這是兩個不同的問題。貝克萊主張第一個等同,否認現象背後有「自在之物」,這是今天大多數哲學家都可贊成的;但他進而主張第二個等同,否認現象在「我」之外的存在,這是今天大多數哲學家都不能贊成的。

我們都是孤獨的行路人
莊周夢蝶的故事
睡著了會做夢,這是一種很平常的現象。正常人都能分清夢和真實,不會把它們混淆起來。如果有誰夢見自己變成了一隻蝴蝶,醒來後繼續把自己當作蝴蝶,張開雙臂整天在花叢草間做飛舞狀,大家一定會認為他瘋了。然而,兩千多年前有一個名叫莊周的中國哲學家,有一回他夢見自己變成了一隻蝴蝶,醒來後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問題:
「究竟是剛才莊周夢見自己變成了蝴蝶呢,還是現在蝴蝶夢見自己變成了莊周?」
好像沒有人因為莊周提出這個問題而把他看成一個瘋子,相反,大家都承認他是一個大哲學家。哲學家和瘋子大約都不同於正常人,但他們是以不同的特點區別於正常人的。瘋子不能弄懂某些最基本的常識,例如不能像正常人那樣分清夢與真實,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會遇到嚴重的障礙。哲學家完全明白常識的含義,但他們不像一般的正常人那樣滿足於此,而是要對人人都視為當然的常識追根究底,追問它們是否真有道理。
按照常識,不管我夢見了什麼,夢只是夢,夢醒後我就回到了真實的生活中,這個真實的生活絕不是夢。可是,哲學家偏要問:你怎麼知道前者是夢,後者不是夢呢?你究竟憑什麼來區別夢和真實?
可不要小看了這個問題,回答起來還真不容易呢。你也許會說,你憑感覺就能分清哪是夢,哪是真實。譬如說,夢中的感覺是模糊的,醒後的感覺是清晰的;夢裡的事情往往變幻不定,缺乏邏輯,現實中的事情則比較穩定,條理清楚;人做夢遲早會醒,而醒了卻不能再醒;如此等等。然而,哲學家會追問你,你的感覺真的那麼可靠嗎?你有時候會做那樣的夢,感覺相當清晰,夢境栩栩如生,以至於不知道是在做夢,還以為夢中的一切是真事。那麼,你怎麼知道你醒著時所經歷的整個生活不會也是這樣性質的一個夢,只不過時間長久得多而已呢?事實上,在大多數夢裡,你的確是並不知道自己在做夢的,要到醒來時才發現原來是一個夢。那麼,你之所以不知道你醒時的生活也是夢,是否僅僅因為你還沒有從這個大夢中醒來呢?夢和醒之間真的有原則的區別嗎?
這麼看來,莊周提出的問題貌似荒唐,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哲學問題。這個問題便是:我們憑感官感知到的這個現象世界究竟是否真的存在著?莊周對此顯然是懷疑的。在他看來,既然我們在夢中會把不存在的東西感覺為存在的,這就證明我們的感覺很不可靠,那麼,我們在醒時所感覺到的我們自己以及我們周圍世界的存在也很可能是一個錯覺,一種像夢一樣的假象。

我們都是孤獨的行路人
感覺能否證明對象的存在
在中國和外國,有相當一些哲學家與莊周抱著相似的看法。他們都認為,我們只能通過感官來感知世界的存在,而感官是不可靠的,所以我們所感覺到的世界只是一種假象。至於在假象背後是否存在著一個與假象不同的真實的世界,他們的意見就有分歧了。有的說有,有的說沒有,有的說沒法知道有沒有。也有許多哲學家反對他們的看法,認為我們的感覺基本上是可靠的,能夠證明我們自己以及周圍世界的真實存在。就拿莊周夢蝶的例子來說,他們會這樣解釋:莊周之所以會夢見自己變成一隻蝴蝶,正是因為他在醒時看見過蝴蝶,如果他從來沒有看見過蝴蝶,他就不可能做這樣的夢了。所以,莊周和蝴蝶的真實存在以及這個真實的莊周看見過真實的蝴蝶是一個前提,而這便證明了醒和夢是有原則區別的,醒時的感覺是基本可靠的。當然,這種解釋肯定說服不了莊周,他一定會認為它不是解答了而是迴避了問題,因為在他看來,問題恰恰在於,當你看見蝴蝶時,你怎麼知道你不是在做夢呢?憑什麼說看見蝴蝶是夢見蝴蝶的原因,其間的關係難道不會是較清晰的夢與較模糊的夢的關係嗎?
在日常生活中,人們都懷著一個樸素的信念,相信我們憑感官所感知的事物是真實存在的。沒有這個信念,我們就不能正常地生活,哲學家也不例外。上述解釋實際上是把這個樸素的信念當成了出發點,由之出發,認定醒時看見蝴蝶的經驗是可靠的,然後再用它來解釋夢見蝴蝶的現象。在哲學史上,這樣一種從樸素信念出發的觀點被稱作「樸素實在論」或「樸素唯物主義」。可是,在莊周這樣的哲學家看來,這種觀點只停留在常識的水平上,不配叫作哲學,因為哲學正是要追問常識和樸素信念的根據。所以,如果你真的對哲學感興趣,你就必須面對莊周提的問題。你很可能不同意他的觀點,但你必須說出理由。你得說明:我們如何知道我們憑感官所感知的現象是真實存在的,而不是一個幻象?感覺本身能否提供這個證據?如果不能,還有沒有別的證據?只要你認真思考這些問題,不管能否找到最後的答案(很可能找不到),你都已經是在進行一種哲學思考了。

我們都是孤獨的行路人
思維能否把握世界的本質
不信任感覺,認為在感官所感知的現象世界背後有一個本來的世界,這實際上是以往多數哲學家的立場。區別在於,有的哲學家斷言我們永遠無法認識這個本來世界,有的哲學家卻相信,我們可以依靠理性思維的能力破除感覺的蒙蔽,透過現象看本質,把握這個本來世界的面目。可是,最近一百多年來,這種長期占統治地位的立場發生了根本的動搖。
理性思維真的能夠把握世界的本來面目嗎?為了解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弄清什麼是理性思維。所謂理性思維,就是我們運用具有普遍性的概念進行判斷、推理的過程。讓我們舉最簡單的加法的例子來說明這個過程。譬如說,桌子上放著一個蘋果,椅子上也放著一個蘋果,問你一共有幾個蘋果,你不需要把這兩個蘋果挪到一起就可以回答說:「兩個。」事實上,當你做出這個回答時,你已經飛快地進行了一個運算:1+1=2。這就已經是一種理性思維了。仔細分析起來,這個過程是這樣的:你首先把「一個蘋果」這樣的具體現象變換為抽像的數字概念「1」,然後運用了一個數學公式(判斷)「1+1=2」,最後又從這個公式推導出「一個蘋果加一個蘋果等於兩個蘋果」的具體結論。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憑感官並不能感知到像「1」「2」這樣的抽像概念和「1+1=2」這樣的抽像命題。那麼,它們是從哪裡來的呢?對於這個問題,有三種可能的回答:
一、我們憑感官可以感知到一個一個的具體東西,也可以感知到它們的集合,抽像的數字概念和算術命題就是從我們的感覺材料中歸納出來的。假定這個答案是對的,那麼,以不可靠的感覺為基礎的理性思維同樣也是不可靠的,並不比感覺更接近那個本來世界。
可是,這第一種回答本身還有著極大的漏洞。我們的感官只能感知個別的具體的現象,從中怎麼能得到抽像概念呢?感官所感知的現象總是有限的,從中又怎麼能得到適用於一切現象的普遍真理呢?譬如說,我們只能看到一個蘋果、一個茶杯、一個人等等,永遠看不到抽像的「1」,思維憑什麼把它們抽像為「1」?我們只能看到一個蘋果和一個蘋果的集合等等,思維憑什麼斷定1+1永遠等於2?由於感性經驗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釋抽像概念和命題的來源,有些哲學家就另找出路,於是有以下第二、第三種回答。
二、抽像觀念和普遍命題是人類理性所固有的,它們如同大理石的紋理一樣潛藏在人類理性之中,在認識過程中便會顯現出來。像「1+1=2」這樣的真理,人類理性憑直覺就能斷定它們是絕對正確的。正是憑借這些先天形式,理性才能夠對感覺材料進行加工整理,使之條理化。這個答案僅是一種永遠無法證實的假說,我們姑且假定它是對的,那也只能得出這個結論:思維形式僅僅屬於人類理性所有,與那個本來世界毫不相干。
三、那個本來世界本身具有一種理性的結構,人類理性是與這個結構相對應的。可是,這一點正是需要證明的,而主張這個觀點的哲學家們沒有向我們提供任何有說服力的證據。
總之,無論在上述哪種情況下,凡我們不信任感覺的理由,對於思維也都成立。所以,看來我們只好承認,只要我們進行認識,不論是運用感覺還是運用思維,所把握的都是現象,它們至多只有層次深淺的不同。世界一旦進入我們的認識之中,就必定被我們的感覺所折射,被我們的思維所整理,因而就必定不再是所謂的本來世界,而成為現象世界了。
世界有沒有一個「本來面目」
好吧,讓我們承認,我們人類所能認識的世界只是形形色色的現象世界。那麼,在這個或者這許多個現象世界背後,究竟有沒有一個不是現象世界的本來世界呢?康德說有的,但我們永遠無法認識,所以他稱之為「自在之物」。我們且假定他說得對,讓我們來設想它會是什麼樣子的。
可是怎麼設想呢?根本無法設想!只要我們試圖設想,我們就必須把自己當作一個認識者,把這個所謂本來世界置於和我們的關係之中,從而它就不再是本來世界,而是現象世界了。也許我們可以想像自己是上帝,因而能夠用一種全知全能的方式把它一覽無餘?可是,所謂全知全能無非是有最完善的感官和最完善的思維,從而能夠從一切角度、用一切方法來認識它,而這樣做的結果又無非是得到了無數個現象世界。我們除非把這無數個現象世界的總和叫作本來世界,否則就根本不能設想有什麼本來世界。
事實正是如此:無論人、上帝還是任何可能的生靈,只要想去認識這個世界,就必須有一個角度。你可以變換角度,但沒有任何角度是不可能進行認識的。從不同角度出發,看到的只能是不同的現象世界。除去這一切可能的現象世界,就根本不存在世界了,當然也就不存在所謂本來世界了。我們面前放著一隻蘋果,一個小男孩見了說:我要吃。他看到的是作為食品現象的蘋果。一個植物學家見了說:這是某種植物的果實。他看到的是作為植物現象的蘋果。一個生物學家見了說:這只蘋果是由細胞組成的。他看到的是作為生物現象的蘋果。一個物理學家見了說:不對,它的最基本結構是分子、原子、電子等。他看到的是作為物理現象的蘋果。一個基督徒見了也許會談論起伊甸園裡的蘋果和亞當夏娃的原罪,他看到的是作為宗教文化現象的蘋果。還會有不同的人對這只蘋果下不同的判斷,把它看作不同的現象。如果你說所有這些都只是這只蘋果的現象,而不是這只蘋果本身,那麼,請你告訴我,這只蘋果本身是什麼東西,它在哪裡?
由於在現象世界背後不存在一個本來世界,有的哲學家就認為一切都是假象,都是夢。在這方面,佛教最徹底,認為萬物皆幻象,世界整個就是一個空。可是,我們不妨轉換一下思路。所謂真和假、實和幻,都是相對而言的。如果存在著一個本來世界,那麼,與它相比,現象世界就是假象。現在,既然並不存在這樣一個本來世界,我們豈不可以說,一切現象世界都是真實的,都有存在的權利?一位詩人吟唱道:「平坦的大地,太陽從東方升起,落入西邊的叢林裡。」這時候,你即使是哥白尼,也不能反駁他說:「你說得不對,地球不是平坦的,而是圓的,太陽並沒有升起落下,而是地球在自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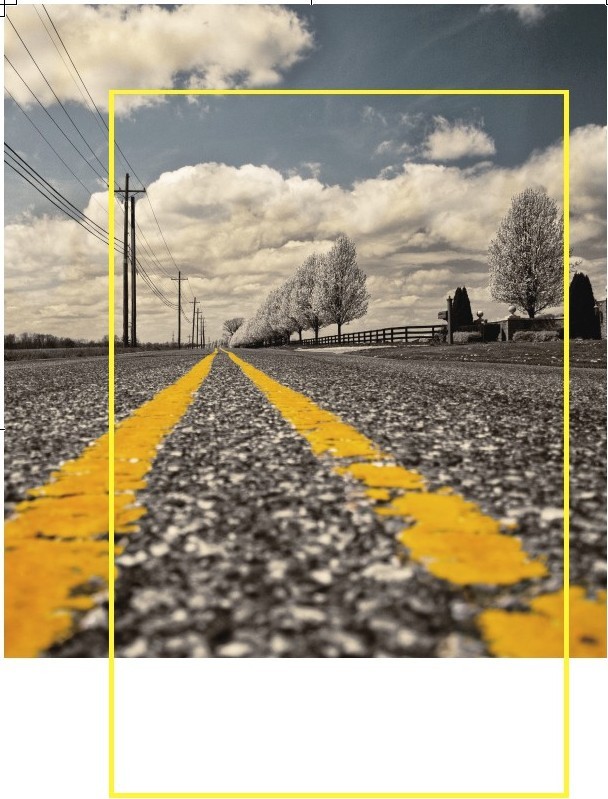
我們都是孤獨的行路人
你的「自我」在哪裡
一個孩子摔了一跤,覺得痛,便說:「我痛了。」接著又說:「我不怕痛。」這個覺得痛的「我」和這個不怕痛的「我」是不是同一個「我」呢?
一個男孩愛上了一個女孩,可是女孩不愛他。他對自己說:「我太愛她了。」接著說:「可是我知道她不愛我。」然後發誓道:「我一定要讓她愛上我!」在這裡,愛上女孩的「我」、知道女孩不愛自己的「我」,以及發誓要讓女孩愛上自己的「我」又是不是同一個「我」呢?
一位著名的作家歎息說:「我獲得了巨大的名聲,可是我仍然很孤獨。」這個獲得名聲的「我」和這個孤獨的「我」是不是同一個「我」?
我在照鏡子,從鏡子裡審視著自己。那個審視著我自己的「我」是誰,那個被我自己審視的「我」又是誰,它們是不是同一個「我」?
你拉開抽屜,發現一張你小時候的照片,便說:「這是小時候的我。」你怎麼知道這是小時候的「我」呢?小時候的「我」和現在的「我」是憑什麼成為同一個「我」的呢?
夜深人靜之時,你一人獨處,心中是否浮現過這樣的問題:「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將到哪裡去?」
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把「認識你自己」看作哲學的最高要求。可是,認識「自我」真是一件比認識世界更難的事。上面的例子說明,它至少包括以下三個難題:
第一,我有一個肉體,又有一個靈魂,其間的關係是怎樣的?有人說,靈魂只是肉體的一種功能。如果真是這樣,為什麼靈魂有時候會反叛肉體,譬如說,會為了一種理想而忍受酷刑甚至犧牲生命?如果不是這樣,靈魂是不同於肉體並且高於肉體的,那麼,它也必有高於肉體的來源,那來源又是什麼?如此不同的兩樣東西是怎麼能夠結合在一起的?既然它不來源於肉體,為什麼還會與肉體一同死亡?或者相反,在肉體死亡之後,靈魂仍能繼續存在?
第二,靈魂究竟是什麼?如果說它是指我的全部心理活動和內心生活,那麼,它就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東西。一方面,它包括理性的思維、觀念、知識、信仰等等。另一方面,它包括非理性的情緒、情感、慾望、衝動等等。其中,究竟哪一個方面代表真正的「自我」呢?有的哲學家主張前者,認為理性是人區別於動物的本質特徵,因而不同個人之間的真正區別也在於理性的優劣強弱。有的哲學家主張後者,認為理性只是人的社會性一面,個人的真正獨特性和個人一切行為的真實動機深藏在無意識的非理性衝動之中。他們究竟誰對誰錯,或者都有道理?
第三,我從小到大經歷了許多變化,憑什麼說我仍是那同一個「我」呢?是憑我對往事的記憶嗎?那麼,如果我因為某種疾病暫時或長久喪失了記憶,我還是不是「我」呢?是憑我對我自己仍然活著的一種意識,即所謂「自我意識」嗎?可是,問題恰好在於,我是憑什麼意識到這仍然活著的正是「我」,使我在變化中保持連續性的這個「自我意識」究竟是什麼?
現在我把這些難題交給你自己去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