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語言的其他形式那樣,詛咒可以說是無處不在的,儘管它的普遍存在是有條件的。當然,由於時空的變遷,被視為禁忌語的那些具體詞語和概念也在不斷發生著變化。在語言發展的歷史過程中,我們經常能夠發現一些原本乾乾淨淨的詞語變得越來越污濁不堪,相反,一些原本骯髒下流的詞語卻被歲月漂洗得一塵不染。舉例來說,當今天的英語使用者在早期的醫學教科書上讀到“女性膀胱頸短,靠近the cunt”時,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都會為此大跌眼鏡的。然而,這是《牛津英語字典》援引自15世紀課本中的原話。記錄此類語言演變的歷史學家傑弗裡·休斯(Geoffrey Hughes)指出:“隨著生機勃勃的男性內褲廣告的問世,蒲公英可以被稱作pissabed、shitecrow、windfucker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禁忌語命運的變遷還直接影響著一部文學作品的可接受性。舉例來說,因為“黑鬼”(nigger)一詞,《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Huckleberry Finn)不止一次被美國學校定性為禁書。儘管這個詞從來就不是個禮貌術語,但是,對於當今的讀者來說,它遠比在馬克·吐溫那個時代的煽動力更強。
當然,隨著時間的推移,一些詞語也從它們的禁忌身份中解放了出來。《賣花女》(Pygmalion)中有這樣一個情節,在一次上流社會的茶會上,女主角伊莉莎·杜利特爾尖聲地喊道:Not bloody likely!(這絕對不可能!)1914年,這部作品被搬上了銀幕,電影中,杜利特爾的這句話不僅令她身邊的那些虛構人物心生反感,就連觀眾也無不對她嗤之以鼻。然而,到了1956年,當這部作品被改編成音樂劇《窈窕淑女》(My Fair Lady)時,bloody(血腥)一詞已經變得毫無驚艷之處,以致編劇們竟然擔心這個詞是不是還能達到原來的詼諧效果。為此,他們還特意添加了這樣一個場景——伊莉莎被帶到愛斯科特賽馬會上,她朝一匹馬尖聲地喊道:Move your bloomin’arse!(甩開你的大屁股,快跑啊!)現在,許多父母都經歷過這樣的難堪,孩子們從學校回來,天真無邪地使用著一些動詞,如,suck(吸吮)、bite(咬)、blow(吹),殊不知,這些詞均源於描寫口交(fellatio)的詞語。不過,家長們是否也考慮過他們自己也不加思索地使用著那些如今被視為無傷大雅的單詞呢?比如,sucker(笨蛋,源自cocksucker)、jerk(混蛋,源自jerk off)以及scumbag(人渣,源自condom)。在這方面,喜劇演員們曾做過很多努力,他們希望通過不斷地重複使用這些猥褻詞語,使之最終達到脫敏點(the point of desensitization,也就是心理語言學家所說的語義飽和過程),或者瞬間將自己扮演成語言學教授,以此呼籲大家去關注語言符號的任意性(arbitrariness)原則。以下片段摘自著名的萊尼·布魯斯語錄。
Tooooooo是個前置詞。To是個前置詞。Commmmmme是個動詞。To是前置詞。Come是個動詞。To是個前置詞。Come是個動詞,一個不及物動詞。To come.To come……這就像一個大架子鼓的獨奏:To come to come, come too come too, to come to come uh uh uh uh uh um um um um um uh uh uh uh—TO COME!TO COME!TO COME!TO COME!—Did you come?Did you come?
Good.Did you come good?Did you come good?Did you come?Good.To.Come.To.Come—Did you come good?Didyoucomegooddidyoucomegood?
下面這個片段摘自卡林關於“7個禁忌語”的獨白。
Shit、Piss、Fuck、Cunt、Cocksucker、Motherfucker還有Tits,哇。你知道,Tits根本不應屬於這個列表。它聽起來如此親切,像個暱稱。聽起來像一個暱稱。“嘿,Tits到這兒來。Tits,這位是Toots。Toots,這位是Tits。Tits,這是Toots。”它聽起來像一份小吃,不是嗎?是的,我知道,它確實像。不過,我並不是暗指那個男性至上主義的小吃,我是想說,新納貝斯克(食品公司)Tits、新奶酪Tits、玉米Tits以及比薩Tits、芝麻Tits、洋蔥Tits、馬鈴薯Tits,是的。
現在,tits這個詞已經是個乾淨的詞語了,它已不會被列入《清潔電視廣播法案》,而且完全可以堂而皇之地出現在嚴肅報刊“灰色女士”(The Gray Lady),即《紐約時報》上。[12]不過,並不是所有禁忌語都有tits的運氣,幾個世紀以來,它們中的許多詞語始終被禁忌著,而且,就像Steve(史蒂夫)的興衰史那樣,在歷史的長河中,究竟哪些詞會被淨化、哪些會被污染,一直是個變化莫測、反覆無常的迷。
類似的脫敏運動(desensitization campaigns)將目標指向了一些婦女和少數族裔的渾名,在這類人群內部,人們盡量有意地、堂而皇之地使用這些渾名,目的是希望將它們“沙化”(reclaim)。因此,我們的語言中有NWA(Niggaz With Attitude,即暴躁的黑鬼,一個黑人嘻哈樂團)、Queer Nation(酷兒國度)、queer studies(酷兒研究)、Queer Eye for the Straight Guy(美國一檔極其火爆的電視節目《粉雄救兵》,一群在各行各業有成就的男同性戀者為在事業和生活各個方面失意的異性戀男人出謀劃策的故事)、Dykes on Bikes(機車女同志,一群騎摩托車的女同性戀)及其網址www.classicdykes.com;我們還有Phunky Bitches(在線婊子),一個“面向女性(以及男性)的實時在線社團,致力於現場音樂表演、旅遊以及其他一些有趣的事情”。在(猶太)寺廟兄弟會上,我從來沒有聽過會員們互相這樣打招呼:“咋樣,猶太佬!”但是,在20世紀70年代,小說家金基·弗裡德曼(Kinky Friedman)卻領導了一個取名為“德州猶太小子”的鄉村樂隊,此外,還有一本專門為年輕猶太讀者創辦的嘻哈雜誌,取名為Heeb(對猶太人的蔑稱)。不過,令人遺憾的是,這些詞語並沒有被中性化成反抗和團結的象徵,準確地說,這是因為在大多數語言社團裡,它們仍然具有很強的冒犯性。倒霉總是青睞那些不知情的局外人,在電影《尖峰時刻》(Rush Hour)中,成龍扮演了一個香港偵探,他傻傻地模仿著他的非裔美國人搭檔向一個洛杉磯酒吧黑人老顧客打招呼“咋樣,黑鬼”,於是引起了一場小騷亂。
當一種語言中的某些特定詞語進入另一種語言時,它們的攻擊力會變得更加強大。在魁北克法語中,merde(相當於英語中的shit)遠比其英語對等詞shit溫和,它更接近於英語中的crap的意思;此外,還有con(相當於英語的idiot)這個詞,大多數人至多也就依稀地知道,它原本是cunt的意思。這還不算最糟糕的,在魁北克法語裡,最糟糕的是你對一個人說Tabernac!(相當於英語中的tabernacle[聖體龕])、alisse!(英語chalice中的[聖盃])、Sacrement!(英語sacrament中的[聖餐])。2006年,天主教會將這幾個詞語連同它們的原始宗教定義噴繪在戶外廣告板上,希望借此沙化這些詞。(一位專欄作家感歎道:“難道沒有什麼神聖可言了嗎?”)目前,在其他天主教地區,宗教褻瀆語十分常見,這種情況與英格蘭宗教改革前的情況十分相似,有關性和糞便的各種術語氾濫成災。
不過,除了這些跨時空的語言變體外,我敢說,世界上絕大多數語言中(或許是全部)都存在著許多用於非高雅社交場合的、富有情感的詞語。一個最極端的例子也許當屬澳大利亞的Djirbal語,一種當地的土著語言。這種語言的特點是,只要是在婆婆和某些堂兄妹面前,“每一個詞”都是禁忌語。當這些親屬在身邊的時候,人們不得不使用一套完全不同的詞語(儘管語法相同)。當然,這只是個極端的例子,像英語和法語那樣,其他大多數語言中的詛咒詞語一般都來自這些有限的話題:性、排泄物、宗教、死亡與疾病,此外還有一些令人不爽的社會群體。
對於聲稱某某語言中根本沒有猥褻語的言論,我們不得不採取客觀的接受態度。事實是,在許多地區,假如你要求那裡的人列出他們的髒話,他們很可能會表示抗議。但請不要忘記,髒話和虛偽總是結伴而行的,一些性格調查問卷甚至將人們對“我有時說髒話”作為核實一個人是否說謊的選項。在《污言穢語已刪除:對髒話的認真思考》(Expletive Deleted:A Good Look at Bad Language)一書中,語言學家露絲·韋津利(Ruth Wajnryb)記錄了這樣一個事實。
利用我獲取日語數據的問題,我的一個被調查者,一位娶了日本女人的英國紳士,對他的妻子進行了問卷調查。她告訴他,她無法回答這些問題,因為她根本不知道日語中有什麼髒話。在明知自己丈夫心知肚明的情況下,她瞪著一雙無辜的大眼睛望著自己的丈夫所說的這番話確實讓人領教了她在這方面的本事。
《褻瀆性格言:言語侵犯研究國際期刊》(Maledicta: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erbal Aggression)上的一篇綜述文章中收錄了大量的性侮辱和低俗的日語詞語,此外,發表在那本期刊上的其他跨文化調查也給出了一些類似的詞彙表。
事實上,禁忌語只是一種叫作“咒語”(word magic)的語言現象的其中一個組成部分,也就是說,咒語所涉獵的範圍更大。儘管音、義結合的任意性是語言學的基礎前提之一,但多數人卻直覺地認為,這其中一定還潛藏著其他奧秘。他們將一個實體的名稱作為其本質,因此,說出一個名稱這樣簡單的行為卻被看成是對其所指稱物的侵犯。
咒語、法術、祈禱以及詛咒是人們試圖通過言語影響世界的一種途徑,相反,禁忌語和委婉語則是人們盡量不去影響它的一種手段。在提及一個期盼的事件之後,就連那些頭腦冷靜的唯物主義者們也會下意識地敲敲木頭[13];而當提及一樁可怕的事情時,他們則會插上一句God forbid(上帝禁止它,即但願別發生這種事);也許出於同樣的原因,丹麥著名物理學家尼爾斯·波爾(Niels Bohr)在他的辦公室門上掛了一隻馬蹄鐵:“我聽說,即使你不信它,它也會顯靈的。”
禁忌語最擅長捕獲人們的注意力
咒罵的普及性及其威力表明,禁忌詞語很可能被接進了情緒腦(emotional brain)的古老而深遠的部位。在引言中,我們已經瞭解到,詞語不僅有外延而且還有內涵:一種與該詞字面所指並不完全等同的情感色彩,例如“有原則的”之於“頑固的”、“窈窕的”之於“骨瘦如柴的”。這種語義上的差別讓我們想起了禁忌詞語與它們的近義詞之間的區別,例如,shit與feces、cunt與vagina、fucking與making love等。早在很久以前,心理語言學家們就甄別出了詞語內涵的3個主要不同方面:好與壞、弱與強、積極與消極,儘管內涵肯定還會有其他維度。舉例來說,“英雄”是好的、強大的、積極的;“懦夫”是不好的、懦弱的、消極的;“叛徒”是邪惡的、軟弱的、主動的。所有禁忌詞都彙集在非常壞、非常強的邊緣地帶。
那麼,內涵與外延真的被存儲在大腦的不同部位了嗎?其實這並沒有什麼難以置信的。除了其他系統外,哺乳動物的大腦中還有一個邊緣系統(limbic system),該系統是一個調節動機和情緒的古老的網絡系統、一個新大腦皮質(neocortex),即大腦的褶皺表面,它隨著人類的進化而激增,它是感知、知識、推理和規劃的加工中心。這兩個系統相互關聯、協同工作,因此,我們有理由假設,詞語的外延集中在新大腦皮質,尤其是在大腦左半球,而詞語的內涵則遍佈新大腦皮質與邊緣系統的連接處,尤其是在大腦的右半球。
在邊緣系統內部可能存在著一個組織,這個組織就是大腦杏仁核(amygdala),一個埋在大腦顳葉(兩側半球每側各一個)前部的、杏仁狀的器官,它協助大腦授予人們記憶與情感。一側杏仁核被移除的猴子雖然還能學會識別一種新形狀,比如一個帶條紋的三角形,但卻很難再學會那些預示令人不快的事件的形狀(比如一次電擊)。就人類而言,當一個人看到一張憤怒的面孔或者一個令人不快的單詞,尤其是一個禁忌詞時,其大腦中的這個杏仁核就會被“點燃”——在大腦掃瞄中,它會表現出更多的代謝活動。事實上,在還未掌握掃瞄工作中的人類大腦這項技術之前的很多年,心理學家們就已經掌握了測量一個禁忌詞影響人的情緒的技術,他們將一個電極綁在人的手指上,測量由突如其來的汗波(wave of sweat)所造成的皮膚電傳導的變化。這種皮膚反應伴隨著杏仁核內部的活動,而且,正如從杏仁核本身記錄下來的內部活動那樣,它可以由禁忌詞觸發產生。詞語的情感色彩或許是在兒童時期習得的:在表達思想方面,雙語使用者們通常會覺得自己的第二語言在表達思想上不如第一語言那麼酣暢淋漓,相比於第二語言,第一語言中的禁忌詞語和譴責更容易令他們的皮膚作出相應的反應。
雙語使用者這種下意識的不寒而慄是由聽到或讀到一個來自語言系統某個基本特徵的禁忌詞觸發的:詞義的理解是機械的。這並不是因為我們沒有可以將不想聽的聲音拒之耳外的“耳塞子”(earlids),而是因為,一旦一個單詞被看到或聽到,我們根本無法將它當作一幅塗鴉或一聲噪聲;相反,我們會條件反射般地在記憶中進行搜索,並對其含義作出相應的反應,其中包括它的內涵。
THE STUFF OF THOUGHT 語言與思想實驗室
斯特魯普效應(Stroop effect)就是這方面的一個典型例證。打開任何一本心理學教科書,你都可以看到有關這個實驗的介紹,不僅如此,到目前為止,僅圍繞這一主題撰寫的科學論文就有4000多篇。這個實驗的情況大致是這樣的:實驗人員要求受試者迅速觀看一個字符串列表,然後讓他大聲地說出每個字符的印刷顏色。下面請你試一下這組字符,從左向右依次大聲說出:black(黑色)、white(白色)、gray(灰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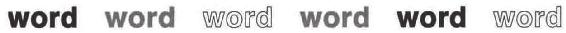
這應該是個極其簡單的任務。再請看下面這組字符,這一組字符應該更容易說出。

現在請注意,說出下面這組字符將要比說出上面那兩組困難得多。

針對上述現象,心理學給出了如下的解釋:就識字的成年人而言,朗讀單詞這種技能已經被他們過度習得(overlearned)至一種強制的程度:即使你設法忽略這些詞語的含義,而將精力集中在它們的印刷顏色上,你也無法用主觀意志力將這一過程“關閉”。這就是為什麼當實驗人員將字符安排成與其含義相同的顏色時,你就能迅速地讀出它們,而當他們將字符安排成不同於其含義的顏色時,你的閱讀速度就會減緩的原因。與此類似的表現還有口頭命名的情況,實驗中,實驗人員要求人們對下面這樣的顏色塊進行命名。

當受試者佩戴的耳機裡傳出“黑色、白色、灰色、白色、灰色、黑色”的指令時,這組讓人分神的顏色詞順序會加強這項任務的難度。
我們說過,禁忌語是最擅長捕獲人們的注意力的。現在,你可以通過這個斯特魯普效應來親自感受一下它們在這方面的特長。下面請你嘗試著命名這些單詞的印刷顏色。

心理學家唐·麥凱(Don MacKay)也曾做了這個實驗,他發現當人們的目光落在每個單詞上時,一種下意識的猶豫的確減緩了他們的命名速度。他所得出的結論是,一個語者或作者完全可以利用一個禁忌詞來喚起受眾的情感反應,不過,這種做法相當違反他們的意願。
一些企業利用僅次於禁忌語的名詞為它們的產品命名,希望借此來吸引顧客的注意力,實際上,它們是在開發利用斯特魯普效應的潛能,比如,那個名為Fuddruckers(福德洛克)的連鎖酒店、FCUK(French Connection UK,意為英國法式連結)服裝品牌以及電影《拜見岳父大人》(Meet the Fokkers)。在語言發展的歷史過程中,人們對禁忌語的下意識反應實際上有助於塑造一種語言。我這麼說的根據來自於一個語言版本的格雷沙姆定律(Gresham's Law):壞的言辭將好的言辭驅逐出語言流通域。人們通常會避免使用那些可能會被誤解為髒話的術語。Coney原本是一個指稱rabbit(兔子)的舊名稱,它與honey(蜂蜜)諧音,但在19世紀晚期,它退出了語言歷史的舞台,究其原因,這很可能是因為它聽起來有點過於接近cunt了。與coney有著類似經歷的還有下面這些詞的禮貌含義:cock、prick、pussy、booty以及ass(至少美國人用ass;英國人仍然用arse這個粗魯名詞,ass在英國只有驢子的意思)。取名Koch(科赫)、Fuchs(福克斯)、Lipschitz(李普希茨)的人,常常會改變他們的姓氏,比如,Louisa May Alcott(路易莎·梅·奧爾科特家族)之前的姓氏是Alcox(阿爾科克斯)。1999年,在一次管理層會議上,由於在預算中使用了niggardly(吝嗇的)這個詞,華盛頓特區市長助理被迫辭職。原因是,他的一個同事對這個詞非常不滿,事實上,niggard(吝嗇鬼)是一個中古英語詞,意為miser(吝嗇鬼),而nigger(黑鬼)這個綽號則是從幾個世紀之後才進入到英語中的西班牙語negro演變而來的,在西班牙語中,negro是個表示“黑色”的單詞。換句話說,niggardly與nigger毫不相干。然而,無論對市長助理或niggardly這個單詞來說有多麼不公平,niggardly這個詞注定逃脫不了被淘汰的厄運。同樣的厄運還降臨到了queer(奇怪的/同性戀)和gay(快樂的/同性戀)這兩個指稱同性戀者的名詞的原始含義上。
正如聽到別人說髒話那樣,大聲咒罵將觸及大腦深處那個古老的部位。失語症(Aphasia)是一種語言遺失現象,由腦皮質和腦白質損傷造成,腦白質沿著大腦橫斷面(大腦外側裂)潛存於大腦的左半球中。神經學家們幾乎在失語症研究初期就注意到,失語症病人並沒有喪失詛咒的能力。英國一個失語症病例的研究記錄顯示,該患者反覆地說Bloody hell、Fuck off、Fucking fucking hell cor blimey以及Oh you bugger等。此外,神經病學家諾曼·格什溫德(Norman Geschwind)還曾經對一個美國病人進行過跟蹤研究,該患者因腦癌切除了整個大腦左半球。病人不能說出圖片的名稱、不能說或聽懂別人的話語、不能重複多音節的單詞,然而,在1次5分鐘的採訪過程中,他竟然重複地說了7次Goddammit、1次God和1次Shit。
失語症患者咒罵能力的倖存表明,禁忌的渾名是以預先構造的公式形式(prefabricated formulas)存儲於大腦右半球中的。此類公式位於一端始於命題話語的連續統的另一端,在這個連續統中,按照語法規則,詞語組合表達概念組合的含義。這並不是說大腦右半球裡包含著一個髒話模塊(profanity module),而是說明大腦右半球的語言能力受限於存儲於記憶中的那些公式,而不是由規則制約的句法組合。一個單詞就是一個典型的記憶組塊(chunk),而且,對於許多人來說,他們的大腦右半球中都有一個相當數量的詞彙表被用於話語理解。不僅如此,大腦右半球中可能還存儲著一些由規則制約的語言特殊形式的對應體,如動詞的不規則變化形式。此外,它還常常參與調配較長的記憶公式,比如,歌詞、祈禱以及um(嗯)、boy(嘿,乖乖)、well yes(嗯,可以啊)等插入語,此外還有會話起始語,例如,I think(我認為)、You can't(你不能),等等。
我們說大腦右半球與髒話有關還有另外一個原因:相比於大腦左半球,右半球更熱衷於參與人們的情緒波動,尤其是消極情緒的波動。事實上,那些禁忌諢名也許並不是大腦右半球中的大腦皮層觸發,它們很可能是由一個更早進化的大腦結構,即那個被叫作基底神經節的大腦結構所觸發。基底神經節(basal ganglia)是一組深埋在大腦前半部的神經元集群。它們的環路會從大腦的許多其他部位接收輸入,其中包括杏仁核以及邊緣系統的其他部位,然後將這些信息回送到大腦皮質,主要是大腦前額葉(frontal lobes)。大腦前額葉的功能之一就是將運動或推理順序打包進一些組塊,當我們學習一種技能時,那些組塊可以用來進一步重組。大腦前額葉的另一個功能是抑制那些被打包進組塊中的行為的執行。由於基底神經節組件彼此相互抑制,因此,不同部分的損傷會產生相反的效果。如果一部分基底神經節發生了退變,則很可能會引發帕金森氏病,其臨床表現為顫抖、僵硬、運動困難。如果是另一部分基底神經節發生退變,則會導致亨廷頓氏舞蹈症,其臨床表現為舞蹈性運動和失控性運動。
我們有兩條證據線索可以證明基底神經節(扮演著行為的打包者和抑制者的雙重角色)與人類的咒罵行為有關。一條線索來自於一個右基底神經節中風病人的病例研究,此次中風給患者留下了一種經典失語症的鏡像綜合征。該患者能用語法句進行流利的交談,但卻無法唱出自己熟悉的歌曲,無法背誦原本諳熟的祈禱文、祝福語或者髒話——即使你說出某句髒話的一部分並引導他將那句髒話補充完整,他也做不到。
除了打包者和抑制者的雙重角色外,基底神經節在人類的咒罵行為中還扮演著一個更著名的角色。20世紀80年代,圖雷特綜合征(Gilles de la Tourette Syndrome),或稱妥瑞綜合征(Tourette syndrome)或簡稱為妥瑞症(Tourette's)突然出現在很多電視劇的情節中,對當時的許多人來說,這種症狀十分令人費解。妥瑞症其實就是一種由基底神經節部分遺傳性畸形造成的神經疾病。就像電視迷們所瞭解的那樣,它最顯著的症狀就是發聲痙攣,同時患者還會高聲喊出猥褻的言辭、民族禁忌語及其他各類污言穢語。醫學上稱這種症狀為穢語症(coprolalia),coprolalia這個希臘詞根還見於下面一些單詞,例如,coprophilous(癖糞的,生存於糞便之中)、coprophagy(食糞症,以糞便為食)以及coprolite(糞化石,石化的恐龍糞便)等英語單詞。事實上,只有少數患有圖雷特綜合征的人才會患上穢語症,較常見的痙攣包括眨眼,面部肌肉迅速抽動,發出怪異的聲音、重複的詞語或音節。
穢語症不僅為我們呈現了一個完整的禁忌範疇,而且還包括了不同語言的相似含義,這一事實表明,詛咒行為確實是一種連貫的神經生物學現象。最近,一篇文獻綜述列出了下列一些美國圖雷特綜合征病人喊出的污言穢語,依次從最頻繁到最罕見:
fuck、shit、cunt、motherfucker、prick、dick、cocksucker、nigger、cockey、bitch、bastard、tits、whore、doody、penis、queer、pussy、coitus、cock、ass、bowel movement、fangu、homosexual、screw、fag、faggot、schmuck、blow me、wop
病人也有可能喊出較長的表達式,例如,Goddammit、You fucking idiot、Shit on you以及Fuck your fucking fucking cunt。該文獻還例舉了西班牙語病人的穢語,它們是:puta、mierda、co?o、joder、maricon、cojones、hijo de puta、hostia。日語病人的穢語列表包括:sukehe、chin chin、bakatara、dobusu、kusobaba、chikusho以及一個在列表中被小心地界定為“女性的性部位”的空白。綜述中甚至還報告了一個耳聾妥瑞氏症患者用美國手語表達的fuck和shit。
圖雷特綜合征患者突然爆發出的污言穢語不只是一種無意識的經驗,而是對一種難以抗拒的衝動的反應,這就好比無法抗拒的瘙癢,或者愈演愈烈的眨眼或打哈欠的慾望一樣強烈。這種無法拒絕的衝動與人類自我控制的較量讓人想起了一種被稱為“恐怖誘惑”的強迫症(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簡稱OCD)——一種可能令人作出可怕事情的具有強迫性的恐懼,比如,在一個擁擠的劇院中高喊“著火了”或者把某人推下地鐵站台。像妥瑞症(強迫症常常伴隨妥瑞症)那樣,強迫症似乎也涉及制動機制與基底神經節加速環路間的一種不平衡。這說明,基底神經節的作用之一是將某些想法和慾望指派成不可思議的東西——禁忌語,以便使它們處於自己的掌控之中。通過標注、封裝、抑制這些想法,基底神經節解決了這樣一個悖論,即為了瞭解什麼是不該加以思考的,人們卻不得不去思考那些不該思考的東西——這就是為什麼人們無法按照指令做到“不要去想一頭大象”。正常情況下,基底神經節能夠利用一個“不要去那裡”的指令將我們的壞思想和壞行為巧妙地隱藏起來。但是,當基底神經節遭到削弱時,它們的加密鎖和安全制動裝置就會瓦解,於是,那些被我們標注為不可思議的或不能說的想法就會肆意地溜躂出來。
在未受損傷的大腦中,大腦操作系統(包括前額皮質和大腦邊緣系統的另一個部分,即前扣帶皮質)能夠對大腦的其他部位發出的行動實施監視,並將其攔截在途中。當彬彬有禮的朋友們一起聊天時,或者當一個牧師和老處女碰了自己的腳趾頭時,那些從他們嘴裡溜出來的、略有刪減的咒罵(truncated profanities)就是這麼來的:每一句標準的污言穢語都會提供一些刪減後的替換選擇。
god的替換選擇:egad、gad、gadzooks、golly、good grief、goodness gracious、gosh、Great Caesar's ghost、Great Scott
Jesus的替換選擇:gee、gee whiz、gee willikers、geez、jeepers creepers、Jiminy Cricket、Judas Priest、Jumpin’Jehoshaphat(傳說中猶大國王的名字,表示驚訝)
Chris的替換選擇:crikes、crikey、criminy、cripes、crumb
damn的替換選擇:dang、darn、dash、dear、drat、tarnation
goddam的替換選擇:consarn、dadburn、dadgum、doggone、goldarn
shit的替換選擇:shame、sheesh、shivers、shoot、shucks、squat、sugar
fuck和fucking的替換選擇:fiddlesticks、fiddledeedee、foo、fudge、fug、fuzz;effing、flaming、flipping、freaking、frigging
bugger的替換選擇:bother、boy、brother
bloody的替換選擇:blanking、blasted、blazing、bleeding、bleeping、blessed、blighter、blinding、blinking、blooming、blow
《賣花女》中有這樣一個情節,管家皮爾斯夫人告誡亨利·希金斯不要在伊莉莎的面前說髒話。
皮爾斯夫人:……有一個特殊的詞我必須要求你不要使用。因為洗澡水太熱,那個女孩自己(伊莉莎)剛剛說出了它。它的首字母與bath的首字母相同。沒有人比她更瞭解這個詞:她是在她母親的膝蓋上學會的,但她絕不能從你的嘴裡聽到這個詞。
希金斯(傲慢地):我不能因為說過這個詞就責備自己,皮爾斯夫人。(她死死地盯著他。他一邊用一種公正的樣子掩飾著內心的不安,一邊補充說)也許除了在極端興奮的時刻。
皮爾斯夫人:就在今天早上,先生,你就將這個詞用在你的靴子、黃油和黑麵包上了。
希金斯:哦,原來是那個啊!那只不過是為了押頭韻而已,皮爾斯夫人,對於一個詩人來說,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
詩人們所說的那些自然的修辭手段實際上是大多數禁忌詞語的委婉形式的來源。在我們剛剛看到的那個改了調的髒話列表中,是頭韻(alliteration)和諧音(assonance)在起著積極作用。就是這個韻律將bloody變成了ruddy、son of a bitch變成了son of a gun。此外,我們還有其他幾十個倫敦俚語中禁忌語的委婉說法也是這樣演變出來的,比如,raspberry(樹莓,源自raspberry tart,樹莓餡餅)替代了fart、Friar(男修道士,源自Friar Tuck,塔克修道士)替代了fuck。還有法語中那個老套的髒話Sacre bleu!變成了委婉說法Sacre Dieu。
一般來說,這些詩學手段通常會對我們心智中某種組織詞語的心智結構進行重複,比如,音節首輔音(onsets)、韻律(rimes)、音節尾輔音(codas)。音位學家已經甄別出另一些更複雜的結構,構成一個單詞的音節被連接到一個界定這一單詞的節拍及其結構的骨架上。在詩歌或修辭中,當一個語言框架的部分被重複時,這就是所謂的平行結構,就像第23首《聖經》詩篇中所描寫的He makethme to lie down in green pastures/He leadeth me beside the still waters(他讓我躺臥在青草地上/他領我來到安靜的溪水邊)那樣。在咒罵的王國裡,這種平行結構在無數胡說八道的委婉表達式中隨處可見,這些委婉形式所共享的只是這種結構的韻律和形態結構。許多表示“偽善”的術語都是由兩個重讀單詞構成的合成詞,它們要麼是單音節詞,要麼是首音節重讀的一重一輕的單詞。
applesauce(胡說)、balderdash(胡言亂語)、blatherskite(愛說廢話的人)、claptrap(討好的)、codswallop(廢話)、flap-doodle(瞎說)、hogwash(廢話)、horsefeathers(胡說八道)、humbug(騙子)、moonshine(突談)、poppycock(廢話)、tommyrot(無聊)
謾罵術語的另一個來源是語音象徵。人們在謾罵時,往往會使用那些聽上去既快又刺耳的語音。它們往往是單音節或首音節重讀的單詞,並且往往包含短元音和阻塞音(stopconsonants),尤其是/k/和/g/這兩個爆破音。
fuck、cock、prick、dick、dyke、suck、schmuck、dork、punk、spick、mick、chink、kike、gook、wog、frog、fag
pecker、honky、cracker、nigger、bugger、faggot、dago、paki
20世紀70年代,我的一位朋友曾經見過這樣一張保險槓貼紙,上面寫著:NO NUKES(禁止核武器),那個時候他還不知道這個術語,於是他竟認為那是一個種族主義的口號!休斯指出:“儘管下面這一觀點可能會遭到合理的反對,即多數謾罵行為並非獨創……不過,它與詩意之間的某些親密關係確實可以被觀察到。在謾罵與詩歌創作這兩個領域中,語言的使用不僅是高負荷的,而且都極具隱喻性;它們所表現出的極致和銳利的效果都是通過壓頭韻,或者通過挑起詞語在不同語域間的對抗而創造出來的,而且韻律至關重要。”
咒罵語義學
既然我們已經大致瞭解了一些有關咒罵語言學、咒罵心理學、咒罵神經邏輯學等方面的知識,那麼,現在我們是否就能找到一條有關詛咒的含義與用法的共同主線了呢?是的。一條最明顯的主線就是它們帶給人們的強烈負面情緒。由於人們對語言的感知是在無意識或者下意識的情況下進行的,因此,他們的注意力會不知不覺地被某個禁忌詞語所捕獲,並被迫去思考其令人不爽的內涵。正是出於這個原因,只要與他人交流,我們就有可能遭受精神上的打擊,就好像我們被綁在一張椅子上,隨時都有可能遭人一擊。要想徹底搞清楚咒罵這種語言現象,我們必須首先弄明白這樣兩個問題:第一,什麼類型的想法會令人感到沮喪;第二,人們為什麼會希望將這些不愉快的想法強加於人。
說來也怪,宗教竟然是英語及其他許多語言的咒罵語的發祥地。這一點在許多方面都能得到印證,舉例來說,《聖經》的第三誡就是個最好的證明。此外,hell(地獄)、damn(該死的)、God(上帝)、Jesus Christ(耶穌基督)等詞語的風靡以及用於指稱禁忌的許多術語本身:profanity(不敬的言語,非神聖的)、blasphemy(褻瀆神明,字面意思是“邪惡的言論”,但在實際使用中指對神性的不敬),還有swearing(咒罵)、cursing(詛咒)、oaths(發誓賭願),這些詞原本是指借用某個神或其某個象徵(另類地出現在天主教的詛咒中的詞語,比如,聖體龕[tabernacle]、聖餐杯[chalice]、聖餅[wafer]等)的符咒來擔保的意思。
在當今英語國家中,宗教詛咒行為幾乎不會讓人感到有任何驚奇之處。一句Frankly, my dear, I don't give a damn.(坦白地說,親愛的,我根本不在乎)會驚得觀眾一片嘩然的年代已經隨風而逝了。今天,如果再有哪個角色被這樣的語言所激怒的話,這只能說明他是個老古董了。宗教禁忌詞語在民間的氾濫是西方文化“世俗化”的最直接後果。正如切斯特頓(G.K.Chesterton)所評論的那樣:“褻瀆神明的現象不可能比宗教本身出現得更早;如果有人對此表示懷疑的話,那麼就讓他去褻瀆奧丁神試試吧。”因此,要想理解這些宗教粗口,我們必須站在語言祖先的角度上設身處地地想想上帝和地獄到底對誰來說才是真實的。[14]
Swearing(發誓/咒罵)和oaths(宣誓/詛罵)的字面意思是“某人對履行自己的承諾而作出的擔保”。這個字面意思往往會將人們帶入那個充滿矛盾策略(paradoxical tactics)的奇愛博士的世界[15],在那裡,人們出於個人利益,心甘情願地自我設限(self-handicapping)。以承諾為例:如果你需要向別人借錢,你必須承諾歸還;如果你需要某人為你生兒育女,並發誓放棄一切、一心忠於你,你就必須保證要以同樣的忠誠對待對方;你也許需要與他人做生意,為了得到你眼下所需要的東西,作為交換條件,你就得承諾將來會如期交貨或保證服務。現在的問題是,那個受約人(promisee)為什麼要相信你呢?很顯然,如果食言,受益者很可能是你。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是,假如你確實食言了,你就得自願承擔一種懲罰,而且這種懲罰的嚴重後果足以讓你心甘情願地信守自己的諾言。以這種方式,你的合作夥伴就無須通過你的口頭承諾來判斷你是否可信,他完全可以通過衡量你的利益得失來決定是否可以與你合作。
在當今社會中,人們用法律契約作為承諾的擔保,如果違約,我們就得接受合同所規定的懲罰條款。貸款購房時,我們以房屋作為抵押,如果不能償還貸款,銀行就有權收回我們的房產。我們遵守婚姻法,如果遺棄或虐待配偶,他們就有權索要離婚贍養費並分割財產。我們繳納履約保證金,如果未能履行自己的義務,保證金就會被沒收。不過,在我們有資格借助商業和法律手段執行合同之前,我們必須首先進行自我設限。擔保承諾時,孩子們會使用那些最原始的說法,“如果騙你我就去死”。就成人而言,過去,他們常常用上帝的懲罰作為起誓,比如,May God strike me dead if I'm lying(要是我說謊,願上帝賜我死)以及這句話的一些其他表達形式,例如,As God is my witness(上帝作證)、Blow me down!(太驚人了!)、Shiver me timbers!(你嚇唬我!)、God blind me!(老天爺!)——英國人的blimey(天哪,blind me的縮略形式)就是由這個表達式衍生出來的。
人們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他們曾一度堅信,上帝隨時都在傾聽他們的懇求,並會救贖他們,當然,在過去那些日子裡,這些誓言會更可信些。可是後來人們逐漸發現,即使他們信誓旦旦地以上帝的名義發誓賭願後食言了,上帝也不曾對自己實施過任何懲罰,於是,他們便開始懷疑這個世界上真有上帝嗎?上帝真的會救贖他們嗎?退一步說,至少人們對上帝對他們的關注程度開始心存疑慮。當然,上帝在塵世的那些代言人們倒是寧願人們保持之前的信仰,堅信上帝始終都在聆聽自己的呼聲,並會在大是大非面前救贖自己;他們希望人們相信,上帝的冷漠是因為人們不分事情的大小輕重,事事都要祈求保佑,而這讓上帝覺得自己的威嚴受到了小視,因而心生不悅。而同樣由於這個原因,人們的起誓也變得徒勞無功了。
既然沒有上帝的直接托管代理,人們便可以更加圓滑地借用聖名來擔保自己的承諾,他們拐彎抹角地將上帝扯進自己的討論中。(在下一章中,我們將看到,最奏效的威脅往往是那些隱性威脅。)人們將自己的信譽與上帝可能始終感興趣的附屬物聯繫在一起,比如,他的名字、他的象徵、他的著述、他的身體部位,等等。於是便出現了以……的名義起誓(swearing by)和憑……發誓(swearing on)等諸如此類的起誓現象。即使在當今,美國的審判程序上仍然有這麼一個步驟,證人將手放在《聖經》上起誓,彷彿在告訴人們,如果做了偽證,即使他可以僥倖逃脫法律的監督,卻無法逃脫無所不知的上帝的眼睛,上帝一定會嚴懲他的。早些年間,英國人以耶穌殉難的名義起誓:他的血('sblood)、他的指甲、他的傷口(zounds)、懸掛他的吊鉤(gadzooks)以及他的身體(odsbodikins)。此外,人們還會以十字架的名義起誓,這就是孩子們說的那句Cross my heart.(我發誓)的出處。不過,最有創意的還是奧利弗·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寫給蘇格蘭長老會的那句話:“我懇請你們,看在基督內臟的份上,相信你們自己也有犯錯誤的可能。”
即使人們並不相信這些誓言真的能夠帶來懲罰,但它們卻傳達了這樣一種信息,即蠅頭小利的日常保證與重大事件的莊嚴承諾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件事。保持一種宗教聖物的神聖性實際上是一種社會建構,它取決於一個社團中的每個成員對其宗教聖物的敬畏和虔誠。這需要一種對集體精神的控制,任何人都不能隨隨便便地看、想或者談論一件神聖的東西。起誓時,人們將這一聖物牽扯到辯論中就是為了迫使對方去思考那些平時不會輕易去思考的問題,因此,這就意味著,說話人是絕對認真的。出於同樣的原因,如果人們過於隨便地利用一種聖物發誓賭願的話,那麼它的神性就會受到這種語義膨脹的威脅,這就是為什麼那些基於神聖統治的政權會採取各種手段遏制這種情況發生的原因。反對“濫發誓”的法律可能會更受歡迎,因為人人都希望,在他們需要用誓言約束自己時,這種語言的威力能夠發揮作用,而且,他們並不希望由於自己的濫用而使得這種語言的魔咒遭到解除。
現在看來,儘管以上帝的血和內臟之名發誓顯得有些過於陳腐,但隱藏在其背後的禁忌心理卻依舊鮮活。作為家長,即使沒有任何宗教信仰,他們也不會輕易地作出“我以我孩子的生命起誓”這樣的承諾。只要一想到要以孩子的生命為代價,無論為了什麼利益,人們都會覺得極其不爽,假如那個孩子恰巧是自己的,那麼,這根本就是不可想像的事情,人們大腦中的每一根神經都會站出來抵制這種念頭。即使這只是個閃念,也會令他們毛骨悚然,不過,這種強烈的自我威脅感確實能夠提高一個人的可信度。普通禁忌心理學正是建立在人類難以接受背叛親人或同伴這一事實的基礎之上。人們在以某種神聖為名進行起誓的過程中,無論它是一種宗教的象徵符號還是一個孩子的性命,這種心態始終貫穿其中。由於語言加工是機械地進行的,用於神聖起誓的敬神話語——也就是swearing這個詞的“發誓”的意思既可以被用來吸引人的注意力並震懾他人,也可以用來造成對方精神上的痛苦——這就是swearing的“咒罵”的意思。
另一個歧義動詞cursing(詛咒)也是個宗教禁忌語。就像人們可以通過一句詛咒將任何形式的不幸或侮辱強加給他人那樣,基督教將一種令人極其不爽的想法打包進各種詛咒中,並強加給他們的仇視者:這種想法就是他們可能會在地獄中度過來世今生。今天,Go to hell!(見鬼去吧!)和Damn you!(你這該死的!)已經演變成常見的溫和修飾語,不過在很久以前,人們確實擔心會被永遠地處以烈火焚身、唇焦口燥的刑法,並終生與可怕的食屍鬼以及毛骨悚然的尖叫聲和呻吟聲為伴,在那些年代裡,這些說法的衝擊力遠比現在大得多。從下面這些咒罵中,我們仍然可以依稀感受到那些詛咒人下地獄的話給當時的人們所帶去的那股原始的衝擊力,設想有人盯著你的眼睛說“我希望你因稅務欺詐而被判處20年監禁。我希望你的單人牢房炎熱潮濕、蟑螂氾濫,到處散發著糞尿的臭味。我希望3個惡棍和你同住在一間牢房,他們每晚都暴打並雞姦你”如此這般。對於那些曾經相信地獄存在的人們來說,詛咒到底有多殘酷?它究竟意味著什麼?當我們對這些問題進行反思時,我們真該感謝當今那些極端又頭腦發熱的人們手下留情,他們畢竟只是將自己局限於一小部分污濁物和性的陳詞濫調之內,我之所以說它們是陳詞濫調,是因為這些咒語的意象很久以前就已經枯槁了。
同樣失去鋒芒的禁忌語義場還包括疾病和瘟疫,例如,A plague on both your houses!(願瘟疫降臨到你們兩家!/意為:你們兩個都別說了!)[16]、A pox on you!(願你臉上出水痘!/你該死!)以及波蘭-意第緒語中的Cholerya!(願你得霍亂!/不得好死!)。隨著環境衛生大幅度改善以及抗生素的誕生,這些隱喻的殺傷力也變得越來越弱,人們很難再感受到它們曾經帶給人們的那種致命的打擊。不過,這兩個語義場倒是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巨蟒與聖盃》(Monty Python and the Holy Grail)中的那一場Bring out your dead!(拉[死於黑死病的]屍體的馬車過來了!)的情節,或醫學教科書中的膿皰、大出血、眼潰瘍、腹瀉以及與這些疾病有關的其他一些可怕症狀。在現代社會中,與這類話語平行的說法大概包括這樣一些詛咒:“但願你陷入火海,讓大火把你燒成三度重傷。但願你中風抽搐,流著口水終生癱瘓在輪椅上。我希望你患上骨癌,在你的親人面前油盡燈枯、氣息奄奄。”看來,那些將發誓賭願說成是文化粗俗化走勢的標誌的評論家們,應該再次反省一下他們的定論了,與上述提到的那些歷史標準相比,我們今天的詛咒該是多麼的溫和淡雅啊。就這一點來說,我這裡還有一個更有力的證據,很顯然,現代人忌諱用癌症(cancer)這種最令人恐慌的疾病起誓。這個詞已經衍生出了一些委婉語,例如,the big C(大C)、malignancy(惡性腫瘤)、neoplasm(囊腫)、mitotic figure(分裂象)等,此外還有一種常常出現在訃告中的說法:a long illness(長期患病)。
儘管人們已經不再以疾病的名義發誓,但體液、身體上的孔洞以及排泄行為等依然是人們借用於起誓的對象。Shit、piss、asshole等詞語還是不能在網絡電視中隨便使用,或在報刊上出版發行。以《紐約時報》為例,這家報紙最近將哲學家哈利·法蘭克福(Harry Frankfurt)寫的那本暢銷書《論扯淡》(On Bullshit)改成了“On Bull——”。Fart也不比上面那幾個詞更被大家接受,《泰晤士報》已決定將其用於印刷體寫成的old fart這個表示年齡歧視的表達式的一部分,而不是那個表示腸胃氣脹的方言詞。Ass、bum、snot以及turd也無一例外地遊走於體面的邊緣。
Bloody是另一讓人聯想起體液的詞。正如許多禁忌語那樣,沒有人真正瞭解它到底出自何處,因為人們往往不會公開發表他們的不敬言辭。儘管如此,各種通俗語源學(folk etymologies)的無稽之談從未銷聲匿跡過。就像我們在第5章中所看到的Fornication Under Consent of the King(國王應允的私通)以及Ship High in Transit(航海過程中升高貨艙甲板)那樣。以bloody為例,休斯曾說過:“我相信我並不是第一個(多次而且是十分有把握地)被告知bloody這個詞起源於那句宗教驚歎By our lady!(聖母作證!)的詞語愛好者。”然而,根據歷史學家的觀點,這是絕對不可能的,因它也同樣不可能出自於God's blood(上帝的血)。
還有cunt,一些人始終搞不懂這個詞怎麼就變成禁忌語了呢。這個詞不僅是對vagina(陰道的學術說法)的一種猥褻表達法,而且,對於美國婦女來說,它還是一個最具侵犯性的綽號;對於英聯邦的男人來說,它也是個不大禮貌的術語。
一般來說,禁忌語的可接受性與它們所指稱的物種的可接受性之間的關係是很鬆散的,不過,有關體內廢物這一類的禁忌語卻是個例外,它們能否被接受完全取決於它們的所指物。Shit(屎)比piss(尿)難於接受,piss(尿)比fart(屁)難於接受,fart(屁)比snot(鼻涕)難於接受,snot(鼻涕)則比spit(唾液,spit根本不是禁忌語)難於接受。這個順序與人們對在公共場所的排泄物的可接受性完全一致。
針對人們對這些物質的反感程度,語言學家基思·艾倫(Keith Allan)和凱特·布裡奇(Kate Burridge)對他們在澳大利亞的大學的員工和學生們進行了問卷調查,希望以此擴大這項研究的調查範圍。他們的調查結果如下:排泄物和嘔吐物並列第一,女性經血排在第二位(男性的看法),尿液和精液名列第三。接下來的排列順序為(按照遞減順序排列),胃腸脹氣方面:膿液、鼻屎、經血(女性的看法)並列第四,緊隨其後的物質依次為:打嗝的氣味、皮屑、汗液、剪下的指甲、口氣、傷口滲出的血液、剪掉的頭髮、母乳以及淚水。不過,它們與粗俗語的對應關係並不完美:儘管嘔吐物和膿液均屬於令人作嘔之物,但英語中卻沒有關於它們的禁忌語。相反,與體內廢物有關的粗俗詞語卻位居首位,其中包括有關精液的各種粗俗的說法,比如,cum、spunk、gizzum、jizz、cream等。
表示體內廢物的這類詞語在許多文化中都是禁忌的,當然也包括這些廢物本身。生物學家瓦萊麗·柯蒂斯(Valerie Curtis)和亞當·比蘭(Adam Biran)從他們在歐洲、印度和非洲所做的調查問卷中總結出如下的結論:“諸多報道中,身體排泄物都是最容易引起人們反感的觸發因子。全部調查列表中均有糞便,而嘔吐物、汗液、唾液、血液、膿性液體以及性交產生的體液的出現頻率也很高。”體內廢物帶給人們的是一種特殊的情感糾葛,這種情感糾葛使它們與伏都教、巫術以及其他種類的交感魔法結下了不解之緣。許多不同文化中的人們都相信,如果對一個人的糞便、唾液、血液、指甲以及毛髮等施咒,這個人就會受到傷害;而假如這些污物受到詛咒、埋葬、淹沒或者其他明顯的拋棄,那麼,人們就可以免遭傷害。由於這些物質在人們心目中的威力,他們還將與這些物質有關的詞語應用到醫藥或符咒中,尤其是順勢療法或淨化的藥劑中。厭惡情感與交感魔法心理是互相交織的。心理學家保羅·羅津(Paul Rozin)和艾普利·法倫(April Fallon)的研究表明,在面對自己的厭惡反應時,比如,只要看到一種看起來令人噁心的東西或過去曾經碰到過類似的東西就不會去碰它,現代西方人往往會訴諸伏都教。詞語魔法僅僅通過一種鏈接就能擴展這一聯繫鏈,並且賦予那些表示體內廢物的詞語一種可怕的魔力。
當然,人們的這種恐懼心理也是可以調節的,因為它畢竟只與性、醫藥、哺乳以及動物和嬰兒護理有關。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委婉語的使用將逐漸淡化人們對這些物質的反感,脫敏運動有時也是可以發揮作用的。
人類對自己體內廢物(既包括它們的禁忌詞,也包括這些物質本身)的異常反應令許多觀察者們都感到不解。就像宗教學者萊因哈特(A.K.Reinhart)所說的那樣:“出於某些原因,許多文化都傾向於將膿汁、嘔吐物、小便、月經、性液體等體內廢物看成是令人討厭的物質或行為,儘管它們伴隨著人類生活的始終,但人們卻將其看成是變態的物質和行為。”柯蒂斯和比蘭找出了其中一些原因。他們注意到,那些最令人噁心的物質往往是最危險的疾病傳播源,他們認為這絕非巧合。糞便是傳播病毒、細菌和原生動物的一種途徑,原生動物至少能導致20種腸道疾病以及蛔蟲病、甲型和戊型肝炎、脊髓灰質炎、阿米巴痢疾、鉤蟲病、蠕蟲病毒、鞭蟲、霍亂、破傷風等。血液、嘔吐物、黏液、膿性液體以及性交體液對病原體同樣也有很大的吸引力,它們往往被病原體當作人際傳播的載體。在高度現代化的社會裡,沖洗廁所和垃圾清運迅速地將我們與我們所產生的廢物分離開來,但在其他落後國家,這些廢物每年都會傳播出無數的疾病。在戰爭時期或天災橫行的年代,比如2005年新奧爾良那場緊隨卡特裡娜颶風而至的大洪水,即便是在高度工業化的國家,人們也同樣難免霍亂和傷寒病的威脅。
厭惡反應的最強烈表現就是不想吃或碰那些令人厭惡的東西。不過,只是想到那些體內廢物、產生廢物的身體器官與身體活動,人們同樣也會感到噁心,而且,由於語言感知是無意識的,所以,一聽到描寫它們的詞語,人們就會感到不爽。處於令人生厭之首的物質當屬那些黏性物質,其次是尿液,而且piss(小便)這個詞本身也屬於一個輕度的禁忌語。尿液通常沒有傳染性,當然,它也是一種攜帶人體代謝物和毒素的廢物,因此,它肯定不是討人喜歡的東西。寄生蟲是傳播疾病的主要載體,它們因此遭到廣泛的憎惡。毫不奇怪,它們的名字在英語的詛咒中隨處可見,例如,老鼠、虱子、蠕蟲、蟑螂、昆蟲、鼻涕蟲等,儘管它們還沒有達到禁忌的地步。有關為什麼這類詞會成為某個特定文化和年代的禁忌語,而另一些詞卻並未遭此厄運的問題始終是個謎。也許禁忌語的習得只能發生在童年時代,或者充滿情感氣息的語境中。或許它們本身有著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只要人們視它們為禁忌語,它們就永遠保持著自己的禁忌身份。
禁忌詞語的另一個主要來源是有關性方面的事情。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許多進步的思想家都認為,這類禁忌實在太荒謬了。他們指出,性是一種共同快樂的源泉,它本不應該是件恥辱和羞愧的事。性語言的過分拘謹只能是一種迷信行為、一種不合時宜的做法或者一種惡意的產物,就像門肯(H.L.Mencken)給“清教主義”下的定義那樣:“它是對某人、某地可能是幸福的這種想法的一種驅之不散的恐懼。”萊尼·布魯斯在他著名的獨白Did you come?(你來/高潮了嗎?)的結束語中說:“在這個房間裡,如果有人發現不及物動詞to come(來)是淫穢的、邪惡的、粗俗的——如果這個詞真的讓你覺得不舒服,而且你覺得我說這話很討厭,那麼‘你’很可能不能來(高潮)。”
對那些最常見的性詛咒,布魯斯同樣感到不解。
什麼是你跟誰都能說的最糟糕的事情?“Fuck you, Mister.”這實在很奇怪,因為假如我真的想傷害你,我應該說“Unfuck you, Mister”。因為Fuck你實際上是件“好事”啊!“喂,媽,是我。是的,我剛回來。噢,fuck you,媽!當然,我是說真的。爸在嗎?噢,fuck you,爸!”
布魯斯的部分疑慮來自於fuck you的奇怪句法,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它實際上並不是“發生性關係”的意思。此外,他的不解還來自於現代人(尤其是青年男子)對性在整個人類體驗中所扮演角色的膚淺認識上。
試想兩個剛剛做完愛的成年人,他們兩人都開心嗎?事實並不一定如此。一方可能會將做愛看成是一種終身關係的開始,另一方則很可能只把它當作一夜風流。而且,一方還有可能將疾病傳染給另一方。不僅如此,這份激情還可能會造成意外懷孕,而這個胎兒並不是此次激情計劃之中的產物。假如這對男女再有親緣關係,那情況就更糟糕了,因為他們的孩子很有可能會繼承同一個隱性有害基因的兩個副本,而且極易受到該基因缺陷的影響。當然,即使沒有懷孕的問題,還會有其他問題,比如,他們之間是不是還存在著一個妒火中燒的情敵、一個處於為別人撫養孩子的危險之中的綠帽丈夫,或者一個處於失去撫養自己孩子權利的危險之中的不忠妻子。此外,其中一方的父母很可能已經為他/她安排了婚姻計劃,這個計劃可能涉及大筆金錢或與另一個家族的重要聯姻。當然,還有可能是這樣一種情況,即這一對戀人並不都是成年人,或並不都是出於自願的。
進化心理學為我們揭示了人類性行為中固有的利益衝突,其中的一些衝突是置身於語言領域之外的。直截了當地談論性,這種行為所傳達的是一種不嚴肅的性態度,即性不過是一種類似於網球或集郵之類的平凡小事而已,在性關係發生的時候,這種態度會被對方感受到。而天長地久的願望則可能受到更大範圍的相關人群的關注。對於父母和其他年長的家族成員來說,他們主要關心的是自己家族傳宗接代的計劃是否會受到妨礙;而就整個社團來說,它所關心的則是性自由可能帶來的婚外生子、競爭,甚至暴力等問題。一夫一妻制度下,儘管夫妻間的理性交流可能過於陳腐,甚至有些不切實際,但對於一個家庭的長者們和整個社會來說,毫無疑問,這種理性化的性交流是最有利於他們的統治的。因此,在談論有關性方面的問題時,個人與社團的守衛者們之間存在的嚴重分歧(伴隨著社團的守衛者們在涉及自己的草率性行為時的道貌岸然),實際上並沒有什麼可值得大驚小怪的。
性衝突在男、女之間的表現最為突出,它遠遠超過了年輕人與老年人以及個人與社會之間在這方面的衝突。我們是哺乳動物,而生殖的不對稱性是這類動物的先天特徵:在整個繁殖過程中,雌性必須致力於很長一段時間的妊娠和哺乳,而雄性則只需幾分鐘的交配便可以萬事大吉。如果一個男人與許多女人發生過性關係,他就可能會有很多後代;而如果一個女性與很多男性發生過性關係,她則不會有更多的後代——即使她選擇了一個願意為她的後代投資的伴侶,或者一個能夠把良好的遺傳基因傳給下一代的伴侶。難怪男人在所有文化中都更加渴望性,更熱衷於一夜情,更有可能採取引誘、欺騙或威逼等手段來獲得性。對於男人來說,在所有條件均等的情況下,無論從遺傳還是從情感的角度來看,隨心所欲的性行為都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我們可能會認為這種不對稱性在人們對性的閒談中也應該有所表現,事實正是如此。就平均而言,男人更喜歡說髒話,而許多性禁忌語所帶給人的感覺都是對女性的侮辱——因此才有了那個禁止在“婦女和兒童面前”說髒話的傳統禁令。
男女對性語言耐受性的差別可能會讓人想起維多利亞時期的婦女,在聽到粗俗的言辭時,她們會把手腕舉到前額上,並隨即昏倒在沙發上。由於掃黃運動語言指南的出現,20世紀70年代女權運動的第二次大潮意外地復活了髒話對婦女的侵犯。格魯喬·馬克思如果知道當今的大學和企業已經實施了他在《鴨羹》(Duck Soup)中治理弗裡多尼亞(Freedonia,《鴨羹》中一個虛構的國家)的綱領“不許吸煙或者講黃色笑話”,他一定會大吃一驚的。許多公開發表的性騷擾指南都將“講性笑話”列入其定義當中,1993年,僅僅因為一位女職員偶然在編輯部聽到他對一個拒絕與他下班後一起去打籃球的男同事說了句pussy-whipped(怕老婆),《波士頓環球報》(Boston Globe)的資深記者大衛·尼漢(David Nyhan)被迫向一個婦女組織道歉,並捐贈給該組織1250美元。以激進的反黃主義聞名於世的女權主義作家安德裡亞·德沃金(Andrea Dworkin)提議,一切性交行為均屬強姦,均是對女性公然的性壓迫:
性騷擾即男性對一個權力不及自己的人所實施的性行為,而且這種定性在這種性行為中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於使那個性行為的承受者蒙受恥辱……在男權社會體系中,性就是他們的生殖器,生殖器就是他們的性主權,而這種性主權在性交中的使用就是他們所謂的男子氣概。
儘管維多利亞時期對性侮辱的過分講究遭到了現代人的嘲諷,但有一個事實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在一種放蕩的社會氛圍中,受到傷害更多的是女性而不是男性。從20世紀60年代的性解放運動早期到20世紀70年代的女權主義革命早期這10年間,許多流行文化的作品都以同情的手法來描寫那些好色之徒,以此慶祝清教主義的徹底瓦解(喬·奧爾頓[Joe Orton]、湯姆·萊勒[Tom Lehrer]、伍迪·艾倫、滾石樂隊的傑作以及詹姆斯·邦德系列電影、《羅文和馬丁斯的大家笑》[Rowan and Martin's Laugh-In]節目都是典型的例子)。重讀這些創作,那些對女性的肆意傷害會讓人感到痛心疾首。作品中的婦女們往往被描寫成放蕩不羈的蕩婦或供男人取樂、騷擾、虐待的天生尤物。中產階級文化中對這種淫蕩行為的短暫讚頌(一端是年輕人對長者、個人對社會的挑戰,另一端是女性對男性的挑戰),部分地揭示了操控性語言所帶來的利益衝突。
儘管當今的人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容易觀賞、談論或者親身體驗性行為,但性交這一話題仍然無法擺脫禁忌的身份。絕大多數人仍然不會在公共場合發生性關係、在宴會結束後交換配偶、與同胞兄弟或自己的孩子發生性關係或者公開進行性交易活動,等等。即使在性解放運動之後,對性的徹底探索仍然任重道遠,而且,這意味著,人們對某些有關性的想法仍然心有餘悸。而在人們設置這種心理障礙的過程中,性語言則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
詛咒的5種方式
有了上述這些關於禁忌語的基本內容(它的語義知識)為基礎,現在我們就可以轉向對其使用方法的探究了(它的語用知識)。回想一下,我們前面說過,所有詛咒的一個共同之處就是那些沒有人願意去體驗的情感糾葛——敬畏感(針對上帝及其外部標誌)、恐懼(針對地獄和疾病)、厭惡(針對體內廢物)、仇恨(針對背信棄義的人、異教徒及少數民族)或者墮落(針對性行為)。由於言語感知是機械的,因此,只要聽到一個禁忌詞,人們就會被迫去思考一些平時不會去思考的問題。這個現象有助於我們研究髒話是如何被使用的,說話者為什麼希望將自己的意志以這種方式強加給聽眾呢?對於這個問題,我們並沒有一個統一的答案,因為人們至少會以5種不同的方式進行詛咒:敘述性的(Let's fuck)、習慣性的(It's fucked up)、濫用性的(Fuck you, motherfucker!)、強調性的(This is fucking amazing)、宣洩性的(Fuck!)。讓我們一個個地進行考察吧。
關於髒話的許多不解之謎歸根到底都是一個問題:一個禁忌詞是如何使自己有別於其他指稱同一事物的文雅術語的?到底是什麼激起了人們如此強烈的反應?舉例來說,人們在什麼情況下會選擇使用feces而不是shit, penis而不是prick, vagina而不是cunt, have sex而不是fuck。
它們的主要差別就在於,禁忌詞是惡俗的——它使人想到它所指稱之物令人最不愉快的特徵,而不僅僅是指稱這個事物。對於排泄物來說,人們不僅討厭看到它、聞到它、碰到它,就連想到它都會感到噁心。然而我們是肉體化身的生物,排泄恰恰是我們生活中的一部分,因此,在某些場合下我們不得不共同商議處理它的辦法,別無選擇。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就是將委婉語(euphemisms,以不引起不良情緒的方法指稱一個實體)和惡俗語(dysphemisms,包括禁忌語,被用於我們希望反覆重申這個實體的討厭程度的誇張場合)區別對待。
無論在物化方面還是傳播方面,禁忌概念的委婉語和惡俗語都表現得相當迅速。據艾倫和布裡奇的統計,到目前為止,英語已經積累了超過800個有關性交的表達式、1000個男性生殖器表達式、1200個陰道表達式以及2000個有關放蕩女人的表達式(這是不是會讓你懷疑,人們為什麼還要對愛斯基摩語中有關雪的詞語量大驚小怪呢?)。在當代英語中,我們還發現了幾十個表示排泄物的專業術語,這大概是因為它既令人厭惡,又不可避免吧。
禁忌:shit
溫和的粗俗語:crap、turd
溫和的委婉語:waste、fecal matter、filth、muck
正式的表達式:feces、excrement、excreta、defecation、ordure
兒童的表達式:poop、poo、poo-poo、doo-doo、doody、ka-ka、job、business、Number 2、BM
尿布上的:soil、dirt、load
醫學上的:stool、bowel movement
動物的,大單位:pats、chips、pies
動物的,小單位:droppings
動物的,科學的:scat、coprolites、dung
動物的,農業的:manure、guano
人類的,農業的:night soil、humanure、biosolids
大多數這類禮貌術語僅限於某種特定的語境,在這種語境中,那些排泄物不得不被提及,而且它們所涉及的行為恰恰適合這種語境(作為肥料播撒、換尿布、出於醫學或科學的目的進行分析,等等)。因此,委婉語自然而然地帶給這個話題一種親近感。
就禁忌術語所指稱的對象而言,英語表現得有些過於專門化,它沒有給人們提供用於閒談的中性表達方式。閒談中,如果你的朋友使用的是feces、flatulence或anus等專業術語,而不是它們的禁忌替代詞,那麼,你即使只是在極端興奮或情緒波動的情況下說了幾句髒話,他們也會感到尷尬的。奇怪的是,其他所有與人體部位相符的盎格魯-撒克遜詞根在我們的日常用詞中都可以找到,但陰莖和陰道卻例外,當人們需要指稱它們時,就不得不使用penis和vagina這兩個拉丁語。正如劉易斯(C.S.Lewis)所說:“只要明確地涉及‘性’的問題,你就只能從托兒所、貧民區以及解剖課上的語言中間作出一種選擇。”
當然在交流中,我們有時會希望提醒對方某事令人不爽之處,此時,我們就不得不求助於那些俗語了。還有的時候,為了使我們的敘事活靈活現或者出於憤怒,我們也會使用禁忌語,借此來形容一個事物到底有多麼骯髒不堪。
那個管道工一邊在水槽下面工作一邊要跟我聊天,我只好一直看著他的屁溝(crack in his ass)跟他聊。
他的座右銘是:如果它(鬥牛)衝過來,就X(fuck)它;如果它不過來,就刺(stab)它。[17]
把你的狗屎(dog's shit)撿起,別讓你的狗在我的玫瑰花上撒尿(pissing)!
假如我們用委婉語(例如,臀部、性交等)將上述句子中的那些禁忌語替換下來,那麼它們就會讓人覺得缺少了些東西,因為我們替換掉的不僅是禁忌語,還有說話人的感情力量。由於禁忌詞語喚起的是聽眾和讀者心中的性慾細節,因此,它們常常被用於色情描寫,或被許多成年男子用於激情的喚起請求:“說點刺激的。”
毫無疑問,並不是每個人都會為特殊的修辭效果而儲備禁忌詞語。To swear like a sailor(像水手一樣說髒話)、to cuss like a stevedore(像裝卸工一樣罵人)以及locker-room language(水手在儲藏室裡說的下流話)等語言表達式表明,說髒話是許多男權和藍領階層社交圈選擇的語言。這其中的原因之一是,詛咒將迫使聽眾去思考一些令人不快的事情,它實際上是一種溫和進攻的表現。因此,它與男人們在戰亂時期炫耀自己的威武雄風、不畏犧牲的其他外部標誌(沉重的靴子、金屬釘、暴露的肌肉,等等)是相輔相成的。另一個原因是,人們故意打破一些忌諱,目的是為了建立一種隨和的氣氛,即一種大可不必謹言慎行的交際環境。近幾十年來,詛咒行為已經蔓延到了婦女和中產階級階層。(在我還是個少年的時候,正趕上“代溝”問題的全盛時期,我一位朋友的父親曾對她說:“南希,你的嘴就像個廁所。”)事實上,這一發展趨勢是20世紀追求不拘一格、男女平等以及男子氣概和酷風尚傳播的一部分。
禁忌語不僅能在人們希望向他人傳達痛苦時喚起對方的情感反應,而且,當人們希望無故造成他人的痛苦時,它也同樣可以大顯身手。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在侮辱、詛咒以及其他語言虐待形式中使用褻瀆語言。
每個人的生活中都會有這樣的時刻,你會特別想威脅、懲罰或挫敗他人的名譽。也許正是這種口頭侵略的藝術將人們的語言本能訓練得比任何其他類型的言語行為都更加富有生機,在許多文化中,它已經被提升到一個極其高雅的藝術層面。16世紀時,英國將這種口頭侵略藝術稱為“攻擊性對詩大賽”(flyting)。請看下面這段莎士比亞風格的謾罵。
亨利親王:……【你】這滿臉紅光的懦夫,這睡破床墊、坐斷馬背的傢伙,你這座龐大的肉山——
福斯塔夫:他媽的!你這餓鬼,你這張小鬼兒皮,你這干牛舌頭,你這枯槁的公牛鞭,你這乾癟的醃魚!啊!我簡直氣得連氣都喘不過來了;你這裁縫的碼尺,你這刀鞘,你這弓袋,你這倒插的銹劍——
再請看意第緒語中的詛咒。
她應該懷石頭而不是孩子。
願你掉光所有牙齒,只剩下一顆留著牙疼。
他應該把自己的一切都獻給醫生。
在打造一句詛咒時,那些能夠引起聽眾或旁觀者不爽的詞語隨手可及,它們方便得讓人根本無法克制自己的想法,這就是為什麼禁忌詞會大量出現在詛咒中的原因。人或人體部位可能被比作體內廢物以及與它們相關的器官和附件,比如:
piece of shit(討厭的傢伙)、asshole(很討厭的人)、cunt(淫婦)、twat(娘們)、prick(蠢人)、schmuck(笨人)、putz(笨蛋)、old fart(老鬼)、shithead(腦殘)、dickhead(白癡)、asswipe(笨蛋)、scumbag(人渣)、douchebag(變態)
人們可以被建議做丟臉的事情,如Kiss my ass、Eat shit、Fuck yourself、Shove it up your ass,還有那個我喜歡的Kiss the cunt of a cow(這個說法的最後一次使用是在1585年)。再如,I’ll rip your head off and shit down your windpipe(我要揪下你的腦袋塞進你的氣管裡),這句話是我在波士頓公共汽車站偶然聽到的。對其他語言中的髒話調查結果揭示了與此類似的主題。接下來就是英語中那個最常見的淫穢詛咒語Fuck you了,不過,要想真正理解它的意思,我們必須仔細考察一下有關性的禁忌語。
英語中表示性的動詞呈現出一種古怪的模式。人類學家阿什利·蒙塔古(Ashley Montagu)將fuck稱作“一個用於描寫人類行為中最及物動作的不及物動詞”,它的古怪性就在於此。想一想有關性的及物動詞——哪個符合John verbed Mary中的verbed這個及物動詞的用法:
fuck、screw、hump、ball、dick、bonk、bang、shag、pork、shtup
它們聽起來不是很好,是吧?說好聽點兒,這些動詞有些打趣或失禮的意味;說難聽了,它們其實就是對人的侵犯。那麼,在上流社會中,人們到底使用什麼動詞來指稱做愛這一行為呢?
have sex、make love、sleep together、go to bed、have relations、have intercourse、be intimate、mate、copulate
上述動詞均為不及物動詞。英譯中,指稱性伴侶的詞往往是由一個介詞引入的:have sex with(與……發生性關係)、make love to(和……做愛)等。實際上,它們中的大多數動詞本身連動詞都不是,而是由一個有名無實的“輕動詞”(light verb),例如,have(有)、be(是)或make(使得),加上一個名詞或形容詞構成的習語(在《瘋狂英語》中,理查德·萊德勒問道:“To sleep with someone[與某人睡覺],是誰在睡覺呢?A one-night stand[一夜情],又是誰站著呢?”)我們在上一節中已經看到,在很多情況下,人們對詞語的選擇是恪守禮儀的。但為什麼社會禮儀一定要將某種東西授權得像一個語法結構那樣令人費解呢?
這裡,我們在第1章中對動詞結構所做的分析又能派上用場了。還記得我曾說過,每一種句法構式都從一組微類(micro-classes)中選擇適合它的動詞,而每個動詞都有一個與該構式本身的含義相符合的含義,二者至少隱喻性地兼容。那麼,利用這一原理,我們是否可以從有關性的動詞(即那些不同於傳統語法的“系詞性動詞”[copulative verbs])的句法中發現一些人類性行為的蛛絲馬跡呢?
禮貌習語都有一些洩露天機的語法特徵。由於缺乏獨特的動詞詞根,它們便無法指定一個動作特有的運動方式或效果類型。由於缺乏直接賓語,它們也無法指定受該動作影響的實體或被動發生改變的實體。不僅如此,它們的語義還是對稱性的(symmetrical):如果約翰和瑪麗做了愛,這就意味著瑪麗也和約翰做了愛,反之亦然。因此,所有這些動詞都可以出現在另一種不及物動詞的替換構式中,在這個構式中,性愛夥伴並不需要通過介詞引入,相反,它構成了一個複數主語的一部分:John and Mary had sex(約翰和瑪麗發生了性關係)、John and Mary made love(約翰和瑪麗做愛了)、John and Mary were intimate(約翰和瑪麗親熱了),等等。而那些具有同樣句法特徵的、與性無關的動詞的語義則屬於一種聯合自主行動(joint voluntary action),例如,dance(跳舞)、talk(說話)、trade(貿易)以及work(工作):John danced with Mary(約翰與瑪麗跳舞)、John and Mary danced(約翰和瑪麗一起跳舞),等等。因此我們可以說,在心理模型中,禮貌性動詞預設著性是一種未指定方式的、雙方共同參與的活動。
下面我們來比較一下那些與性有關的粗俗及物動詞。回憶一下我們在第1章中的發現,及物動詞所描寫的是一個故意對一個實體實施侵犯、影響,或者既侵犯又影響的施事者。儘管fuck與我們在第2章中看到的那5類及物動詞都不完全符合,但它確實與運動-接觸-效果(motion-contact-effect)那類動詞微類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它可以被意動類(conative)、物主提升類(possessor-raising)或者中間構式(middle constructions)所接納,但卻不能進入接觸格構式(contact-locative)和反使役構式(anticausative construction)中。這與fuck這個動詞在古斯堪的那維亞語中表示beating(有節奏地伸縮)、striking(敲打)或者thrusting(插入)的動詞詞源學是一致的,此外這與fuck的兩個及物同義詞bang和bonk是動詞這一事實也是符合的。
如果描寫性的及物動詞意味著其直接對像受到了影響,那麼,準確地說,它到底是怎樣受影響的呢?我們可以從萊考夫對性動詞參與概念隱喻的方式所做的分析中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許多性及物動詞都可以被隱喻性地用來指稱不擇手段地利用(exploitation),這一隱喻還包括:I was screwed(我完蛋了)、They fucked me over(他們耍了我)、We got shafted(我們受騙了)、I was reamed(我被X了)以及Stop dicking me around(別逗我了)。
這些性及物動詞的另一個隱喻性主題是嚴重的傷害,例如,fucked up(徹底完蛋了)、screwed up(搞砸了)、buggered up(搞糟了)以及英國人說的bollixed(搞亂了)和cockup(一團糟)。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軍隊中的俚語包括首字母縮略詞snafu、tarfu(Things Are Really Fucked Up,簡直他媽的一塌糊塗)、fubar(Fucked Up Beyond All Recognition,亂得他媽的面目全非)。後來,這些術語被工程師們採納,並成為他們的行話,現在,當計算機程序員在創建一個臨時文件或教初學者命名一個臨時文件時,他們往往會使用foo.bar——有點兒書獃子氣的幽默。性及物動詞背後的隱喻就是“發生性關係就是不擇手段地利用某人”、“發生性關係就是傷害某人”。
許多其他語言中也都有這些概念隱喻。在巴西葡萄牙語中,fuck的粗俗等價詞是comer,“吃”的意思,這個單詞也是以男性(或採取主動的同性戀夥伴)做主語。假如站在交配力學隱喻的角度,這個動詞是不可思議的,因為應該是女人身體隱喻性地吃男人的身體。不過,它卻符合人們對性行為的理解,因為在性交過程中,總是女人被男人所享用和開發。
因此我們可以說,性動詞的句法揭開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性心理模式。第一種模式讓人聯想起性教育課程、婚姻手冊及其他更為社會認可的觀點:性是一種細節不明的共同活動,是兩個平等夥伴的交互參與。第二種性心理模式則比較陰暗一些,它介於哺乳動物生物社會學與德沃金式女權主義之間:性愛是一種強有力的行為,它在一個主動的男性的鼓動下發起,並對一個被動的女性實施影響,其中的女性要麼被不擇手段地利用,要麼遭到嚴重的傷害。兩種模型均捕獲了人類性行為的全部臨床表現,假如語言真是我們思想模式的嚮導,那麼我們便可以說,第一種性心理模式是公共話語所許可的,而第二種模式是禁忌的,儘管它在私下裡還是會受到人們的廣泛認可。
正如我所說的,純粹惡俗語與跨域到禁忌中的術語之間的界線是很難判斷的。對許多人來說,excrement的內涵遠比shit令人作嘔,因為excrement專供描述污穢和骯髒之物,而shit則可以被廣泛地用於習語和非正式語境中。然而,儘管如此,shit還是比excrement更令人難以接受。同樣,被冠以fuck的行為帶給人的不安程度無論如何也無法與被冠以rape的行為相提並論,可是rape連禁忌詞都不是。人們將一個令人不爽的詞處理成禁忌語的習慣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於一旦有人將其處理成禁忌語,其他人也會這麼做,因此,這些詞語的身份也許只能聽任那個決定著一般詞語和名字命運的“興衰”的流行病學的擺佈了。
所有這一切意味著,儘管禁忌詞喚起的是人們頭腦中關於它們的指稱對像最糟糕的印象,但並不會因此而遭到人們的排擠。禁忌身份本身就賦予了它們一種情感上的活力,這與它們所實際指稱的東西毫不相干。正是出於這個原因,無數習語中都包含著禁忌術語。一些習語還將這些術語的某些令人不快的方面隱喻性地投射到話語的主題上,例如,bullshit(胡說)、They fucked me over(他們耍了我)、He pissed on my proposal(他褻瀆我的提議)、She pissed away her inheritance(她把遺產揮霍殆盡)等。然而,更多的習語並不這樣,出現在它們當中的那些禁忌詞只起到了激發聽眾興趣的作用。
He went through a lot of shit.(他經歷了很多挫折。)Tough shit(糟透了!)We’re up shit's creek.(我們進退維谷。)We’re shit out of luck.(我們倒霉透頂了。)A shitload of money.(一大筆錢。)Shit oh dear!([新西蘭英語]天啊!)Shit, eh?([新西蘭]祝你好運。)Let's shoot the shit.(有空一起扯扯皮。)Let's smoke some shit.(讓我們吸這狗屎的煙。)Put your shit over there.(我們倒霉透頂了。)A lot of fancy shit.(許多花哨的東西。)He doesn't know shit.(他什麼都不懂。)He can't write for shit.(他什麼也寫不了。)Get your shit together.(收拾一下你的爛攤子。)Are you shitting me?(你耍我呢?)He thinks he's hot shit.(他以為他有什麼了不起。)No shit!(胡扯!)All that shit.(全是狗屎。)A shit-eating grin.(吃屎的笑容。)Shitfaced[drunk].(爛醉如泥。)Apeshit.(發瘋。)Diddly-shit.(廢物。)Sure as shit.(肯定。)
It's piss-poor.(太差了。)Piss off!(滾!)I'm pissed at him.(我生他的氣。)He's pissed off.(他被惹怒了。)He's pissed.(他喝醉了。)Full of piss and vinegar.(朝氣蓬勃。)They took the piss out of him.([英國]他們嘲弄他。)
My ass!(才怪呢!)Get your ass in gear.(挪挪你的屁溝。)Ass-backwards.(搞錯了。)Dumb-ass.(蠢驢。)Your ass is grass.(你死定了。)Kiss your ass goodbye.(滾蛋吧。)Get your ass over here.(快點過來。)That's one big-ass car!(一輛超大的車!)Ass-out[broke].(一毛不剩。)You bet your ass!(你太他媽的對了!)A pain in the ass.(眼中釘。)
Don't get your tits in a tangle.([新西蘭]用不著這麼激動。)My supervisor has been getting on my tits.([英國]我導師總是無緣無故地跟我發火。)
Fuckin-A!(操!)Aw, fuck it!(噢,他媽的!)Sweet fuck-all(操她媽的!)He's a dumb fuck.(他是個白癡。)Stop fucking around.(別瞎胡鬧了。)He's such a fuckwit.([新西蘭]他就這麼白癡。)This place is a real clusterfuck.(這地方一塌糊塗。)Fuck a duck!(去你的!)That's a real mindfucker.(那可真是個痛苦的局面。)Fuck this shit.(真他媽的見鬼。)
在詞典編纂者傑西·薛洛爾(Jesse Sheidlower)所編輯的專業詞典《髒詞》(The F-Word)中,類似於上述這種類型的詞條至少有250個。正如我們在第4章中看到的,隱喻和習語可以凝煉成無須進一步分析的公式。這一點似乎已經在這些粗俗習語上(至少部分地)得到了驗證,在禁忌語的冒犯使用方式中,連同fucking amazing(太他媽的讓人震驚了)這樣的咒罵語,它們構成了最溫婉的表達方式。
禁忌詞對情感的超強影響力使得它們進入了一個同義詞的怪圈:即使在語法或語義方面沒有任何關係,它們也可以在習語中彼此替代。我猜測,許多令人不解的不合語法的髒話一定源自一些更可理解的宗教髒話,尤其當它們在從宗教到性以及污穢的咒罵的轉變過程中時。
Who(in)the hell are you?(你到底是誰?)→Who the fuck are you?(你他媽的是誰?)(Also:Where the fuck are you?What the fuck are you doing?Get the fuckout of here, etc.)(亦作:你到底他媽的在哪兒?你到底他媽的在幹啥?給我滾出去,等等。)
I don't give a damn.(我根本不在乎。)→ I don't give a fuck;I don't give a shit;I don't give a sod.(我才不在乎。)
Holy Mary!(天哪!)→Holy shit!Holy fuck!(天哪!)
For God's sake(看在上帝的份上)→For fuck's sake;For shit's sake(他媽的)
就禁忌詞語間的內部關係而言,它們的內涵要比語義或句法更能說明問題。它有助於我們理解英語髒話句法中的兩個重大奧秘:fuck在Close the fucking door(關上那該死的門)和Fuck you!中分別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對於這些難解之謎的探討最初見於紀念文集:《關於胡言亂語的研究:值此詹姆士·D.麥考萊誕辰33或34年之際獻給他的誹謗文章》。它可以稱得上是學術史上最新奇的一本文集了。已故語言學家吉姆·麥考萊(Jim McCawley)是生成語義學的創始人之一(此外還包括當代語言學家喬治·萊考夫和哈吉·羅斯[Haj Ross]等人)。麥考萊的貢獻包括一本名為《語法理論三千萬》(Thirty Milion Theories of Grammar)的指南、一本名為《語言學家們一直想瞭解(但都羞於咨詢)的全部邏輯問題》(Everything That Linguists Have Always Wanted to Know about Logic[But Were Ashamed to Ask])的初級讀物和一本《食者的漢字指南》(The Eater's Guide to Chinese Characters),最後這本是教授讀者用中文菜單點菜的指南手冊。1971年出版的這本紀念文集中彙集了眾多的反常規文章,其中有幾篇是麥考萊以筆名Quang Fuc Dong和Yuck Foo(這兩個名字據說都是他所創作的虛構的南河內理工學院的語言學家的名字)所創作的。在這部文集中,儘管有些詼諧和實例令人一知半解和乏味,但麥考萊對英語禁忌表達式所做的精細的語法分析,至今仍被學術研究所引用(有時被稱為“Quang[1971]”或“Dong, Q.F.”)。
感歎詞,如bloody(非常的)和fucking(他媽的)也許是閒談中最常用的禁忌詞了,儘管它們的語義和語法都很荒唐。一本有百年歷史的英國俚語詞典對bloody這個詞條做了如下的定義:“最常見的……因為在倫敦底層人口中,每兩到三個音節中就會反覆乏味地出現一次這個詞;它的使用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含義,更不用說什麼血腥的含義。”湯姆·沃爾夫(Tom Wolfe)對一種叫作Fuck Patois(他媽的方言)的方言也做過類似的觀察,比如,在一個關於士兵的故事中,那個士兵說:“I come home to my fucking house after three fucking years in the fucking war, and what do I fucking-well find?My wife in bed, engaging in illicit sexual relations with a male!”(打了他媽的三年仗,我他媽的回到了家,進了該死的房間,我他媽的看見了什麼?我的妻子正在床上和一個男的胡搞呢!)
這種扮演咒罵角色的fucking語法成了2003年的頭版新聞,當年,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直播了金球獎的實況,愛爾蘭老牌搖滾樂隊U2的主唱波諾發表了如下感言:“This is really, really, fucking brilliant”(這他媽的實在、實在太好了。)事後,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並沒有馬上處罰有關媒體,因為他們的相關指南將“下流”定義為“描述或描繪性或排泄器官或活動的語料”,而波諾對這個fucking的使用屬於“強調一種感歎的形容詞或虛詞”。然而,文化保守派對此卻表現出了強烈的憤慨,加州參議員道格·奧賽(Doug Ose)還試圖利用美國國會規定的最污穢的法案,即《清潔電視廣播法案》來彌補委員會的這一漏洞:
法案
對《美國法典》標題18項中的第1464款進行修正,並為某些褻瀆廣播節目的行為提供懲治條例及其他用途。
國會會議中,眾議院和參議院代表制定了如下法案:《美國法典》標題18項的第1464款現修正如下——
(1)通過在“任何人”前面插入“(a)”,並且(2)在此條款的結尾處補償如下內容:(b)本條款規定,就語言而言,profane(褻瀆的)這個術語的內容包括英語單詞shit、piss、fuck、cunt、asshole以及短語cock sucker、mother fucker、ass hole以及這類詞和短語相互使用,或者與其他詞或短語或其他語法形式(包括動詞、形容詞、動名詞、分詞和不定式形式)相互使用。
不幸的是,對於奧賽議員來說,該項法案絲毫沒能彌補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的那個漏洞,因為它未能恰當地指定波諾所說的那句髒話的句法(更不用說法案裡面cocksucker、motherfucker以及asshole的拼寫錯誤,或者將它們認定為“短語”的錯誤)。
《清潔電視廣播法案》假定fucking是一個分詞性形容詞(participial adjective)。遺憾的是,這是個錯誤。正如Quang所指出的那樣,對於一個真正的形容詞來說,比如lazy(懶惰的),你可以將它們交替地用於這樣兩種構式中:Drown the lazy cat(淹死那只懶貓)和Drown the cat which is lazy(把那只懶惰的貓淹死)。但Drown the fucking cat(淹死那只該死的懶貓)肯定不能與Drown the cat which is fucking(淹死那只正在發情的懶貓)替換使用。同樣的,Drown the bloody cat(淹死那只該死的懶貓)並不意味著Drown the cat which is bloody(淹死那只血腥的懶貓)。你也不能說The cat seemed fucking(那隻貓似乎他媽的),或者How fucking was the cat?(那隻貓有多麼他媽的?),或者the very fucking cat(那只非常他媽的貓),這是3個經常用來測試形容詞詞性的小實驗。
一些批評人士還對《清潔電視廣播法案》中另一個語法上的無知進行了調侃。如果有什麼不同的話,短語fucking brilliant(太他媽的好了)中的fucking應該是個副詞,因為它修飾的是形容詞,英語中只有副詞才能修飾形容詞,就像下面短語中的副詞那樣:truly bad(確實很壞)、very nice(非常好)、really big(確實很大)。然而,在上面的profane一詞的定義中,奧賽恰恰忘了將“副詞”這一語法範疇包括進去了!碰巧,禁忌感歎語(expletives)也確實不是真正的副詞。關於胡言亂語的研究中的另一篇文章指出,儘管你可以說That's too fucking bad(太他媽的糟糕了)和That's no bloody good(不咋地),但你卻不能說That's too very bad(那太非常壞了)或者That's no really good(那不真的好)。同時,正如語言學家傑弗裡·納恩伯格(Geoffrey Nunberg)所指出的那樣,儘管你可以用very(太精彩了)來回答How brilliant was it?(到底有多精彩?)但你卻永遠也不會聽到這樣的對話:“How brilliant was it?”(到底有多精彩?)“Fucking”(他媽的)。
還有比這更反常的情況,禁忌感歎語竟然還可以出現在一個單詞或一個合成詞的中間,舉例來說,in-fucking-credible(難以他媽的置信)、hot fucking dog(熱他媽的狗)、Rip van fucking Winkel(瑞普·凡他媽的溫克爾)、cappu-fucking-ccino(卡布-他媽的-奇諾)以及Christ al-fucking-mighty(全能-他媽的-上帝)——英語中唯一一種利用中綴來構詞(infixation)的情況。此外,bloody也能做中綴,例如,abso-bloody-lutely(相當絕對)、fan-bloody-tastic(相當奇怪)。威爾士作家狄蘭·托馬斯(Dylan Thomas)在他的回憶錄《青年狗藝術家的畫像》(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Dog)中寫道:“你總是能辨別出從大橋那端傳來的布谷鳥的叫聲……cuck-BLOODY-oo, cuck-BLOODY-oo, cuck-BLOODY-oo。”
禁忌感歎語的語義與它的句法一樣離奇。bloody和fucking一般表達不贊成的意思,不過,這個反對卻未必是針對那個被修飾的名詞的。
面試官:英國食品為什麼這麼糟糕?
約翰·克裡斯:因為我們要經營我們了不起的帝國,你明白了嗎?
(Because we had a bloody empire to run, you see?)
克裡斯實際上並不是在諷刺英國這個日不落帝國;他是在表達對英國食品很糟糕這一事實的嘲諷。同樣,如果我說They stole my fucking laptop(他們偷了我該死的筆記本電腦),毫無疑問,我肯定不是在詛咒我的筆記本,它說不定還是個手感極佳的鈦強力筆記本呢(蘋果),17寸的顯示屏、1.67千兆赫的處理器。禁忌感歎語所傳達的信息是,整個事態,而不是由那個名詞所命名的實體令人不開心,儘管那個實體與整個事態有必然的聯繫。同樣重要的是,我們說這個情況令人不爽,一定是站在說話者的立場上的,而絕不是這個句子所提及的任何其他人。如果有人告訴你John says his landlord is a fucking scoutmaster(約翰說他的房東簡直就是個他媽的童子軍團長),你應該將他對童子軍團長的不敬歸罪於向你報告的那個人,而不是約翰,儘管fucking被用在了傳達約翰話語內容的從句裡。
這一語言難題的部分解釋是,bloody和fucking這樣的禁忌感歎語很可能是在禁忌語更新換代的過程中產生的(儘管它們之間並沒有相同之處),比如,允許Where in hell(究竟在哪)轉變成Where the fuck(究竟在哪)、Holy Mary(聖母啊)轉換成Holy shit(天啊)的過程。就fucking scoutmaster(他媽的童子軍團長)或者bloody empire(了不起的帝國)中的禁忌感歎語而言,它們的歷史源頭很可能是damned(該死的)或God-damned(該死的),在一些表達式中,它們現在依然存在,例如,Damn Yankees(該死的美國佬)、They stole my goddam laptop(他們偷了我該死的筆記本電腦),還有abso-goddam-lutely(絕對地)。Damn是在damned的虛綴-ed被吞音並在感知上被忽視的情況下演變而成的,例如,ice cream(冰激凌)、mincemeat(甜餡)、box set(盒子佈景),它們之前分別為iced cream、minced meat、boxed set。如果有什麼東西是被詛咒的(damned),那麼它就是該受譴責的、值得憐憫的、不再有世俗用處的。fucking、bloody、dirty、lousy、stupid這些與damned有著類似情感弦外音的詞語能夠讓人聯想起damned的含義。因此,在英語史上,一旦某些宗教禁忌感歎語失去了鋒芒,它們便與damned一道將其取而代之。
這一語言難題的另一部分解釋方案是,富載態度(attitude-laden)的詞語有時會躲開標準的語法機制,即在句法樹形圖上通過詞語的組織順序來計算“誰對誰做了什麼”的語法機制。克裡斯托弗·波茨(Christopher Potts)等語言學家主張,英語語法不僅允許說話者在一句話中作出斷言——什麼是“有待解決的問題”,而且還為他們提供對該斷言發表個人評論的科學方法。這些方法有時被稱為規約含義(conventional implicatures),它允許說話者表達自己對正在談論的事情的態度,比如,他對結果的意見或他對參與者之一的尊重程度。其中一種方法就是,允許一個富載態度的詞語擺脫被描寫事件中的人物,轉而傾向於說話者的世界觀。例如,如果我說“蘇相信那個混蛋戴夫得到了晉陞”,這很可能意味著蘇對戴夫有著很高的評價,但它同時暗示著,我並不這麼看待戴夫。這恰恰就是fucking和bloody這樣的禁忌感歎語的解釋方案。
禁忌術語的可更新性(swappability)還可以用來解釋Fuck you之謎。還記得伍迪·艾倫那個詛咒司機的笑話吧——“多子多孫,枝繁葉茂,見你的鬼去吧”,這個笑話假設Fuck you是第二人稱祈使語氣,就像Get fucked(去死吧)或者Fuck yourself(滾)那樣。萊尼·布魯斯也作過同樣的假設,正如比爾·布萊森(Bill Bryson)在他那本令人賞心悅目的小書《母語:英語以及來龍去脈》(The Mother Tongue:English and How It Got That Way)中所寫的那樣:
英語的非凡表現就在於它既囊括了無稽之談,也囊括了令人神清氣爽的事物。我們的語言有一個不被人知的怪癖好,當我們希望表達自己的極度憤怒時,我們會懇請我們的憤怒目標去做一件解剖學上不可能的事情,更有甚者,我們甚至會懇請它去做一件勢必讓它快樂無比的事情。你想想,還有什麼能比Get fucked更不可思議的情緒嗎?我們有時也會咆哮著說“祝你發財”或“祝你好心情”。
Quang對上述理論進行了細化。首先,在第二人稱祈使語句中,人稱代詞必須是yourself(你自己)而不是you(你)——麥當娜的那首流行歌曲題為Express Yourself(表現自我)而不是Express You(表達你)。其次,真正的祈使句,例如,Close the door(關上門),可以嵌入在許多其他構式中。
I said to close the door.
我說關門。
Don't close the door.
不要關門。
Go close the door.
去把門關上。
Close the door or I’ll take away your cookies.
關上門,否則我拿走你的餅乾。
Close the door and turn off the light.
關上門,然後再關上燈。
Close the door when you leave tonight.
晚上離開的時候關門。
而Fuck you卻不能這麼用:
*I said to fuck you.
*Don't fuck you.
*Go fuck you.
*Fuck you or I’ll take away your cookies.
*Fuck you and turn off the light.
*Fuck you when you leave tonight.
此外,在第三人稱賓語中,這種差別也可以被觀察到,例如,Fuck imperialism!(X帝國主義!)。儘管可以通過一個共享賓語將兩個祈使句聯合在一起,例如,Clean and press these pants(清洗並熨燙這些褲子),但卻不能用同樣的方式將一個詛咒語和一個真正的祈使句聯繫起來,例如,Describe and fuck imperialism(描述並X帝國主義)。
Quang並沒有就Fuck you的民俗詞源學觀點——它是I fuck you的省略形式,進行任何評價(就像在引言中那個不耐煩的顧客和空姐的故事裡所描寫的那樣)。很顯然,這種民俗看法與“性是一種不擇手段的利用或傷害”這一概念隱喻是相輔相成的,但遺憾的是,就語法來說,它卻是講不通的。首先,fuck的時態是錯誤的;其次,主語的缺失也是無法解釋的;最後,語言中並不存在與此類平行的結構。還有更重要的一點,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證明,在英語中,I fuck you曾經是一種常見的詛咒。
最簡單的解釋是,fuck you中的fuck與Where the fuck(究竟在哪)和fucking scoutmaster(他媽的童子軍團長)中的fuck是一樣的:對一個有著類似情感弦外音的老宗教髒話的更新。在這種情況下,它的一個最可能的詞源就是Damn you(該死的),也許是God damn you(天罰你)和May God damn you(願上帝懲罰你)的縮略形式。它原來的語義應該是一種第三人稱的祈使含義May it be so(但願如此),這個含義常見於祝福(May you be forever young[願你永遠年輕])和詛咒(May you live like a chandelier:hang by day and burn by night[願你的生活像一盞吊燈:白天掛著晚上發熱])。但其詛咒卻漸漸融入到了對不滿的整體聲明中。正如Quang所說的,Fuck you不僅與Damn you類似,而且與僅僅表達說話者對某個對象的強硬態度的其他構式也相類似:To hell with you!(見鬼去吧!)、Shit on you!(去死吧!)、Bless you!(祝福你!)、Hooray for you!(為你喝彩!)以及那句常用的挖苦話Bully for you!(哦,你可真行!)
禁忌語的最後一個用途是宣洩——當人們感到莫名的痛苦、挫折或遺憾突如其來時,damn、hell、shit、fuck或者bugger等便脫口而出。如果你問他們為什麼這樣做,他們會說,這樣可以“釋放壓力”或者可以幫助他們“宣洩憤懣”。這就是所謂的情感液壓隱喻(hydraulic metaphor),這種隱喻還見於宣洩情感、尋找出路、大發雷霆時。儘管這種隱喻捕獲了憤懣的感覺,但它卻不能對這種情感本身作出解釋。目前為止,神經科學家還沒有發現大腦中的血管或管道攜帶加熱液體(除了複雜模式中的燃燒神經元網絡以外)。而且,目前也沒有哪個熱力學定律能夠解釋為什麼Oh和fuck能比Oh、my或者Fiddle-dee-dee(胡言亂語)的發音能更有效地消耗熱量。
不過,在宣洩式辱罵的過程中,大腦的一些其他機制也會參與活動。舉例來說,觸角電生理反應(electrophysiological response)機制在人們剛意識到犯錯時就開始啟動了。這一機制源於前扣帶皮質(大腦邊緣系統的一部分),它主要參與對認知衝突的監測。在公開場合,認知神經學家稱這種反應為“錯誤相關負電位”(Error-Related Negativity),而私下裡,他們則稱其為“狗屎波”(Oh-Shit Wave)。
一些構成哺乳動物憤怒基礎的邊緣環路也與此有關。其中一個邊緣環路叫作憤怒環路,它始於杏仁核(amygdala)的一部分,下行通過下丘腦(那個極小的調節動機的大腦集群),然後進入中腦的灰質。這一憤怒環路最初封裝著一種反射,這種反射能讓一個突然受傷或遭圍捕的動物對驚恐、傷害作出劇烈反抗,並且在逃離捕食者的過程中,它常常會發出一陣令人毛骨悚然的吼聲。任何人不小心坐到一隻貓身上或踩了狗尾巴都可能發現他們的寵物會發出一種新的聲音,有時,它們還會在腿上留下爪痕或牙印。實驗心理學對這種被稱為挫折-攻擊假設(Frustration-Aggression Hypothesis)的觀點進行了一系列研究。例如,當兩隻老鼠一同放進一隻籠子裡並對它們進行電擊時,它們就會打架。當獎賞它們的食物被突然取出時,一隻老鼠會對另一隻老鼠進行攻擊,這大概是出於對其他同伴突然竊取食物、空間或別的資源的適應吧。在人類進化的過程中,就是這個潛在的大腦環路被保留了下來。在手術過程中,當病人大腦中的這一部位受到電刺激時,他們會表現出暴怒。
這裡我們所談的是一種關於宣洩式咒罵的假說。大腦憤怒環路起著對邊緣系統與消極情緒相連成分的激活作用,因此,人類的疼痛或挫折感都來自於這裡。與消極情緒相連成分包括具有強烈情感負荷的概念表徵以及與它們相關的詞語,尤其是大腦右半球中那些積極參與負面情緒的表徵和詞語。在正常情況下,這些成分由一個基底神經節控制下的安全制動機制所控制,但這個制動機制並不是萬無一失的,在強烈的神經衝動的作用下,它就會崩潰。因此,失去理智的人很難再做到謹言慎行。就人類而言,受控反應主要是禁忌語的脫口而出。我們前面說過,動物的憤怒反應中也包括一種可怕的尖叫。也許正是這些詞語的火上澆油,再加上人們釋放反社會情緒的衝動以及他們對吼叫的強烈渴望,才使得大腦中的那些負面概念最終以詛咒的形式(而不是那種傳統的哺乳動物的尖叫)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達。(當然,人們對劇痛的反應說明,人類這一物種仍然保留著動物的咆哮本能。)綜上所述,宣洩式咒罵很可能源於那個被賦予了人類概念和發音慣例的哺乳動物的憤怒環路的串線(cross-wiring)。
這種串線假說有一個問題,即人們憤怒時發出的咒罵並不是隨心所欲的,而是約定俗成的。就像其他單詞和公式那樣,它們是基於記憶中聲音和含義的一種組合方式,而這種組合方式是一個語言社團所共享的。當我們撞了自己的頭,我們不會喊Cunt!或Whore!或Prick!,儘管這些話與shit、fuck、damn一樣,都是禁忌詞(實際上,在其他語言中,它們是人們腳被踩時所發出的喊叫的英文翻譯)。同時,根據人們所遇到的不愉快事情的成因,這些髒話也會作出相應的調整。當人們突然受到他人的侮辱時,他們會喊Asshole!(混蛋),而假如他們的手指被掉下來的熱鍋燙到或被捕鼠器夾住,他們就不會這麼喊了。因此,宣洩式咒罵是有場合和語言專屬的。就像皮爾斯夫人談及伊莉莎使用b-word單詞(bloody)時所說的那樣,我們是在母親的大腿上,或更多情況下,是在父親的大腿上學會這些用法的。在我4歲那年的某一天,我坐在爸爸身邊的副駕駛座位上,車轉彎時,車門被甩開了,我隨即說了句:“哦,該死!”當時,我為自己能在這種情況下說出像大人一樣的話而感到無比驕傲。可遺憾的是,話音剛落,我就遭到了父母的虛偽訓斥,沒辦法,這也許就是做父母的特權吧。
人們為什麼一定要出於咒罵的目的而刻意去學一些特定的詞語呢?換言之,他們為什麼不讓自己的憤怒隨便去激活某個頭腦中固有的古老禁忌語呢?事實上,語言中還有一種比宣洩詛咒更加普通的現象,即所謂的“脫口而出”(ejaculations)或稱“應急叫喊”(response cries),我們這裡所說的宣洩式咒罵只是這種現象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已。請看下面這個詞語列表。
Aha(啊哈)、ah(啊)、aw(哦)、bah(呸)、bleh(哦)、boy(嘿)、brrr(呵)、eek(呀)、eeuw(噢)、eh(嗯)、goody(太好啦)、ha(哈)、hey(喂)、hmm(嗯)、hmph(哦)、huh(哼)、mmm(嗯)、my(哎呀)、oh(哦)、ohgod(噢)、omigod(天哪)、ooh(哦)、oops(哎喲)、ouch(哎喲)、ow(哦)、oy(嗯)、phew(唷)、pooh(呸)、shh(噓)、shoo(噓)、ugh(啊)、uh(恩啊)、uh-oh(噢唔)、um(嗯)、whee(呦)、whoa(咳)、whoops(哎呀)、wow(哇)、yay(哇)、yes(是)、yikes(呀)、yipe(呀)、yuck(啐)
乍看起來,上述這些單詞似乎並不怎麼像真正的英語,它們倒像是一些人們在痛苦降臨時所發出的本能叫聲的意譯形式(transliterations of the noises)。它們根本無法用於語法句,如*I like goody(我喜歡太好啦);*I hate ouch(我討厭哎喲)。而且,其中許多單詞還違反了英語的語音模式,例如,eeuw(噢)、hmph(哦)、shh(噓)。它們甚至無法用於交換意見。
遺憾的是,它們確實是有著約定俗成的語音和語義的英語單詞。人們熱衷於對它們進行標準的改造,而不僅僅將其作為某種情感的自然流露。許多人甚至將漫畫家們用於渲染人們驚厥的擬聲形式也改造成這類感歎詞,例如,Gulp!(狼吞虎嚥)、Tisk, tisk!(看看看!)以及Phew!(唷!)等。感歎詞的誤用最容易暴露一個人的外地身份,比如在談話間,一個說著流利法語的美國人錯誤地使用英語中的um(嗯)或ouch(哎喲)等。有這麼一個笑話,在一個高級鄉村俱樂部裡,一個試圖冒充歐裔美國人的猶太婦女走進了一個冰冷的游泳池。她不顧一切地大聲喊道:“Oy vey!”(不,不!)……管它是什麼意思呢。
與語言中的其他詞語一樣,oy vey以及其他應急呼喊詞都是約定俗成的。當你看到一個可愛的嬰兒,你會說什麼?當你覺得週身發冷或者在送到嘴邊的蘋果裡發現了一條蟲子,你又會說什麼?把餐巾掉在地上呢?或者發現開著的窗子正在往屋裡刮著風呢?當一勺熱湯暖遍了你的全身,你又會作何感歎呢?毫無疑問,針對上述情景,任何一個正常的英語使用者都能從前面那個列表中準確地選出一個恰當的感歎詞。
在日常生活中,人們苦心經營著自己在真實或假想觀眾心目中的形象,作為生活這個大舞台上的一個劇院評論家,社會學者歐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為我們分析了人們在生活這場大戲中的表演,尤其是他們的言辭。他指出,人們這種表演的目標之一就是讓旁觀者們放心,自己是理智的、稱職的、通情達理的,不僅如此,他們對當前的時局有著明確的目標和理性的看法。一般來說,要想實現這一目標,人們就不能在公開場合自言自語,然而,在理性受到突發事件的挑戰時,他們有時也會破例。就這一點而言,我有個很好玩的例子。我們有時會將該帶的東西落在辦公室,可是發現時卻已經走到半路了,於是就不得不原路返回,這時,我們往往會喃喃自語,似乎在告訴身邊的人,我們並不是漫無目的瞎溜躂的精神病患者。
高夫曼認為,人們之所以發出應急叫喊是有原因的:暗示同類,我們有能力且我們對某種情形的看法與他人是相同的。一個撞到玻璃的人很可能被認為是個笨手笨腳的傢伙,但如果他說了whoops(哎喲),那麼至少能讓我們知道,他是不小心為之,而且他對此感到很遺憾。如果某人把比薩醬撒到襯衫上,或者踩到了狗的糞便,然後說聲yuck(啐),那麼這個人至少比那些對此無動於衷的人更容易被大家理解。宣洩式咒罵也是如此。面對人生目標或幸福突如其來的挑戰,我們告知世界,這次挫折對我們來說很重要,事實上,它的重要性主要體現在我們的情感層面上,因為它不僅會喚起我們最壞的想法,而且令我們瀕於自控的邊緣。與其他應急叫喊一樣,破口而出的禁忌語也是按照挫折的嚴重程度校準的,shoot(唉)表示微不足道的煩惱,而fuck則表示相當嚴重的打擊。按照人們對詞語和說話口吻的選擇,一句破口而出的禁忌語可以起到求救、恐嚇敵人的作用,或者警告一個粗心大意的傢伙,他正在無意中造成傷害。高夫曼總結說:“應急叫喊並不代表情感的宣洩,它所代表的是人們對同類事件看法的心照不宣。”
將宣洩咒罵看作是一種副產品的憤怒環路理論與將其看作是一種適應性的應急叫喊的理論其實並不矛盾。絕大多數應急叫喊也都是以約定俗成的語音表現形式出現的,例如,brr(哇)表示冷得牙齒打顫、yuck表示從嘴裡面吐出來。這種儀式化很可能是構成宣洩式咒罵的基礎。起初,這類諢名可能是由憤怒環路所釋放出的禁忌詞演變而成的,這些禁忌詞從妥瑞症患者的口中脫口而出,隨後被俗化成針對某一種冒犯或不幸的標準化應急叫喊,於是就有了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些宣洩咒語了。目前,達爾文主義的觀點已經被一些認知神經科學家們再次採用,他們主張,語言化的爆發(verbalized outbursts)是靈長類動物的叫聲向人類語言進化過程中的一個缺失環節。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麼,咒罵在人類文明中發揮的作用遠遠要超出一般人的想像。
關於詛咒的利弊權衡
那麼,針對這些粗話,我們究竟應該採取怎樣的措施呢?咒罵的科學研究能否有助於一些社會問題的解決呢?比如,廣播節目主持人語言低俗的問題以及廣播電視節目的淨化與風化問題等。就政府的方針政策而言,我個人的言論也許是無足輕重的,而且也毫無新意可言。在我看來,一方面,言論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礎,懲罰或承諾人們對某些話語的使用並不是政府的正當權利;另一方面,根據人們的品位標準和市場需求,私營媒體有權強制執行一種獨特的媒體風格,並將聽眾不喜歡的言辭排除在外。換句話說,一個藝人說fucking brilliant(太他媽的精彩了),這與政府毫不相干;如果有人不願意告訴自己的孩子什麼是口交,那麼就應該為他們開設不會讓他們感到為難的電視頻道。這裡,我並無意評論政府的相關方針政策,我只是希望就下面這個與語言相關的問題再談談我的看法,這個問題就是:禁忌心理語言學是如何幫助我們對什麼場合下應該禁止髒話、什麼場合下應該寬容甚至歡迎,作出合適的判斷。
語言常常被視為一種武器,既然是武器,那麼在瞄準何處、何時開火等問題上,人們肯定會三思而行。所有禁忌行為的一個共同之處就在於,它們均屬於一種將討厭的想法強加於他人的行為。因此,我們有必要認真思考這樣一個問題:一個人認為到底多長時間向他的聽眾提及一次糞便、尿液和濫交這樣的髒話是合適的。即使只是為了引人注目而說出的一句最溫和懶散的髒話也同樣會讓人感到不舒服。對於聽眾來說,那句話會令他們心煩意亂,而說話者卻說,他想不出還有什麼比這更能吸引聽眾注意力的辦法了。那些作家們就更是過火,要知道,英語中有50多萬個單詞可供他們慢條斯理地進行選擇。如果哪個記者在撰寫關於東德斯塔西警衛的暴行時,選不出比fucker(混蛋)更恰當的名稱來指稱那個警衛,那只能說明他需要一本更好的同義詞詞典了。
還要提醒大家反思的是,語言禁忌是否總是一件壞事。為什麼我們會遭到冒犯、為什麼我們應當被冒犯——什麼時候一個局外人士會用nigger來指稱一個非洲裔美國人、用cunt來指稱一個女人或者將一個猶太人指稱為fucking Jew(該死的猶太人)?這些術語本身並沒有什麼實際意義,所以它們的冒犯性也不可能來自它們本身。當然,它也不是對說話者令人生厭的態度的反應。當前,人們完全可以通過直截了當地說出“我討厭非洲裔美國人、女人和猶太人”來表達自己的反感,問題是,這種做法與其說是對攻擊目標的侮辱,倒不如說是對自己的侮辱,而且他們很快就會被當成令人憎惡的瘋子。我猜想,人類的攻擊意識很可能源於人們對語音識別和詞語內涵的理解。如果你是一個英語使用者,當你聽人說nigger、cunt或者fucking時,你肯定會聯想到整個英語文化對這些詞的理解,其中包括它們所隱含的情感意義。聽到別人說nigger時,事實上就是在迅速地驗證這樣一個想法,即非洲裔美國人的身上有一些令人鄙視的品質,而且整個文化一致將這一判讀標準定位在一個單詞中。其他禁忌詛咒詞也是這個道理:僅僅聽到這些詞語就會讓人感到不道德,所以,人們不僅會將它們看成是令人不爽的言辭,而且還覺得根本就不該去想它們——這就是禁忌的真正含義吧。請注意,我並不是說這些禁忌詞應該被禁止,而是我們應該理解並能預期它們給聽眾帶去的影響。
另一個值得反思的問題是:祖輩遺贈給我們的語言為什麼會在處理某些話題時表現得如此謹小慎微和縮手縮腳呢?回想一下,按照20世紀60年代言論自由者們的觀點,禁止性語言不僅毫無意義,而且相當有害。他們辯稱,將性行為從髒話中解放出來將消除人們的羞恥心和愚昧無知,從而減少性病、未婚生育以及性帶來的其他危害。不幸的是,聖·萊尼的這種觀點最終被證明是錯誤的。自20世紀60年代早期開始,性語言變得空前普及,然而,未婚生育、性傳播感染、強姦以及性競爭所帶來的附帶結果(女孩子們的神經性厭食症和男孩子們的吹牛文化)卻愈演愈烈。雖然沒有人可以確定其中真正的因果關係,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這些變化與人們對性的恐懼和敬畏的降低以及性禁忌語的解禁有必然的聯繫。
以上事實解釋了我們重新審視詛咒問題的原因。除此之外,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如果過度使用禁忌詞語,無論是精心策劃還是隨心所欲,都將削弱它們的情感表現力,這就等於剝奪了人們擁有的一種必要的語言應急工具。這讓我想起了那些詛咒贊成者們的論斷。
首先,遭人類詛咒的都是些無法改變的事實。作家的義務是為人們呈現一幅“有關人性的、恰如其分的生動意象”,這其中包括當藝術需要的時候,他們必須對人物的語言加以如實的描寫。1948年,在創作第二次世界大戰寫實小說《裸者與死者》(The Naked and the Dead)時,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清楚地知道,如果不讓士兵說髒話,那就會違背對他們的描寫。然而,出於咒罵在當時的敏感性等問題的考慮,他還是採取了妥協。小說中,他讓士兵們一律使用偽諢名(pseudo-epithet)fug(即fuck)。(當多蘿西·帕克遇見作者時,她說:“你就是那個不知道fuck怎麼拼的男人。”)可悲的是,這種謹慎的態度並不是那個時代的專利。今天,一些公共電視台仍然不敢播放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有關藍調音樂發展史的紀錄片和肯·伯恩斯(Ken Burns)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紀錄片,其原因就是,在這兩部片子中,作者與他們所採訪的音樂家和士兵們都操著滿口的髒話。廣播媒體對髒話的禁令將藝術家和歷史學家們逼成了騙子,不僅如此,它還顛覆了成年人探索世界的使命感。
為了令人信服地渲染人類的激情,即使他們的主人公不是士兵,作家們有時也必須讓他發誓賭願。在一部根據艾薩克·巴什維斯·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偽情半生》(Enemies:A Love Story)中,一個甜美的波蘭農村姑娘將一名猶太男子隱藏在一個乾草棚裡,當時正是納粹佔領時期,戰爭結束後,她自然而然地成了他的嬌妻。然而好景不長,不久他有了外遇,而且還當著那個女人的面失控地打了自己妻子一個耳光。強忍著憤怒的眼淚,她目不轉睛地看著他,一字一句地說:“我救過你的命。在乾草棚裡,我把最後一口食物給了你。我為你端屎端尿(shit)!”此時,除了shit這個詞,再沒有其他任何詞語能淋漓盡致地表達她對他忘恩負義的極度憎恨了。
對於語言愛好者來說,著名作家的作品並不是他們享受髒話樂趣的唯一來源。任何一個習語都是某個有創意的前輩的腦力勞動的結晶,其中許多世俗化的表達方式都值得我們敬佩。我們真的應該放慢奔波的腳步,細心品味這些語言大師們留給我們的豐富遺產,是他們賦予了我們的士兵shit on a shingle(鵝卵石上的爐渣,指軍隊裡對抹在吐司上的熏牛肉片的描述)、我們的男人與男人之間的性忠告Keep your pecker in your pocket(把你的命根子揣好)[18]。還是這些語言大師們,他們所構思的這些表達方式是任何其他形式所無法替代的:pissing contest(毫無結果的辯論)、crock of shit(一團狗屎,荒唐可笑的謊言)、pussy-whipped(受女人支配的,怕老婆的)、horse's ass(膿包,無能之輩)以及He doesn't know shit from Shinola(他不分狗屎和鞋油,意為毫無判斷力、一無所知)。就評價人的言辭而言,下面這幾位大師獨特的遣詞方式堪稱首屈一指:林登·約翰遜(Lyndon Johnson),見長於描寫那些令他不能信服的人,其中包括肯尼迪的助手(He wouldn't know how to pour piss out of a boot if the instructions were printed on the heel[如果指南印在了他的腳後跟上,他都不知道該怎麼才能把靴子裡的尿倒出去])、傑拉爾德·福特(Gerald Ford, He can't fart and chew gum at the same time[就連嚼口香糖和放屁他都不能同時進行])以及埃德加·胡佛(J.Edgar Hoover, I’d rather have him inside the tent pissing out than outside pissing in[我寧願讓他站在帳篷裡面往外撒尿也不願意讓他站在外面往裡撒])。
髒話在詩歌中也同樣奏效,比如,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1974年的那首《這就是詩》(This Be the Verse)中關於“人們是如何手把手傳遞痛苦”的主題。
They fuck you up, your mum and dad.
They may not mean to, but they do.
They fill you with the faults they had
And add some extra, just for you.
他們搞出了你,你的老媽和老爸。
這也許並不是他們的本意,但他們確實搞出了你。
他們將自己的缺陷全部傳給了你。
還苦心孤詣地增加了不少額外的不足,只為你。
這類語言還可以用於科學論證,比如,朱迪·哈里斯(Judith Rich Harris)對孩子的人格是父母塑造的觀點所作的如下反駁:
可憐的老爸老媽:公開地被他們的那個詩人兒子指責,卻從未得到過任何機會為自己辯護。他們現在該有一次機會了,請允許我冒昧地為他們說兩句:
How sharper than a serpent's tooth
To hear your child make such a fuss.
It isn't fair—it's not the truth—
He's fucked up, yes, but not by us.
多麼鋒利的牙齒,比蛇蠍還毒。
聽到自己的孩子如此小題大做。
這不公平—也不是真相—
他確實被搞糟了,確實,但並不是被我們搞糟的。
這類語言甚至還可以用於抗議政府制裁髒話的處罰規定,比如,巨蟒劇團(Monty Python)的艾瑞克·愛都(Eric Idle)的那首著名的《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之歌》(The FCC Song)。
Fuck you very much, the FCC.
Fuck you very much for fining me.
Five thousand bucks a fuck.
So I'm really out of luck.
That's more than Heidi Fleiss was charging me.
算你他媽的狠,聯邦通信委員會。
你罰了我的款,我算你他媽的狠。
五千塊錢X一次。
我著實倒霉透了。
這比海蒂·弗蕾絲要的價還高。
在眾多表現邏輯學家們對詞語的“提及”與“使用”之間的差異的例子中,這是我所聽過的最直觀的一個。
當咒罵被人們明智而審慎地使用時,它可以起到搞笑、一針見血、獨具匠心的作用。它比其他任何語言形式都更能激發我們的語言表現力:句法的組合能力,隱喻的喚起能力,對押韻、節拍、韻律的欣賞能力以及對態度(意料之中的以及意料之外的)的情感操控能力,等等。此外,它還可以調動我們大腦的全部時空範疇:左右、上下、遠古、當代。眾所周知,莎士比亞以擅長詛咒聞名於世,他筆下的卡利班[19]就曾說過這樣一句話:“你教會我人類語言,而我所收穫的絕非一種語言而已,現在,我知道怎麼罵人了。”就因為這句話,卡利班被莎士比亞塑造成了全人類的代言人。
